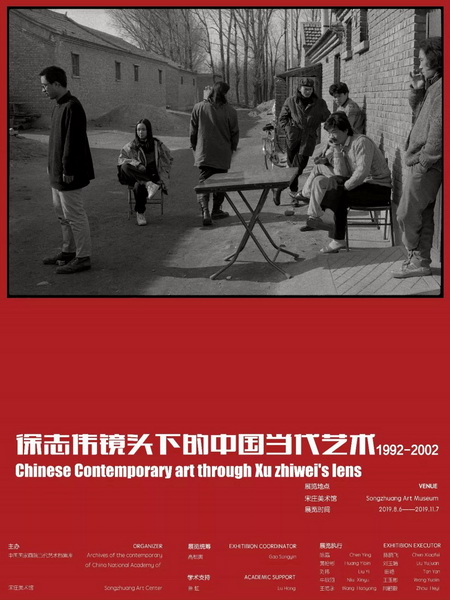文︱黄永砯
1986年9月28日—10月5日由厦门市群众艺术馆,厦门现代美术研究室主办下,一个占卜未来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种种可能性的展览在新艺术馆公开展出,这次已经不同于1983年5月“五人现代画展”那样只能是守灵式的内部观摩。(注)
83到86三年的时间,国内的现代艺术运动,包括青年艺术群体和展览可以说是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现代派”已经从瘟疫一样令人害怕变成一种赶时髦的口头禅。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足于称道的或可以留史的艺术杰作出现,只有各种折衷,夹生,粗糙和充满模仿痕迹。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使得艺术界的阵脚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同时造就了新一代人。这种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个明显的“达达”意味,在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代看来已经到来。
这三年的发展,无论是内涵或形式,是自我表现或是苦闷象征精神分析或是纯审美的形式探索,基本上追求一种自我孤绝,自我封闭为特点;青年艺术家形象则是一种浪漫的、带有忧郁症病态的所谓气质;社会、公众则反映出不适应和不理解;理论界就写实或抽象,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而争论不休,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前现代主义现象,基本上深受西方从1900到1950年艺术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西方的基本命题是艺术形式即是艺术的内容,作为自主的独立体(塞尚开始),则是沿袭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与艺术家作为一个专门职业并有专门的价值判断,这种沿袭日益抽象化和形式化。但是50年代来,西方的景观就不一样,对于西方艺术的骤变,中国人的接受程度从来就是腼腆和有节制的。有些东西是回避的。但短短几年毕竟草草地经历了西方半个世纪的艺术经验,这也是中国本土的特有现象,当然也无法产生什么对世界艺术有影响的新观念,但中国人很愿意穷追不舍,承认这一点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不可能有新观念出现,倒有些空位需要去填补,“达达”以前没光顾过,现在它也来了,凡是没有光顾过的东西一定会光顾——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都是舶来品——必然带来更深刻的混乱。那种认为国内艺术家对于国外动向几乎毫无所知的定言已经欠妥,尽管国内艺术家少有机会能目睹原作,但那对现代主义重要的东西,对于后现代则无关紧要,最终作品样式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许多通过印刷的文字和照片已经能很好地传播了思想,而关键是这种思想的启迪。开放的不可抑制,传播媒介的加速交流,对于新思潮人们已经不是合乎逻辑地吸收、消化、再吸收,而是面临着同时涌来的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的各种思潮;普普、极简艺术、偶发艺术、观念艺术、表演艺术、新表现主义,前期的、后期的等等。今天的艺术家已经不谈寒尚和马蒂斯,毕加索和米罗,达利和克利,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现在是M·杜象【1】(一个蔑视形式和内容的反艺术先驱)、Y·克莱茵(为表达信念而可以无限地扩大艺术领域)、P·曼左尼(认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把世界本身作为偶像崇拜了)、J·强斯(观察事物和正确取一个名字的困难)、J·凯奇(在艺术与生活中不寻求任何目的,只接受各种状态)、J·波伊斯(今年刚去逝的德国前卫“无所不包”的传奇人物)。劳生柏画展首先带来这一信息(下文将谈到)——一种与生活渗透、参与、兼容并包,(包容前现代主义以及它的所有对立面)多元的后现代已经到来,就中国的现状而言。
这三年中有二个国外画展值得一述,这是个消极和积极互反,终止与开始并协的展览,一是83年9月赵无极画展。这个中国人在西方现代艺坛首次成功的范例,他的成功消极地抑制了这种混乱,似乎中国宋人山水或文人画意也可能顺利地带入现代抽象绘画。看上去像一条清晰可视的成功之途,既可保持西方现代主义的非具象与平面性,又可融入东方意识中的“道”与“禅”。这种中国传统绘画与现代西方艺术的直接嫁接的局限性已日渐明显。而另一个积极反响是85年年底的劳生柏画展,这显然加剧这种混乱,前者是前现代主义,后者则属后现代,对于激进的中国人来说,赵无极显然已经老朽不足以仿效,虽然他也蔑视所谓很糟的国内“地下”国家,但毕竟不是同代人了,赵无极50年代在法国的发展与台湾“五月画会”和香港70年代的现代画基本同属一类,也就是这些致力于东方或现代主义者无不从中国哲学中周易、老子、庄子,佛教禅宗中寻求内涵,如果说其中有所获的话,那也是离质甚远,因为他们基本上还是审美的、形式主义的,本质上乃是一种自欺的理性主义,而“道”和“禅”本质上是非审美和非形式的(注2)尽管艺术家可以去直书直谈“道”和“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得其东方哲学精髓的却是一些西方人,而东方人则只抵达注诠,表现,解释这些教义,东方艺术也只是这些精神的译文而非本文。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只有后现代才从解释禅变为本身成为禅,而又没有禅的痕迹。劳生柏的一件艺术品可以以任何长短时间存在,可以用任何材料,在任何地方,为任何目的,以及任何归宿的看法,更符合于“道”而所不在,在缕蚁,在稊稗,在瓦壁,在尿溺(庄子)。他的随手拈来之物,各种不同东西同时置于画而更接近于庄子的齐物的,同一性和并存观点;杜象则比任何现代东方人更接近于老子的韬诲,静观和生活智慧,用倒置的瓷器便壶(杜象)和内装艺术家大便的闪光圆筒(曼左尼)来解答“什么是艺术”的方式,与禅宗大师的“干屎橛”(云门)“麻三斤”(洞山)来解答“如何是佛”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这种方式都是以“解答”不作为解答来理解,坚持用这种无意义的行动或语言来揭示“问”和“答”的无意义。克莱茵的通过练习日本柔述和体验身体在空中降落的感觉与禅宗的穿衣吃饭,运水搬柴的精神是一致的,凯奇的打破自我中心,以及日常生活即是演戏与禅的生活不外乎日常行事中随时体现这样的境界以及随缘任远的生活态度。波伊斯大量地用最原始的材料制作作品,意味着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不问意义,只要你同意这种情趣的暗示,他的支持所有方式的自由,他对动物讲话,都大大超出我们关于艺术或绘画的原有概念,而无不体现东方精神中博大,不执着,任自然的精髓。
当然,这些后现代出现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当时还是外主流,这类似禅宗开始标榜的“教外别佳”,但是如今已成为无所不包的主流,探其源头,无不归结为1915年达达的崛起,从瑞士达达到1920年的德国达达,以及五十年代后的各种“新达达”,如英、美的“普普”,法的“新写实主义”,直到今天的各种后现代,所以受“达达之洗礼”将使我们自觉地进入后现代。
在某种精神意义上可以这么说:禅宗即是达达,达达即是禅宗,而后现代则是禅宗的现代复兴,它们都以最坦率和最深刻著称,而且基本上不是美学意义的,而是关于真实的不可能真实,以及极端的怀疑和不信任。查拉1922年达达演讲中宣称:达达之开始,非艺术之开始,而是恶心之开始。正是由于一阵恶心之后,非艺术——不是艺术,开始转换为:非艺术——一种新艺术之开始,这是个对每个人开放的运动,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解放自己,在艺术领域中一切皆被容许,但这种解放和容许本身却无需称道,因为任何解放和最大程度的容许却意味着存在不真,因而一种新的艺术仿品,艺术家和新的公众的一个最大特征,即是其界限模糊不清,艺术作品开始不以私人杰作的积累而是公众参与或消亡,艺术家开始不用手枪,而是用微笑来行事,这意味放弃艺术家崇高的假象,放弃竞争和创新,放弃价值标准。公众对一切“新”的观念和作品不惊慌和无所谓,既把毕加索的画当作白布上的无意义涂抹,又把其当作艺术杰作。就像禅宗既把一尊木雕的释迦当作佛,又把其当作一块烧火的木料,当作“佛”是为了联系生活的世界,当作“木”是作为超越生活世界,在这一点上“佛”和“艺术”完全是作为生活世界中一个无法改变的意义而存在的。
但是一切也并非美妙,如同杜象所说,一切都要合理地不合理废除。把艺术当作“道”和“禅”的化身,也只能是相对地接近而无法等同起来。作为“道家”和“禅宗”本身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如同世界万物一样处于盛衰和变动不居之中。所以“达达”是深刻的,“达达”宣称不是所有运动上再加一个运动,而是反对所有运动,这是一个悖论:“达达”反对自身。如此一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而凶年之后呢?
最后回过来谈这次展览,这次展览与上次一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物,与实物结合的绘画以及新近增加的照片(制作和演出作品的过程)、文字(注释性或直接作为展品)、多式多样的悬挂物(作为雕塑还是作为环境的某种界限不清的东西),在没有统一纲领和散自创作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形成一个最明显的倾向:达达。看来是一种必然,不在此处,必在它方。关于这些作品具体如何,将不在特别关心之列。
1986.9.26
注1:1983年5月的五人画展是许成斗、林嘉华、俞晓刚、焦耀明、黄永砯;
注2:李泽厚把庄子哲学称为美学,主要谬误是其作者本身是个美学家。
编注:
【1】本书原稿中所提到的“杜象”,即Marcel Duchamp,1887-1968,达达主义绘画代表人物。现通译为“杜尚”。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价值判断。
扩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