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田千春(Chiharu Shiota)
盐田千春(Chiharu Shiota)1972年出生于大阪,现在工作生活在柏林。1996年从京都精华大学油画系毕业以后,她搬到德国,师从Marina Abramovic。作品包括装置、行为、录像。
在2001年横滨双年展上,作品《皮肤的记忆Memory of Skin》让她开始在日本和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关注。艺术家的创作通常与童年受到的创伤、记忆有关,Shiota对记忆的使用甚至到了有点偏执的地步。
她小的时候,曾经目睹了邻居家的一场火灾,她至今仍清晰的记得钢琴在大火里垮掉的声音。后来,她开始尝试把这种对她来说刻骨铭心的记忆转换成相对安全的可见的形式。她在房间里拉满无数密密麻麻的棉线,从地板到天花板到墙,为所有东西作茧,包括烧过的钢琴。这是她对记忆和遗忘的迷恋。
她的作品,也是对亚洲、欧洲文化转换的一种尝试。
Shiota纽约第一个个展《At Goff + Rosenthal》上,她烧掉几十把椅子,然后也给它们缠上无数的线。足足用掉14公里的棉线。从四面八方织起来的线网构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还冒着糊味的椅子,消失在观众的视线中。这只是Shiota所构建的场景的一个例子。它们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死亡、压抑、灾难的综合震撼。
Shiota经常被拿来与Eva Hesse比较,但她与Gertrude Goldschmidt更有相似之处——都把“线”作为主要材料。而线之于Shiota,更象是画布,是二维的空间,用线作画笔构成的几何刺绣。
艺术家作品

《成为一幅画Becoming Painting》 行为 1994

《我从未看见自己的死亡I´ve never seen my death》行为 1998

《我从未看见自己的死亡I´ve never seen my death》行为 1998

《尝试和回家Try and Go Home》行为 1998

《浴室》行为 录像 1999
“在这个虚伪、无止尽的世界,我用“泥土”作为创作材料。我试图一次次把泥倒在自己的脸上,以重获意识,找寻自己真正的使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仪式。我小时候的玩具娃娃已经变得破烂肮脏,逃脱了与我的关系。她有了自由,但不能呼吸。恐惧,面对生活无法相信任何事物,死亡和现在。在浴室里我把泥浆浇到头上,听身体呼吸的声音。我想要接触泥土。”

《束缚Bondage》布娃娃 泥 线 1999

《皮肤的记忆Memory of Skin》22件衣服 泥 水 2000

《皮肤的记忆Memory of Skin》22件衣服 泥 水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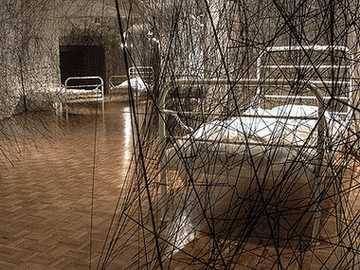
《睡眠During Sleep》装置 线 床 2001

《Zweite Haut》2001

《无题》2001

《睡眠中During Sleep》2002


《During Sleep》2005

《睡眠中During Sleep》2002

“沉睡间”即在生与死的混沌中
这次发表的另一个大作是以床为系列的,这一系列的作品是怎样诞生的呢?
盐田:96年我到德国后,在最初的3年中搬了9次家。渐渐地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感觉。做梦梦见自己在日本,起床时会分不清这里是德国还是日本。因此,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想法,希望可以加固自己所在的地方。从而开始在自己柏林的家里编织床。那之后刚好赶上发表作品的机会,就使用了这个创意。
对这一作品您是怎样考虑的呢?
盐田:床是人大多数人出生也是死亡的场所。我对这一生死混淆的场所怀有感悟,那里给我一种不安与混沌的印象。
这么说来作品是从个人的不安及焦躁感出发,从而进一步涉及生与死等普遍问题的吧。这中间的意义,想必也包含了许多近年您曾经患癌的感受吧。
盐田:实际生了病住在癌症病房的话,周围全都是会死去的人。而在妇产科那边,又会有新的生命诞生。我因有过置身其中的经验,觉得自己可以看到的世界杯扩大了。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真正使人沉默的想必正是这个吧。
原来如此。床与丝线的作品,围绕着场所及存在的主题,其出发点原来是盐田小姐的个人经验。可是,将这种个人的意向做成巨大的装置艺术的过程中,夹杂着与 和志愿者们的合作,为了避免头脑中的最初印象被破坏,您是怎样做的呢?
盐田:刚开始我会觉得无论场地多大,都只能由自己来完成。但在2000年慕尼黑的个展中,在10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要放80台床,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的话无法完成,便在那时第一次请人来帮忙。才明白除我以外别人原来也可以编得很好呢。自己一个人的话,如果不满意,剪剪编编的,做到什么时候都行。如果让别人来帮忙,就会开始犹豫不决了。也可能是这个缘故吧,产生更加崭新的作品。并没有具体的编制方法。就算从一开始编起,从那引出一条线,这条线也已经就与我最初的设计不一致了,因此作品不会按自己的意图发展。
当感觉不到所用的素材是丝线,而是好像在编织空气的时候,我便会觉得作品已经完成了。一两根的话,那只是丝线,但有许多叠加在一起的话,丝线的感觉便消失了。去年,在横滨举办名为《来自沉默》的个展的时候,水泽勉指着展品目录上我的作品评价说:“就像远处存在着安静确蠢蠢欲动的东西”。我觉得这句评价正中我心,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我感觉混沌的的远方确是存在着什么,而我就是为了能够到达那个东西的身边才创作作品的。

《静默In Silence》2002


《不确定的日常生活Uncertain Daily Life》2002

《等待Waiting》 2002

《Angst vor》 2003

《Dialogue from DNA》 2004

450双鞋都是在克拉科夫和华沙搜集来的别人不要的鞋子。请每个人写上一段关于这个鞋的故事。

将人们的思想与彼方相连的红线
这次把“精神的呼吸”作为个展的题目,请问其由来是?
盐田:大约是在3年前开始准备展览。那时虽然自己心中对想展现给别人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模糊不清,但当时想要通过展示,让观者可以听到作者精神的呼吸。
一下美术馆的电动扶梯,仿射状鲜红的丝线便直逼眼前。结着红色丝线的许多鞋子这一装置作品,在此之前已经多次发表,不过在日本确是首次公开吧。
盐田:是的。这个作品先是99年在柏林,之后又在荷兰的华沙和克拉科夫先后发表。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不过像这样大的规模确是首次。这次通过美术馆的主页的途径,早在一年前便开始对公众征集,共寄来了2136双鞋子呢。
几次展览中,不同国家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反应么?
盐田:在荷兰展出的时候,看见这么多的鞋子,使大多数观众都联想到了奥斯威辛。这也是因为展地克拉科夫与奥斯威辛离得很近,在纳粹时代那里每天有2000人被杀害,说起来就是个杀人工厂一般的强制收容所,遗迹到现在还被清晰地保留着。虽然我自己并没有此意,不过观众似乎会难以抑制的联想到这一点。
看来被丝线所结的与观者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呢。另外,展览中的每只鞋子都系着主人的留言,在这些留言中有印象深刻的么?
盐田:恩,这里面既有令人愉快的留言,也有十分沉重的呢。有婚礼时穿过的鞋,也有去逝的丈夫的鞋子,相对来说遗物相当多呢。另外,其中还有一位坐轮椅的人,为了重新站起来而买的鞋子,结果还是没能再行走,因此把用不上的鞋子送到了这里。这样一来,仿佛渐渐看到了本应看不见的鞋子的所有者们的存在,借由眼前的鞋子,感受到了他们强烈的存在感。虽然展出的只有留言条,却似乎可以看到留言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一部分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作品。
在感受空间感的同时,也确实感受到了透视时间的感觉呢。在以前的采访中,您曾说自己会就同一主题进行多年的探索,在多次发表的过程中不停调整完善自己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么?
盐田:大概,是……因为我想让看到自己作品的人能被一瞬间带到另一个世界。美术虽是视觉的产物,,但如果你想将观众带到视觉以外的领域,就要花打量时间。在这一过程的某个时刻,我会突然明白:“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啊”。而且,也清楚了自己创作它的意义。
鞋子的作品这一次的展示也与最初的发表时有一些变化吧。
盐田:是的。最初的作品最里面是被烧毁的家,从那里伸展出红色的丝线。塞黑的诗中有这样的一节“不管路把我带到何处,那里都会有令人怀念的灶火在燃烧。只是我从来不曾感受过什么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故乡。”因为当时对诗句怀有同感,便在作品中设置了具有故乡意味的家。
原来是这样。最初是以这样的形式发表,之后红色的丝线变为射向虚置的墙壁,是为了使看的人能够自由的想想吧。 从这件鞋子的作品开始,您先后创作了好几件关于丝线的作品,您能谈谈开始使用这一材料的原委么?
盐田:丝线实际是去德国以前我就开始使用了。最初只是在房间中结线,表现类似于绘图般气氛的作品,是更加视觉化的东西。现在不同的作品注入的气氛也有所不同。比如像这次的《越过大陆》,我想表现的是人的思想、回忆与红色丝线相结,即便远去却又被自己的心拉回的状态。

《from - into》 2004

从东柏林找来的700扇旧木窗和24张床,200㎡,5米高。现场请来24位女士睡在床上。

《Closed Daily Life》2005

《his chair》2005
750个旧窗户搭成的高6.5米、直径4米的塔,地面上铺满碎玻璃。

《house of windows》 2005

《Zerbrochene Erinnerung》2005


《Einsame Zelle》2006

《My Cousin´s Face》2006

《from in silence》2007

《from in silence》2007


《Trauma》2007


《Trauma》2007

《记忆》2008

《State of Being》2008


《traces of life》2008


《traces of life》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