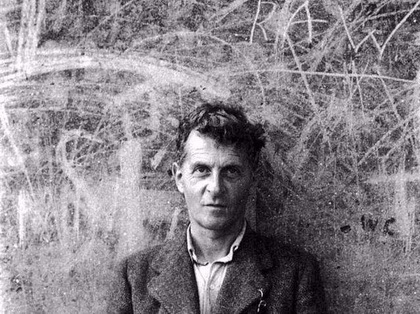旋转与升腾
——新经典主义文学的哲学视野对话
邓晓芒
2013年初,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研究古典哲学和现代文学的教授汉斯·费格尔(Hans Feger)博士来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作“两种文化:从艺术自律到文学的知识传播”的讲演,谈到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他先引述了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的观点:
哲学和艺术在历史上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如同分析者和歇斯底里者的关系。如我们所知,歇斯底里者去找分析者,对他说:“从我的嘴里说出真理,我在这里,而你,有知识的你,告诉我我是谁。”可想而知,无论分析者的专业的、敏锐的回答是什么,歇斯底里者都会让他知道,那样的回答还不算完事,她的在这里逃脱了偶然,一切还得重新开始,想要讨好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样一来她就把控制权拿在了手里,她就成了大师的主人。与此完全一样的是,艺术一直就在那儿,一直在向思想者提出“她是谁”这个无声的、捉摸不定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却由于她的持续的创造天赋和变幻莫测而对于哲学家关于她所说的一切感到失望……
歇斯底里患者想要的……是一个主人。她想要他者是主人,想要他知道许多事情,但还是不要他知道得那么多,乃至不相信她才是他的全部知识的最高价值。换句话说,她想要一个由她主宰的主人。她主宰,而他却不支配。
听到这里,我猛然想起我两个月前在北京和残雪的对话来。那次对话是我们所策划的整个关于哲学和艺术的对话的最近一次,在此之前,2011年的5月和8月还进行过两次。至于2009年8月和2010年4月的那两次,则已经收录在我和残雪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一书中了。这个系列的三次对话和前一个系列的两次虽然都是谈文学和哲学的关系,但侧重面有所不同。前一系列的侧重面在于为文学提供哲学的根据,而这个系列则主要是以文学为质料来建立一种新型的哲学观。但无论如何,上引拉康对哲学和艺术的关系的描述,都极为真实地再现了我和残雪这些冗长、纠结而又冲劲十足的谈话的现状。
当然,所谓“歇斯底里患者”不过是精神分析家的偏见,他们以为艺术家就是一种精神病态,虽然有创造力,毕竟是不健康的。我相信,他们如果见过残雪这样的精神强健的艺术家,就不会那样说了。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例如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就具备极为强大的理性,费格尔在讲演中也专门提到他,说他“发展出一种能动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一方面对被认为已经僵化的传统理性原则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也与那些宣扬‘对非理性的狂热崇拜’的信徒们(伯格森、梅特林克)保持着距离。”这种理性体现在一种“精确性”、尤其是“精确的感觉”上,在这方面,用穆齐尔的话说,“我们不是理性太多心灵太少,而是在心灵问题上只有太少的理性”。费格尔认为,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代表了西方文学中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最早可以追溯到席勒对哲学和诗所做的联结,这时,“艺术的观念化活动成为哲学的秘密代理机制——直至到了谢林那里,艺术被上升为哲学的喉舌器官和哲学的文献,因为它兑现了一种比概念思维更具优先性的真理和认识诉求。”的确,在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艺术直观已经超越了哲学的理智直观而成为体系的顶峰。于是,这样一来,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就几乎颠倒过来了。现在,哲学是处在歇斯底里者的位置,是它在向艺术要求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是它自己给不出的,但与此同时,由于它的精确性和科学性诉求,它又对艺术的无知不能满意。“浪漫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哲学文学的双重现象,在其中,诗与哲学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在这场精神革命之后,艺术变得高于哲学了:它甚至能够把那些被哲学作为至高之物加以谈论,但同时却又深知自己无法以认识的方式加以把握的东西也带到意识面前。”
看来,这种对拉康反其道而行之的观点正是费格尔自己的观点。通过会后与他的交流,我证实了这一点。就是说,表面上,哲学家在和艺术家的交往中是艺术家的精神病医生,他似乎能够给艺术家做出清晰的定位;但实际上艺术家才是哲学家的唤醒者,他(她)能够发掘出哲学家在潜意识后面所坚持的东西并将其置于危险的境地。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歌女士的娴熟的中德同声翻译,我向费格尔教授介绍了我与残雪的历次对谈的情况,他表示极感兴趣。我们约定,在适当的时候将进行一次三人对谈(由王歌女士当翻译)。我将这一消息通报给了残雪,她也感到很兴奋。
现在,我与残雪第二系列的这次对谈也已经整理完毕,计算字数,居然接近70万字,这使我们两人都吓了一跳。想想也是,我们涉及了太多的复杂的问题,哲学问题和文学艺术问题,都是高端的难题。三次探讨基本上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就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打通文学和哲学的哲学体系,如何从根基上把两个历来毫不相干、甚至相互冲突的领域结合在一起?与前一本书(《于天上看见深渊》)不同的是,在那里只是初步提出问题,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对自身的哲学根据加以搜索和定位;而在这里则是开始煅造一种新的艺术哲学。我们在选择术语、比较概念、划分层次上花了不少功夫,尤其是在新哲学的开端问题上(包括要不要一个开端的问题上)殚思竭虑。话题主要涉及中西哲学和艺术精神的比较,包括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代的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萨特和加缪,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中国的儒、道、禅,《易经》和《红楼梦》……所有这些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看他们能否对我们要建立的体系有所帮助、有所启发。这些对话有些是非常默契的,差不多是一点就通;但有许多地方是极其艰难的。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们两位对谈者各自的立场是如此的顽固,我们各从一个极端来就一个话题相互碰撞,各自都有说服对方的强烈愿望,但却很难被对方说服,因此时常会擦出思想的火花来。在哲学上,我自认为比她读的书要多,经常会引经据典,有时还会搞得她无法招架,只得退让;但她仍然在自己的基本立场上寸步不让,觉得我没有能够理解她。她极端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被表面的逻辑推理所迷惑。我觉得这恐怕正是一位艺术家所应有的素质。所以总的来说,我对她是比较迁就的,就连她的那种目空一切、狂妄不羁,我也认为总是有她的道理的。

话题中牵涉到中西比较的部分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哲学上,我历来是一个典型的“西化派”或理性派。这不是由于我的专业本行是德国古典哲学,而是由于我自身的长期底层生活,使我痛感中国缺乏理性精神的病状,就连我当初决心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也是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想要对现实社会施以疗救。相比之下,残雪在这方面就比我要淡漠得多,她考虑更多的是纯文学本身,因而比我更加抱一种古今中西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意识到这一点,我常常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锋芒收敛一点,隐藏一些,甚至还会帮她出点主意,比如怎么样把《易经》和道禅的原则吸收进她的体系中来。虽然我感到这样一来,很有可能会对我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新批判主义精神有所突破,但也不妨把这当成一场试验。因为这种突破如果成功了,也许意味着将我自己的观点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决不意味着我对新批判主义的放弃。我也曾想到过,那个更高的层次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但在没有达到那个历史阶段之前,还是应该在现有层次上多下些功夫,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不过有时又觉得,现在为未来作些准备也不错。我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进行这些对话的。我有一种预感,这种矛盾并不表明我的思考全无价值,相反,它是我的思想还充满可塑性和思想活力的表现。我并不想搞出一个“绝对真理”放在那里供人们景仰,我的新批判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对自身的批判,它一定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残雪从文学立场所提出的那些生动活跃的“质料”,无疑也具有将我的哲学从根基上加以震撼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她的确倒是有点像在对我的那种僵化和固定的倾向进行一种预先的提醒和治疗。当然,这本身也是我自己的哲学观点所认可的。
因此,本书的读者也许不能指望在书中读到什么现成的结论,而更多地是一种思想探索的历程。当一个艺术家想对自己为之献身的艺术进行一种哲学把握的时候,或者一般说来,当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想对自己的生命进行终极的定位的时候,他就可能陷入这种迷宫的探索之中。在这里读者可以期待的是,这种探索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而是由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代表女性思维的作家,另一个是代表男性思维的哲学研究者,在对话中进行一种身体力行的示范或演习。还是费格尔说得好:“认识不在于从现象之洞穴中上升到真理,而在于沉潜进第奥尼索斯式迷醉的昏暗的无分别状态之中。这是对真理之理解的一种逆转,亦即在不能把握真理的地方,人们离真理更近。”这正是我们这场对话所要达到的效果,即:恰好在问题扑朔迷离地展示出来让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在看起来怎么说都有它的道理的时候,就是最接近真理的时候。自从黑格尔以后,人们都对一个封闭的体系深恶痛绝,哲学家们纷纷宣称自己不搞体系,或者宣称自己的体系是开放的。但何谓开放?就是要在最高层次、最顶尖的位置上留下余地或空白。或者说,在其他地方都要把问题说清楚,但最关键的地方则不能说得太绝对,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被触及到。当然不再有其他问题留下来,而这恰好就是解答。”开放的体系总是留有自己的“缺口”,这种缺口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迫不得已,因为人毕竟不是上帝。人总是有限的,发展中的,总是要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余地。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有创见的新的观点也必然要从前人体系的缺口处入手,在弥补前人的不足之处的同时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所以全部的问题就取决于,能否发现前人体系的“阿基里斯之踵”?而这往往不是逻辑思辨的事,而是生命力和感悟力的事,在这方面,艺术气质通常比理论思维更为敏锐和有效。就连黑格尔那样坚不可摧的体系,当年也是由德国浪漫主义最早向它发出了挑战。当然,要将新的世界观建立起来,则还要做大量的理论工作。
就我自己而言,我很早就意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主要是针对着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一个是陈旧的思维模式;但对于传统的审美意识,我通常都是手下留情的,虽然也意识到其狭隘性和扩展视野的必要性,但却充分肯定传统的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不朽的价值。在《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1989)中,我对中西审美意识的融合充满期待,并提出了克服中西双方在艺术精神上各自的局限性的设想。但从逻辑上说,这种温情与我对传统的新批判主义态度其实是不能相容的,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它的其他方面,与伦理道德和思维模式(包括哲学思想),都是分不开的。因此,我的新批判主义如果说有什么缺口的话,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能自洽。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的哲学上的论战对手们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一点来对我进行反驳。倒是残雪作为一个艺术家向我提出的质疑,迫使我不得不全盘考虑我从纯哲学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评价。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对以往观点的放弃,而是对以往观点的完善化和提升。我经常强调的一个命题是:只有批判中国文化才能弘扬中国文化,在批判之前谈不上真正的弘扬。但毕竟也可以在批判的同时考虑一下未来的弘扬问题。与哲学比起来,文学艺术更具有时代的超前性,甚至永恒性。这正是文学能够成为我的哲学的缺口、也就是突破口的原因。但问题在于,突围以后怎么办?我与残雪的整个谈话,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进行初步的探讨,试着摆放了几块最初的基石。但这一切都还在未定。我们充分意识到问题的艰巨性。
尽管如此,我们对自己的努力仍然抱有某种自信。费格尔问道:“如果‘为对世界进行精神把握做出贡献’这个哲学的诉求转移到了文学中,那么哲学会变成什么呢?”他的回答是:“哲学现在也许会要求自己去做从前诗所做的事情:发明创造。那样一来,哲学就主要不再是解决问题,而是发明新问题。”但是,如果仅仅只限于“发明新问题”的话,那又如何能够“对世界进行精神把握做出贡献”呢?我觉得,回答还可以再积极一点,就是:通过解决老问题来逼出新问题,或者说,虽然没有能够解决新问题,但毕竟有了新视野,并由此使老问题迎刃而解。
但愿我们的对话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推进,虽然它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2013年2月25日,于武汉。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