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疆域:地缘的拓扑”展览现场
专访鲁明军︱疫情之后,去年的艺术事件似乎不值一提
鲁明军是活跃的艺术史学者,也是积极的当代艺术策展人。2019是事件频出的一年,世界格局、社会运动和科技的发展都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似乎改变了整年的艺术格局。在这个访谈里,鲁明军分享了他对艺术、伦理、策展和学术的诸多观点。
采写︱余雅琴
新京报:你可以先分享下2019年让您最为深刻的艺术事件是什么吗?
鲁明军:自新冠疫情发生后再回看过去的一年,似乎没有值得一提的艺术事件。
新京报:但可以想见,一定会有艺术家以疫情为主题做出艺术作品,这可能触碰到某些伦理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攫取他人的苦难,并一定程度上贩卖这种情感?有此一问也因为#metoo等运动席卷全球,艺术家的私德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被绑定公共性的话题,而与此类似的,动物保护或对少数群体的权益等问题都在一些领域引发了争议甚至抗议。美术馆、策展人或艺术评论的工作是否要考虑这些不同层面的道德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和平衡呢?政治正确是否如同一些人所说成为了“猎巫”式的泛暴力,成为一种新的规训?
鲁明军: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对于那些简单粗暴的体制批判也没什么兴趣,我关心的是集体的混乱和体现在某些人身上的分裂性诸如此类的现象。所以,我正在策划的新展览“恶是(Being of Evils)”的目的不是批判体制,发泄不满,也无意反思人性,劝人良善,而只是想以艺术的方式传递一个事实:恶何以是(being),恶以何是,以及恶,何以为恶?!
这些问题看上去很抽象,展览也不提供一个结论,但如果你到现场仔细看了展览,相信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的。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也许它只属于那一刻。但我觉得这样的展览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2017年,古根海姆的“世界剧场”展览活生生被动物保护事件扯到一边去了,结果媒体只关心动物保护,反而对展览本身很少有严肃的讨论。美国《十月》杂志发了一篇长文专门讨论这个展览引发的动物保护问题,让策展人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metoo所针对的可能更多是艺术系统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包括个人私德),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决定一件作品的好坏,也不能成为判断一个艺术家的绝对标准。除非,#metoo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并且真的释放出足够的政治力量,否则,政治正确并不能成为判断艺术的标准。很多优秀的黑人艺术不光是因为他是黑人,也不光是因为他关注种族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艺术实践本身所具有的力量。
政治不正确,不见得他不是一个好艺术家,也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作品。是个人都可以表达政治正确,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好艺术家。在欧美特别像纽约这样的城市的艺术机构大多会将政治正确作为工作的考量因素之一。但在国内,似乎很少有美术馆、机构会涉及这个层面的问题,而主要体现在很多留学回来的年轻艺术从业者身上,他们对此相对更加敏感。类似#metoo这样的社会运动是阶段性的,在某个时间点被引爆,本质上还是事件性的,所以很快就会被另一个事件所替代,也许,过一段时间还会卷土重来。但它对很多从业者还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古根海姆美术馆展览“世界剧场”现场
新京报:此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科技展、网红展铺天盖地,侧重社会、政治和历史议题的艺术作品逐渐少了,能再具体聊一下这个话题吗?
鲁明军: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观看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着艺术媒介,但或许是因为科技的力量过于强大,反而固化或抽离了人们复杂而细微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即便是很多带着反思和批判态度的作品,也最终陷入了一种无聊、乏味的套路中。
另外,科技展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不存在被审查的风险,有一些和官方的倡导是一致的。但事实上,这几年特别在欧美,反而很多原生性的、带有人类学色彩的作品又卷土重来。这当然跟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恰恰与那些冷冰冰的科技展构成了一种张力。国内这些年也有一批艺术家在做类似的实践,比如他们前往西北、西南边疆寻找灵感和素材,再比如像很多东北艺术家,本身的地域性就非常强。
当然,地域性也很容易被裹挟在身份政治里面,而我更加看重的还是原生性的力量和潜能。这就涉及你说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议题的作品,其实我说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是觉得这几年那种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作品越来越少见到,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好的艺术正是知识和经验抵达不了的那个部分。知识和经验相对容易表达自己的态度,也容易引发观众的回应和情感的共鸣,但同时也限制和束缚了艺术家的想象空间。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新京报:你之前也谈及中国当代艺术的空前发展却同时面对审查的张力,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召唤和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发展的困境呢?
鲁明军: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受众群很小,它原本就不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别说那些非艺术专业出身的专职审查人员,连留洋回来的北大教授都认为当代艺术是骗子,不过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西方也不见得所有人都理解和喜欢当代艺术。
在当代艺术系统中,资本市场扮演的角色是多层次的,不可一概而论。不能否认艺术市场存在泡沫,也不能否认资本毁掉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但资本也是推动艺术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17世纪,荷兰艺术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由市场的力量,明代的时候很多文人画家的作品就已经进入了市场流通,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已经和市场、商业完全裹在一起了,波洛克这些人很早就开始为佩姬·古根海姆站台了,再后来,资本成了艺术语言,出现了“波普”“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等这样的艺术流派和潮流,到今天还在延续。试想,如果没有画廊,没有博览会,没有资本家的支持,很难说艺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何况,即便是作为抵抗的对象,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说到这里,我想起去年惠特尼双年展期间,一些艺术家要求主办方惠特尼美术馆开除董事会成员武器(催泪弹)制造商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由于美术馆没有及时作出回应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多位艺术家提出抗议,并纷纷退展,这个展览也因此被称为“催泪弹双年展”。
后来,纽约有个画廊老板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这个矛盾,她说艺术家虽然在抵制和反抗那些政治不正确的大资本家和艺术赞助人,但事实上自有史以来,很多经典的艺术品都是高价卖给了那些“坏人”,那么她想问艺术家,你是情愿以3万美金的价格卖给牙医,也不愿意以10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那些“坏人”吗?这可能是我们今天遭遇的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
新京报:近期,你主要关注什么问题,研究的方向有什么转向吗?外部世界的变化也深刻影响到艺术创作,你如何理解艺术介入社会的行动,或者说,作为艺术史学者,你如何理解历史和艺术的关系。
鲁明军:年前在纽约的一家画廊策划了一个小群展“不可抗力”,展览是18号开幕的,20号在虹桥机场转机回成都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了钟南山院士公布了新冠疫情“人传人”的消息。展览原本不是应疫情的发生策划的,但没想到一语成谶。目前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展览,顺利的话,4月份开幕,跟这次疫情有关,但不是直接针对疫情,更不是抗疫救灾的展览,我更加关心的是疫情发生后朋友圈的各种情绪,所以想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关于“恶”的探讨。
关于艺术介入社会,我之前也提到过,今天的策展都偏向事件性,但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政治、社会、文化和知识、艺术的变化,我们越来越加难提供具有一定纵深度的结构性思考,事件替代了结构。这和艺术介入社会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是同构共生的。
当然,也不能否认当代艺术同时也是一种认知方式的探索,在这个层面上,它是非常前沿的,它超出了既有学科的界限。包括历史,其实也是当代的一部分,这里无论是考察一个历史真相,还是诉诸过去与当下的碰撞,关键在于能否从中激荡出新的政治和文化动能。反之,这样一种观念和认知也在启发着艺术史研究,二者并不矛盾。
在西方,不少杰出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艺术史学者同时也是当代艺术重要的评论家,比如列奥·施坦伯格,他原本是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史的,但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却是一部当代艺术评论集《另类准则》,这本书成了20世纪艺术评论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但在国内,直到今天,大多研究古代的艺术史家对于当代艺术还是怀有很多偏见,甚至包括一些年轻的艺术史学者。

▲《另类准则》
[美] 列奥·施坦伯格著,沈语冰、刘凡、谷光曙译
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新京报:你是学者也是策展人,还是艺术评论家,如何看待这些身份?在去中心化的后现代语境里,艺术评论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鲁明军:身份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觉得什么场合扮演什么角色,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一些基本的职业素质。这些身份之间也不矛盾,更像是一个互相滋养的关系。关于艺术评论的反思,是一个老话题了,很多人说艺术评论已经死了,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其实只是方式变了而已。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媒体化和事件化构成了今天艺术写作最重要的特征。这跟我们接受信息方式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期待某种结构性力量的出现,因为事件很容易流为泡沫。
所以,不管是在教学中,还是写作实践中,我反而更看重李格尔、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和瓦尔堡、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传统,包括格林伯格、施坦伯格以及后来“十月”学派的写作,这些看似过时了,但今天看他们的东西反而更有力量。
策展人和写作者其实是一样的,都同处一个艺术—知识系统,所以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和变化的可能。当代艺术的特质是不可概括、不可定义,它本身就是在不断地自我定义过程中,因此很难也无须描述发展状况。
但在国内,因为大多美术馆和艺术机构都不设策展部门,所以很多独立策展人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妥协做一些无效的重复性工作,没过多久,锋芒可能就没有了,不得不改行做其他了。即使在艺术系统内部,很多人对策展的认识还是很粗浅,也不见得有多少认可度,相比其他,策展在中国其实是一个还很不成熟的职业。
新京报:我同时也注意到你的学术视野很广阔,你如何看待国际思潮和动荡对艺术生态的影响,你同时关注地缘民族等问题,在这些变局中,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的位置都是尴尬而复杂的,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鲁明军:2018年初我在OCAT上海馆策划了“疆域:地缘的拓扑”展,这个展览针对的是反全球化浪潮,包括民族国家边界冲突、层出不穷的民族问题以及重新发现边疆等,涵盖的面很广,一方面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全球政治与艺术的变局。
很庆幸那个展览举办得很顺利,尽管还是有几件录像作品审查没有通过,至少这个问题当时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公开讨论。大概半年多后,好像就不让过度公开谈论民族、边疆问题了。同年底原本计划做一个东北亚的展览,后来也取消了。这里面,如果从艺术家的角度讲,他们的位置还是个体化的,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每个时代都有局限,而艺术家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局限。所以,不存在尴尬不尴尬。
的确,2017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世界剧场: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展览之后,整个西方美术馆系统看上去有点孤立中国,反而东南亚、日韩、中东、拉美的艺术家更受他们的关注,但这并不能影响国内艺术家们的实践和行动。
新京报:你的新书《目光的诗学》里探讨了不少关于媒介艺术,大众文化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重学术和现实的对应,你能谈谈这本书的学术脉络和构思吗?
鲁明军:这是一本评论集,主体部分是从这些年撰写的艺术家个案的评论中挑选的15篇短文,然后用3篇相对理论化的文字串了起来。三个部分之间有一条线索,第一部分讨论的是感知,主要是从基本的形式、视觉、物这样一个次序展开的;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政治与剧场;第三部分是空间、记忆与时间。书的副标题《感知—政治—时间》是出版社杨全强老师帮我加的,非常贴合整本书的构架。
这本书谈不上严肃的学术著述,只是一本评论集,但从选择个案到搭建结构,我想还是不乏当下的针对性,从物与感知(现代主义的重申)到正义剧场(全球化政治)和“世纪幻影”,它隐藏着一条普遍性的线索,也可以说是“特殊性vs普遍性”的三个不同维度。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自1990年代以来所遭遇的处境,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即将出版的另一本书《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换了一个视角,系统地清理了20世纪以来现代(当代)艺术运动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

▲ 《目光的诗学》,鲁明军著
上河卓远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新京报:2019年,你担任了CEF实验影像中心的学术顾问,策划了线上影展“野火”。你的选片思路是什么?又是怎么看待影像艺术在今天的现状的?
鲁明军:CEF实验影像中心是一个线上艺术平台,它的特点是短平快,所以更适合做一些“事件性”的小项目,这样持续下来,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事件流”,而“事件流”兴许就构成了一部独特视角的历史叙事。“野火”源自那段时间的香港街头,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带着一种反思的视角和态度去审视这个事件及其背后的复杂成因。但我并没有直接针对这个事件去选片,我更看重的是当下年轻人普遍的情绪。
关于影像艺术,我并不把它作为一种自足的媒介看待,我恰恰觉得,影像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后媒介”。它一方面植根于媒体生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对这个生态构成了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按照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的说法,这是一种“反馈的干扰”。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年初,我和孙冬冬策划了王兵的影像收藏展“重蹈现实”并就此写了一篇长文。
新京报:在传统电影行业,不少人对流媒体的发展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你怎么看流媒体在影像艺术领域的作用和价值呢?
鲁明军:去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颁给了美国黑人艺术家亚瑟·贾法(Arthur Jafa),他就是一个流媒体艺术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网上视频档案剪辑而成的。他的成名作《爱是信息,信息是死亡》最早是在通过视频网站发布的,后来因为有画廊的介入等原因,作品都是在美术馆通过大屏幕投影展示的,这样一种展示和在电脑、手机屏幕上看还是不太一样。贾法很看重音乐和声响效果,他的作品都很有煽动性,大屏幕展示明显更有力量。
去年年底,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关于图像的讨论会上,我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从“互联网与‘图像流’”“‘弱图像’与‘强图像’”“非虚构与后真相”“图像密度与政治共情”四个角度分析了贾法的作品,但最终我还是觉得它还是一种事件性的,甚至还带有一点反智主义的色彩。我本人很喜欢贾法的作品,同时也会看一些网上类似的小视频,我认为这其实是代表了今天大多人感知当下世界的一种普遍方式。不过后来还是受到了李洋等一些师友的“质疑”和“批评”,在不少人眼中,流媒体可能就是“病毒”。

▲ 亚瑟·贾法获得金狮奖最佳艺术家奖
新京报:“病毒”之说能不能再详细展开谈谈?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是,新技术和艺术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张力?新技术对艺术除了推动作用之外还有可能产生反作用?
鲁明军:“病毒”这个词,也是来自乔斯利特那里,比如他认为白南准的录像作品对于当时的电视机生态而言就是一种病毒。这里的病毒,在我看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于电视机代表的大众文化而言,录像艺术作为一种“病毒”,构成了一种反馈的干扰;其次,对于人类而言,电视机本身也可能是一种“病毒”。
我并不否认所有的新技术艺术,比如“法医建筑”这样的实践,其实也非常技术化,但问题是今天更多的新技术艺术恰恰暗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缺少了那种张力和批判性的介入。甚至还有将技术本身作为目的的,问题是这种未经技术领域检验的所谓新技术不见得是新的,很可能是一个老的技术。
我更关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与其他的关系。比如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帕梅拉·李(Pamela M. Lee)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探讨控制论与同时期冷战意识形态、现代主义的普遍性扩张等之间的潜在关系,这些问题反而更吸引我,而不是控制论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技术不是一个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自足的媒介,我宁愿将它视为一个相对比较松动的“后媒介”。新技术可能成为艺术,但它不是艺术的全部,更不可能成为我们判断艺术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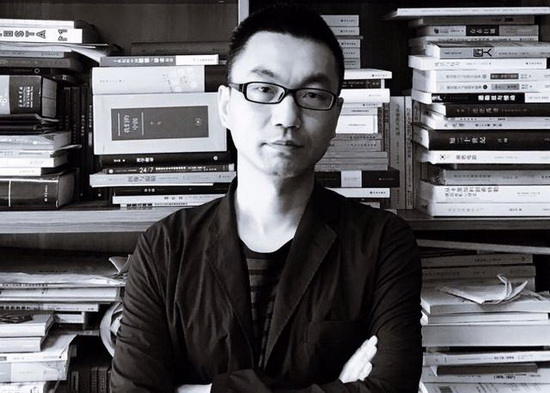
鲁明军,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策展人。剩余空间艺术总监。论文见于《文艺研究》、《美术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刊物。近著有《目光的诗学:感知—政治—时间》(2019)、《理法与士气:黄宾虹画论中的观念与世变(1907-1954)》(2018)等。近期策划“疆域:地缘的拓扑”(2017-2018)、“在集结”(2018)、“没有航标的河流,1979”(2019)等展览。2015年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2016年获得YiShu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2017年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ACC)。同年,获得第6届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CCAA)。2019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年度策展人奖(AAC)。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