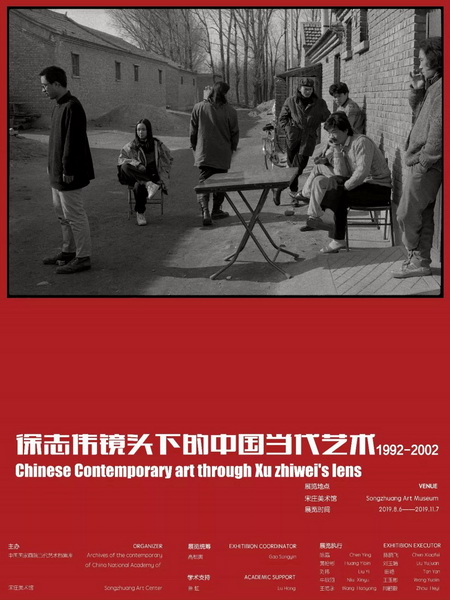编者按:保马今日推送的是鲁明军老师的《自我解放的歧途:“1999”作为一个叙述时域》,作者回溯性地审视了近2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曲折而胶着的历程,认为其始终无法脱离这样一个由全球化/后殖民所主导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但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寻找“自我的解放”是必由之路。作者将视点放在了90年代末、二十世纪初这个“最为模糊、最不确定也是最具张力的一个话语地带”,希望通过不同的“歧途”,在矛盾、复杂的现实中,看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内在联系与流动性。
文章系鲁明军新作《后感性· 超市·长征计划:1999年以来的艺术实践与社会变动》之“序论”,该作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 1989年5月,中国艺术家黄永砯(左)、顾德新(中)、杨诘苍(右)参加了由蓬皮杜艺术中心主办的展览“大地魔术师”;图为三位艺术家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前广场的合影
自我解放的歧途:
“1999”作为一个叙述时域
文︱鲁明军
1989年5月,三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顾德新、黄永砯、杨诘苍参加了由马尔丹(Jean- Hubert Martin)策划、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主办的极具争议的展览“大地魔术师”(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海外的展览。展览开幕不久,“天安门shijian”爆发,而年初“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肖鲁的“枪声”也一度被视为这一事件的预言。这一“突变”多少还是影响了三位艺术家的去留,黄永砯、杨诘苍(包括一同去参加展览研讨会的策展人费大为)选择留在了巴黎,从此开始了海外华人艺术家的生涯,顾德新则毅然选择了回国。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而此前不久,福山(Francis Fukuyama)已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文中宣告了“共产主义的破产”,并提出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两年后,苏联宣布解体,冷战结束,“后冷战”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体系。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逐渐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紧接着,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在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1993)上集体亮相,从此踏上了“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这一新的征程。同年,徐冰在北京翰墨艺术厅实施的表演《文化动物》(1993)已经带着反思的姿态回应了这一新的时代的来临。可从此,真正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代名词的是“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它们与“告别革命”、“后革命”、“反崇高”、“反英雄主义”这样的知识界、文学界的论调共生为一个新的时代的普遍特征。
如果说“大地魔术师”是一个全球化的征兆,“后冷战”或“后八九” 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终结论”及其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的话,那么1996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是对于这一“普遍乐观主义”的一次全面诊断和批判性的反思。从另一个角度看,“后冷战”或“后八九”也是“后殖民”的开端,而“大地魔术师”则因此成了“后殖民”的一个预言,甚或说它本身就是一次“后殖民”的实践。诚如《第三文本》(Third Text)的创办者兼主编拉希德·阿瑞安(Rasheed Araeen)所说的:“像马尔丹这样宣称自己的‘善事’,不仅不会质疑反而是在肯定西方的支配,并否认了那些被排斥的文化质疑现有权力架构和自我解放的能力。”[1]就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发表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汪建伟、冯梦波两位艺术家应邀参加了第10届卡塞尔文献展,这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由卡瑟琳·戴维(Catherine David)策划的这届文献展之所以成为文献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因为她将其从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主义趣味拉到了全球政治、社会、文化的框架中,以此直面其中的差异、变动及其复杂性。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开始思考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对于社会和经济的破坏性”[2],无论国企改制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还是签署世贸协议,凡此皆被认为不仅加速了私有化的进程,也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处境。同年,《天涯》杂志发表了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3]一文,在知识界掀起了持久的“左右之争”,亦开始了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整个现代性进程及其不平等的霸权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可即便如此,伴随“新左翼”、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的依然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野蛮入侵和全面渗透,乃至连反全球化本身也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浪潮。这期间,《读书》杂志刊发了一系列有关“后殖民”与“全球化”的文章,就此展开深入的论辩。[4]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11月10日,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中国亦正式加入了WTO。一时间,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也正是这些事件,促使了当代艺术的合法化,甚至成了政府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此前(最早可以追溯至2000年由文化部批准、上海美术馆主办的第3届上海双年展“海上·上海”,但也因此忽视了展览真正的主题,即关于“一种特殊的现代性”的讨论,其中“海上”自然是全球化的象征,而“上海”所指的就是本土和在地)当代艺术在中国则一度处在不合法或“半地下”状态。而几乎同时,在德国汉堡火车站美术馆,由范迪安、侯瀚如策划的展览“中国在此时”高调开幕。接着,在文化部的推荐下,王功新、颜磊、邱志杰、卢昊及汪建伟等参加了第25届圣保罗双年展(2002)。其中一个根本的变化是,当代艺术已成了政府行为——尽管不久前文化部还下文严禁以“艺术”的名义搞丑恶行为。相形之下,大洋彼岸似乎更是“动荡不安”:“9·11恐怖袭击事件”直接导致了美国右翼的反弹,美国趁机发动了“反恐”战争。一年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一书也因此备受关注,两位作者将全球资本主义及其跨国体系视为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一个新的“帝国”形态[5]。“9·11”无疑给了“帝国”致命的一击。这期间,黄永砯的《蝙蝠计划》不失时机地被卷入其中。

▲ 黄永砯,蝙蝠计划Ⅱ
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南海上空与一家中国军用飞机相撞,中国飞机被撞毁,美国侦察机降落在海南岛。5月底,中美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拆除该架EP-3侦察机运回美国。与之同时,黄永砯应法国策展人阮格琳贝(Alberte Grynpas Nguyen)的邀请,参加由中法合办、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承办的“被移植的现场:深圳第四届当代雕塑展”。期间,在从巴黎飞往上海的途中,他看到了EP-3侦察机拆除后运回美国的消息,启发了他《蝙蝠计划》的方案。然而,就在制作作品的过程中,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突然介入,要求停止该作品的制作。参展艺术家们公开提出抗议,但未能挽回局面。2002年,首届广州三年展邀请黄永砯参展并希望展出《蝙蝠计划》,黄永砯提出《蝙蝠计划Ⅱ》的方案。可是,在制作和安装进入尾声的时候,美国领事馆通过中国外交部开始介入,要求撤除作品,最终作品还是被撤走。直到2003年6月,《蝙蝠计划Ⅰ》和《蝙蝠计划Ⅱ》的草图、照片、文档及模型,在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紧急地带”单元展出。[6]

▲ 黄永砯的《蝙蝠计划Ⅱ》受到美国领事馆的干预后,部分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发起公开抗议,以示不满。
这一始自新闻的艺术计划结果演变成了连锁的政治事件。飞机在此显然是象征性的,它直指美国的霸权,以及既有的国际政治秩序。拆解的行为亦不乏隐喻,艺术家认为是对权力的解构,而在我看来,它也巧妙地暗示了权力对于既有秩序的破坏。艺术家并非是有意挑衅,尽管他认为艺术就是政治,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将艺术政治化。事实是,当他的实践屡屡被中止时,意味着艺术本身已经被政治化了。更重要在于,以往涉及审查或自我审查,只是限于国内的体制和政治现实,然而,黄永砯的实践将我们拉到了一个国际的视野,法国领事馆的施压和美国领事馆的干预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支配体系和结构的不平等。应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是迫使黄永砯的艺术实践遭到中止和取消的重要原因,而他最初的计划和行动也巧合地预示了几个月后的这一事件。
2002年,由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策划的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即是“后殖民与全球化”。展览对文化的本土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全球化认知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中国艺术家冯梦波、杨福东应邀参加了展览。也是在这一年,赵汀阳发表了《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一文,作者用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尝试取代“帝国”,并论证了其作为新的世界制度的可能性。[7]次年,汪晖完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研究,在这部耗时十余年的著作中,作者从清帝国传统与近代国家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内外关系的模式,探讨了现代中国如何超越西方“国家-帝国”二元论及其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进而从帝国(准确说是清帝国,它不同于与资本主义密切关联的西方现代帝国)自我转化为一个既是帝国也是民族-国家(或者说,既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及其儒学普遍主义的内涵。[8]同年底,《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对甘阳的访谈《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甘阳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格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能否自觉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中,借此,他重申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基于保守主义的视野,驳斥了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学界的种种“西方化普世文明”的幻觉。[9]随之而生的“(古典)政治哲学”和儒学的政治转向成了“新保守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标志。是年,栗宪庭策划的群展“念珠与笔触”在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和大山子艺术西区开幕,六年后,高名潞策划了大型展览“意派”(北京今日美术馆,2009)。意味深长的是,两位曾是85美术运动的灵魂人物,是前卫艺术在中国的主要推动者,而此时却都试图通过回溯中国历史传统,重新理解并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方式。期间,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2002)和河清的《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2005)先后出版,《美术》杂志也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挞伐并全面否定了当代艺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艺术体制(包括画廊、美术馆、博览会等)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当代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中,市场也由此开始主导艺术系统,其标志就是以北京798、上海M50等为代表的各地艺术区的兴起。在此期间,几乎所有以反市场、反资本为名的批判、反动,本质上依然依附于这个系统,甚至是为了更正确地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迄今亦未走出危机的泥潭,而近年来愈发猖獗的ISIS和种族冲突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全球性的危机。金融危机导致2005-2007年间中国艺术市场的“狂热胜景”瞬间不再,好在并没有触及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根本,加之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包括汶川大地震,反而诱使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再次抬头,并引发了有关“中国模式”,以及“和平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之间的论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亦不可忽略的是,伴随经济崛起的除了民族自信以外,还有日趋严重的社会失衡、阶级固化以及普遍的心理焦虑。这些内外交织的冲突、矛盾及困惑再次引发了关于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争论虽然无果而终,但至少表明一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同时脱节,意味着旧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似乎无法解释今天的世界变局。无论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还是激进或保守,都已无力应对这样的状况。[10]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开始将目光从过去的沉思转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直到2008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它标志着“90年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11]就像同年徐震的行为、装置《饥饿的苏丹》对90年代初同名事件的“重演”,我们已经很难用既有的概念框架简单地去概括它,它含括了“全球化”、“后殖民”、“新殖民”以及内在的“阶级眼光”等交织着多重冲突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可定义性。

▲ 徐震,饥饿的苏丹,装置、行为、摄影,2008;图片来自香格纳画廊网站
是年,由高士明、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张颂仁联合策划的“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三届广州三年展”意图彻底彻底告别“后殖民”这样一个艺术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的叙述框架和感知体制,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种种“意识形态的现成品”和“未经消化的现实”[12],但有一点暧昧的是,它看似是意图重返艺术和政治本身,回归作为艺术的政治,可一旦植入当时的语境,似乎又暗藏着一个“国家主义”的叙事。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早就说过:“全世界都是后殖民的。”[13]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与后殖民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因此,与其说是“与后殖民说再见”,不如说是“与全球化说再见”。甚或说,这其实只是一种话语姿态。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即便是今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中国”,也似乎很难给出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界定,它既“不卑不亢”地主动参与全球化的游戏,但并不完全受制于此,或是完全依循于它所谓的普遍性逻辑,更没有去扮演一个狭隘的抵抗者的角色。它有着特殊的国际地缘政治处境,也有着复杂的、多层次的内部结构。同样是就此,萨拉·马哈拉吉的论述似乎更为审慎和准确,在他看来,所谓“与后殖民说再见”并不是——也不可能——彻底告别后殖民,而是为了给“后殖民”这个概念增加一种弹性,以使它能够与更多的现实发生关系。[14]可即便如此,当我们在树立文化本位,强调差异的时候,已然自觉地将自我本质化,同时也将全球化或西方本质化。
对于这段反复被提及的历史,我们其实并不陌生。然而,之所以在此重新编织这段曲折、胶着的历程,是因为近20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无法脱离这样一个由全球化/后殖民所主导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然而,无论是主动选择进入,还是被迫卷入其中,对于大多艺术家、策展人而言,归根结底,他们念兹在兹的还是自我的解放,只是道路不同而已。而这迫使我不得不再次回到90年代末、新世纪初,在我看来,基于“艺术(文本)—思想(亚文本)—行动(事件)”这一系统性的观察和思考[15],这一时域恰恰是其中最为模糊、最不确定也是最具张力的一个话语地带,今天我们所遭遇或面临的诸多问题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有所显露或处在萌芽之中,更重要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框架,或是暗地将其作为一个反思和否弃的对象。
1999年上半年,由吴美纯策划、邱志杰撰文的“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和由徐震、杨振中、飞苹果(Alexander F. Brandt)联合策划的“超市”这两个实验性展览分别在位于北京和上海的两个临时空间举行,40余名年轻的艺术家参与了这两个展览,且如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除了几位作为策展人的艺术家外,还如刘韡、杨福东、郑国谷、阚萱、张慧、朱昱、王卫、孙原等)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远在伦敦的卢杰也刚好完成了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University of London)的毕业策划案“长征计划”。三年后,由卢杰担任总策划、并与邱志杰共同执行策划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正式启动实施,项目至今还在继续。曾参加“后感性”和“超市”的部分艺术家也都参与了“长征计划”。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卢杰当时所在的学校金史密斯学院也是与“后感性”密切相关的英国YBA(Young British Artists)成员的大本营,大多成员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 “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参展艺术家合影,1999;图片由王卫提供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展览/计划作为讨论的重心,首先是因为它们恰好同时发生,虽然各自有着明确的不同的针对性,但如此出现并非巧合。“后感性”针对的正是被国际艺术体制所吸纳或是有意迎合某种国际眼光的本土观念艺术,而意图回到自由的直觉现场和感官实验中,包括后来系列临时性的剧场展演,实际也是为了对抗国际艺术体制裹挟下的僵化的、恶性竞争的展览制度;“超市展”关注的是如何以个体化的方式介入日常经验和市民生活,如何通过新的展览语言,尝试突破既有的那些条条框框的体制性约束;“长征计划”针对的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系统和展示制度,一方面试图提供一种鲜活的、流动的、扎根于民间色彩和地方生态的艺术创作和展示模式,以及艺术史和理论书写的跨媒体的新模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重新面对和整理百年来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生活的经验。[16]三者并不适应和契合当时的整体语境和时势,也不是后者催生的反向力量,毋宁说是一种自我开启的道路。而且它们之间亦不乏张力,每一个实践及其脉络甚至落实到艺术家和具体作品身上,同样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 陈羚羊,《蜜》(“后感性:异形与妄想”现场),装置,尺寸可变,1999
图片由邱志杰提供

▲ 郑国谷,《前卫艺术加油前进》,“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展览现场表演,1999
图片由王卫提供
其次,作为“开端”,1999年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时域。在它们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零星实验,只是到了1999年,才汇聚成为一种力量,而且,它们的实验不仅是持续性的,还深刻地影响了诸多参与艺术家个体后来的实践。在北京,“后感性:异形与妄想”之后,他们先后策划实施了“后感性:狂欢”(2001)、“后感性:报应”(2001)、“后感性:内幕”(2003)、“后感性:忐忑”(2004)、“后感性:黑白动物园”(2006)及“联合现场”的系列实验(2005)等剧场表演。不过到了这里,他们也已渐趋于解散了,而作为其中核心人物的邱志杰的志趣也已转向了“总体艺术”。这些实验成为上世纪末以来临时空间、自我组织的一个典范。同样,在上海,“超市展”后,徐震、杨振中又持续策划组织了诸多类似的展览,如“有效期”(2000)、“范明珍和范明珠”(2002)(2002)、“24:30”(2002)、“62761232快递展”(2004)等以及“比翼艺术中心”和“Art-Ba-Ba流动空间”中的系列展览,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观念层面,“超市展”对于徐震后来系统性转向的影响,包括“香格纳超市”(2007)、“小平画廊”(2008)以及“没顶公司”(2009)、“徐震品牌” (2013)、“没顶画廊”(2014)、“徐震超市”(2016)、“徐震专卖店”(2016)等都与“超市展”密切相关。展览实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超市”成为新世纪以来艺术全面市场化的一个征兆。“长征计划”意在重提退出视野或被“中西之辩”(如2000年前后批评界关于要不要打“中国牌”的争论)取代了的大众与精英、传统与现代这两层关系。[17]这里不存在中西对立,也不存在“左右之争”、“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全球化vs本土化”这样的冷战或后冷战思维,更不是退守到一个“保守”的状态,毋宁说是为了打破既有的教条的认知框架,重新探寻变革的据点和行动的道路。当然,它也是国内最早有关人类学与社会学模式的展览语言(包括对民间力量的再发现)最早的尝试。

▲ “超市展”现场,1999;图片由杨振中提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们的观念与实践既深嵌在90年代末的艺术与文化政治语境中,同时又并不受制于当时的语境,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种自我抽离或否弃的方式,意图提供一个朝向未来的批判性实验和创造性的话语。按照汪晖(包括其他知识分子)的叙述,1999年本身就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年。3月24日,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这引发了北京及其他城市的大学生、市民阶层抗议游行,“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vs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以及人权应否或能否凌驾于主权也因之成了思想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失业、下岗、制度性的和日益国际化的腐败、贫富分化、环境危机和其他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其不仅击破了任何关于现代社会的天真幻想和理论幻觉,也表明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要不要加入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内在问题。[18]同年,爱德华·W·萨伊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的中文版出版。我们知道,这一年蔡国强的《威尼斯收租院》获得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而两年前栗宪庭发表的《我们做不做国际艺术拼盘上的“春卷”》一文也因之再次引发争议,文中写到:“春卷不需要发言,也不需要被理解,只要摆好东方风情的姿态就好了。”[19]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后感性”,还是“超市”,都没有被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纷争所裹挟,他们更没有刻意地去迎合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恰恰是在这一复杂的情境中,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从既有的艺术、文化、社会以及政治或意识形态体制中将自身解放出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触及这些问题,而是以更加微观和个人化的视角和语言方式碰触或进入现实及其复杂性。他们所贡献的不是某种既定的政治姿态,而是一种流动的、含混的、在变的感知和思考。这也是“长征计划”实践的理念,尽管方式、取径有所不同。诚如卢杰所说的,无论是历史上的长征,还是今天的“长征计划”,都包含着中国对西方的想象、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中国对“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的想象等。[20]它不再是“冲击—反应”的逻辑,也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若按汪晖所说,“这是一种在多重视线中同时观看他者和自我的方式:观看别人也观看自己;观看别人如何观看自己;从别人的视线中观看自己如何观看别人,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个观看过程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在相互发生关联,并因为这种关联而发生全局性变化的过程中展开的。”[21]
2003年前后,随着艺术系统的建立,和美术馆、画廊和博览会的兴起,艺术家们纷纷进入其中,但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受制于资本支配,或完全依从于全球艺术市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些带有集体或小组特征的实验难以为继的原因所在,反而是资本和体制为艺术家提供了能够充分发挥个体能量的平台和条件,于是他们选择了从一个“正确”的临时群体中出走,进入了另外一个“不正确”的系统。按照刘韡的说法,市场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回避这个事实,就变得不真实,也自然不能触及现实的痛处和爆点。[22]自2000年以来,他几乎所有的实践皆植根于全球化背景下北京的城市化运动,来源于都市景观和城乡结合部的日常生活经验和阶级化的美学形态,而他的作品也一直深受市场的认可。相比而言,在这方面徐震的波普化取向和系统性实践无疑更为彻底。自2009年成立“没顶公司”以来,他大量的实验和创制都涉及到商业和资本,而在他看来商业化本身就是2006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最为真实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徐震的实践也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艺术系统最为适切的一种症状式表征,或称其为一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23]

▲ 徐震,《小钱(人民币坦克)》,一元人民币纸币,23cm ×50cm×17 cm,2011-2015,没顶公司出品;图片由没顶公司提供
2016年11月初,也就是在“西岸”、“021”两个博览会期间,一周之内仅上海本地就有大大小小60余个展览开幕,比起空间稀缺、展览匮乏、市场阙如的90年代、新世纪初,这几乎是一个“疯狂”的事件。“徐震专卖店”就是在此期间开业的。在这里,它既是其艺术系统和产业扩大化的一个举措,同时也是对于周边这样一种艺术商业情境的巧妙介入,其态度虽然是模糊的,但也因此,在资本内部构成了一种干预。[24]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长征计划”与“长征空间”的关系,“长征计划”最初的动因之一即是批判性地反思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艺术体制,但后来转向画廊“长征空间”后,意味着又成为这一艺术体制的一部分。对此,卢杰不以为然,他认为二者并非矛盾,“长征空间”只是“长征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当然二者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暧昧”关系中,才可产生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话语和政治。

▲ “长征队伍在昆明塔特林式建筑前”,2002;图片由长征空间提供
自1989年后,意识形态的“牢笼”一直统御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念和实践,全球化主导的世界体系以及艺术系统中,艺术家们唯恐政治不正确。这一度作为他们艺术能动性的主要来源,并构成了一种既定的主体性机制。而无论是“后感性”、“超市”,还是“长征计划”,它们并不是否认这一世界体系和艺术现实,而是希望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歧途,重新回到艺术的主体以及作为艺术的政治主体,在矛盾重重、荆棘丛生的现实中,重新建立与全球政治、文化、社会及其变动的内在关联。与之相伴随的不仅是艺术的解放,也是政治的解放,更是自我的解放。
注释:
[1]转引自佚名:《大地魔术师,当代国际艺术大展的领航者》,“99艺术网”,2015年5月1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6be7890101ja25.html。调用时间:2017年5月1日。
[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37页。
[3]同上, 第58-97页。
[4]参见《读书》杂志编:《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5]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2003年10月,《蝙蝠计划Ⅲ》在参加由顾振清策划的“左翼”展览的过程中,同样被要求中止和取消。两年后,《蝙蝠计划Ⅳ》以“不公开”的方式参加了由高名潞策划的《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展览。参见黄永砯:《蝙蝠计划:备忘录》,载菲利普·维赫涅(Philippe Vergne)、郑道炼编:《占卜者之屋:黄永砯回顾展》,毛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76-79页。
[7]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 第一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821-829页。
[9]甘阳:《文明 国家 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15页。
[10]参见鲁明军:《对话汪晖》,北京: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2016年4月3日,未刊稿。
[11]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罗岗:《“短暂的90年代”与当代文化研究的使命》,“保马”微信公众号,2015年6月2日。
[12]高士明、萨拉·马哈拉吉、张颂仁:《主体概念:与后殖民说再见 》,载:《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三届广州三年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第3页。
[13]Gayatri C. Spivak,“Gayatri Spivak on Politics of Subaltern ”, Socialist Review, Vol 23,No.3(1990), p.94.
[14]广东美术馆编:《第三届广州三年展读本(1)》,澳门:澳门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第195页。
[15] 参见曾念长:《断裂的诗学:199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16]卢杰、邱志杰:《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前言,2003,未出版。
[17]卢杰、邱志杰:《策展人的话》,载:《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2003,未出版。
[18]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第389-488页;鲁明军:《对话汪晖》,北京: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2016年4月3日,未刊稿。
[19]此文系栗宪庭在台湾国立美术馆举办的“世界华人策展人会议”(1997)上的演讲。
[20]卢杰、邱志杰:《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前言,2003,未出版。
[21]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时位置(之一)》,2017,未刊稿。
[22]广东美术馆编:《第三届广州三年展读本(1)》,第203页。
[23]Xiaorui Zhu-Nowell(朱晓瑞) , Capitalist Realism,2017,未刊稿。
[24]同上。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