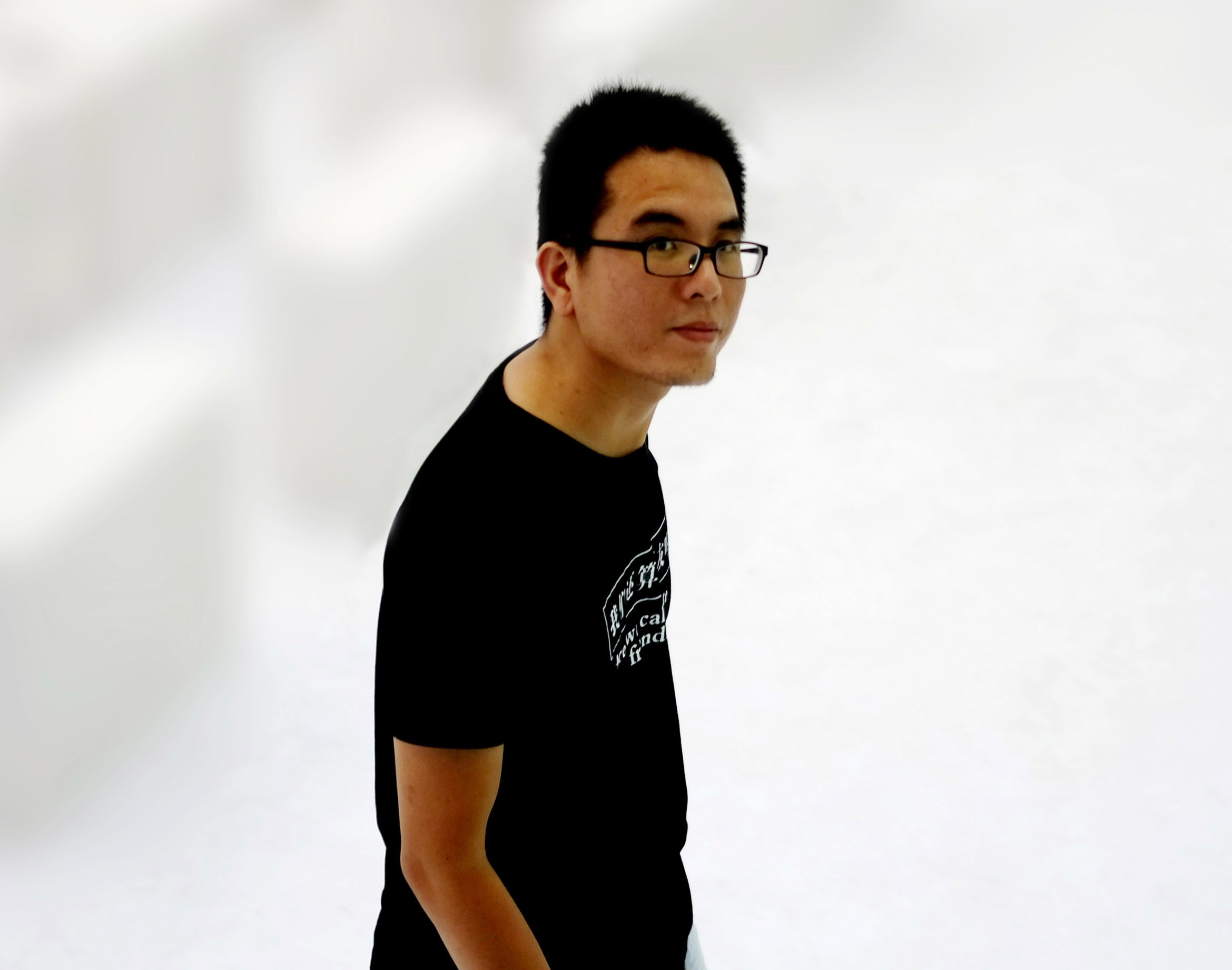黄然(Huang Ran)
简历
黄然,1982年生于四川西昌
目前在北京和伦敦工作
2004年他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英国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并获得纯艺术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200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Goldsmiths College(英国)纯艺术硕士专业;
2009年,黄然成为由欧洲媒体艺术家进驻计划(EMARE),欧盟文化部,以及英国艺术委员会共同支持的16位艺术家之一,在英国和德国完成了艺术家进驻项目。通过这次机会,黄然把自己的开放创作推进到更为多元的层面,开始尝试和电影语言的复杂性相交集。
联展
第13届Videonale,德国波恩美术馆(2011),“瑞信今日大奖”,今日美术馆(2011),“超有机”中央美院美术馆双年展,中央美院美术馆(2011),“ Videonale巡展”, 英国格拉斯哥现代艺术馆(2011),第42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艺术电影”单元 (2011), “北京之声:在一起或孤芳自赏”,佩斯北京(2010), “Projectables”第7届Mercosur双年展,巴西 (2009),“MOVE”, Werkleitz媒体艺术中心,德国(2009)等。
艺术家作品

黄然《愉悦悲剧》影像截屏,14'48,2010
2010年,黄然在798空间站展出他的新作《愉悦悲剧》,在这件时长14分56秒的视频作品中,黄然有目的地利用电影语言,把神秘故事和历史编撰在一起。通过引人入胜的“唯美”画面,探究了爱、色情、性别、暴力以及死亡间某种不确定的共谋关系,表现了在当代美学中无解的混乱状态,极具诱惑力和欺骗力。电影的模糊性则让观众在质问图象内容所引发的畸形感受的同时,也在怀疑图象在美学“质量”上的完美所带来的愉悦反应。某种程度上,观众需要自行编撰故事,引出自己的欲望。黄然在这里制造了一个沉醉状态——对合法化的当代美学不合理性的渴望。

黄然《美的,让人渴望的,卓越的,邪恶的》丝网印刷,115x85cmx2,2011
同时展出的还有两组(每组40张)幻灯片,题目 “美的,让人渴望的,卓越的, 邪恶的”,每单张间隔2秒,循环投影于展厅的墙上。从观念性的策略出发,黄然把“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爆炸灾难的录像片段以及一系列19世纪医学类版画进行了后期加工,并转印到了反转片上。这一行为把图象放置在了录像和静止画面之间,干扰了彼此的时间概念以及感官上的延续性。反转片整体上描述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灾难事件,但是单张图片本身却在传达一种残酷的现实美感。这让美学“质量”上的完美性同“畸形”概念彼此形成反差的同时也相互勾结在一起。

黄然《假动作逼真》,2009,5’56”,Red One Digital转普通DVD
在2009年事物作品《假动作逼真》(时长6分钟)中,两位复古装束的男性拳击手在一个抽象的黑暗空间里上演了一出没有身体接触的拳击比赛,整个电影都没有做现场录音,两人似乎在无声地打斗,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从70年代的色情影片中截取的男性的呻吟声被有节奏地嵌入到了打斗中,和各种暴力动作结合起来,取代了运动中的喘息声。有目的地出拳和这种尖锐的喘息声同步模糊了视觉上单纯的暴力感。电影的结尾在两人长时间的亲吻和令人眩晕的两个场景间交错着。伴随着一段同样是从70年代色情电影中截取的极具庸俗趣味的情爱音乐。
这种被压制的性关系和男性彼此间的混乱关系和模糊状态揭露了隐藏在当前可视暴力层面下的某种亲密关系,暗示了原本对立的极端点间的相互勾结和纠缠,色情和暴力的勾结试图制造一个伦理上的混乱状态,并挑战当代政治美学上的无解状态,让判断本身超越了好与坏的清晰标准,在《假动作逼真》所营造的错位世界里似乎已经没有事物可以保证自身的清白状态了。

黄然《下一轮才是真实的生活》,高清DVD影像截屏,27'37,2009
同年,黄然创作的另一件作品《下一轮才是真实的生活》是一部长达27分37秒的Video作品。 影片中,三位中年男性角色轮流进入画面,彼此间相互传递并共享着同一块泡泡糖,上演了一个无休止的接力——轮流吃同一块口香糖。随着泡泡糖的甜味被一点点消耗,这种循环的接力行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对泡泡糖原本的甜美味道的反感,并且这样的反感随着接力的继续在不断的加强。
吃泡泡糖这样一个行为在根本上否定了“吃”的功能性——因为吃在本质上是为了给身体机能储存能量。然而,对泡泡糖的无休止咀嚼却是以消耗身体机能为前提,在精神上提供一种转瞬即逝的放松感及愉悦感。
三人之间的这种接力暗示了一个对当代文化以及政治尴尬状况的反讽。政治消费和文化消耗行为上的高度饱和状态,在非常短暂的层面上,持续地激发着某种朝生暮死的,带有压制性的诱惑力, 以及对于未来的种种甜美幻想。然而, 与此同时,这种别无选择的,压制性的高饱和接力行为也暴露了当代文化以及政治行为在本质上所无法避免的,悲观的,令人反感的陈腐和乏味。

黄然《破坏性的欲望,镇定剂,遗失的清晰》高清录像转蓝光DVD,22分钟,3/5,2012
黄然——“破坏性的欲望,镇定剂,遗失的清晰”
北京长征空间于2012年3月16日推出代理艺术家黄然个展——“破坏性的欲望,镇定剂,遗失的清晰”。这也是自2010年合作以来,黄然在长征空间的首次个展。(此展览中的部分作品也将参加2012年5月的弗瑞兹纽约博览会长征空间展位的“黄然个展”)
这次展览,黄然将继续回应自己对于美学和道德的无解坍塌所产生的诱惑和沉迷状态的兴奋与不安。此次与展览同名的电影新作《破坏性的欲望,镇定剂,遗失的清晰》描绘了一对青少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深藏在背后的历史中的某段残暴线索所勾结在一起。在尝试安全化某种转瞬即逝的“美”的同时,也暗示着某种字迹模糊的体验,孤独,残忍,下流,短暂,纯洁。乔装的宁静画面,自我矛盾地试图同精神错乱以及狂热的混乱状态发生关联。这种来自内部本身的矛盾取代了关于违反戒律的实体图像,在一个极端可疑的浪漫主义及表现主义色彩下,挑战着我们道德美学的边缘。电影释放着同我们自身的美学价值以及道德意志的某种不可能性进行交流的冲动,但是同时也在从内部否定这种内容上的交织。它在提供一个适合我们当代趣味的貌似合理的美丽图像的同时,也在背后隐藏着其本质上的揶揄——被自身极力否定的固有不安全感所保护着。
展览的另一部分由不同尺寸的装置/雕塑作品构成。其中一件的题目是《意志的软弱,对社会的恐惧》。在这里,"机会"和"冒险"共同扮演了一种阴谋,放任了那些难以忍受的物理安全感同虚无的心理不安全感之间的私通。在对材料固有语法的消耗过程中,黄然把漠不关心的笑,软弱,恐惧,自信,爱,意志等诸多人类条件转化成了片刻的冷酷物质化过程。
黄然的创作并不寻求吸附于哲学或者批评思考以便从中思考我们自身的条件。它更像是某种被挑战的欲望本身,满载着可能性但是也处于对自身不经久的安全感的恐慌之中。他的作品并不追求理解上的允诺或托辞,“它在尝试验证某一个转折点,在那里我们自愿被安全化后的美学不安全感所阉割。如同身处宗教狂热,我们选择的是某种美学实用主义而不是理解那与生俱来的缺陷和无解。艺术从未真正意义上关心过某事某物,它所真正在乎的或许只是关心事物时所激发的片刻沉醉情感和体验。”黄然说。



黄然《与生俱来的敬畏和恐惧之中的爱》有机玻璃缸、4台千斤顶、食品油、全净水,120x120x150cm,2012

黄然《消耗不能同时成为自治的和有活力的》,钢板、船用发动机、水、黑色墨汁,180x110x90cm,2012

黄然《或许我们只是在乎关心事物时的感觉》,Stainless Steel, Bubble Machine, High-Voltage Generator
每件:2010mm x 3015mm x 110mm (共4件),2013

黄然《救赎的约束性同仍然活着的事物相冲突》,纸本丝网印刷,108.7x76.9cm,2012

黄然《寻求中断和自我意识》纸本丝网印刷,108.7x76.9cm,2012

黄然《压制解放了被压制的欲望No·1》Inkjet Print, Metallic Ink on Paper,65x45cm,2011

黄然《压制解放了被压制的欲望No·7》Inkjet Print, Metallic Ink on Paper,65x45cm,2011

黄然《压制解放了被压制的欲望No·8》Inkjet Print, Metallic Ink on Paper,65x45cm,2011


《压制解放了被压制的欲望》
访谈:青年艺术家黄然谈新作及其他(节选)
ARTINFO:你似乎一直都在表达一系列相关的概念与意象,只是借由不同角度切入。那么这两件作品间的关联、以及不同的切入点分别是什么?
黄然:要说关联的话应该是观念层面上的,是图像背后的想法。二者都关乎我对于道德无解坍塌所制造的诱惑和沉迷状态所持有的兴奋与不安. 这些作品都在尝试将不安全感安全化,而非消除不安全感。而我不太会去强调一个展览中不同作品间的外在的关联性,那只会让我觉得作品是不完整的。
从视觉上看,二者之间的差别很大,包括每一个媒材的语言也是不同的,而我对待不同媒材要求的是不同的策略。电影语言中主要是在图像(image)上,而图像又涉及到“图像的含义”(the meaning of image)与“图像的现实状态”(the fact of image)两方面,所以我做电影作品通常是在最终直观呈现的图像上做文章;而面对装置,我更多的是在媒材本身固有的语法体系下将不同材料拼起来,是在处理不同物体对象之间的关系,而非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譬如将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在其固有的语法条件下, 它们之间所生成的关系让我有可能在原有的固定语言框架下推翻某种均衡。
具体到这两件作品,装置作品中,我并没有尝试想要改变油或者水给我们的感受,想要强调的只是油或水本身的纯度、重量等等,还有亚克力材料、承重的千斤顶本身的语法环境。当我们面对鱼缸式的巨大玻璃箱时,即便它被做得有8厘米厚,也还是会同时感受到它承重能力的极限点与易碎的特性,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不安全感。我将这些常规的东西组合起来,它们在本身的语法环境内部挑战自身已经固定的结构,而非我在外部建立某种新的语法环境来与之对立。
ARTINFO:所以说,是将媒材作为一种表达的工具。
黄然:对。媒介不是问题,甚至原创性都可以不是问题。我所强调的是,在对媒介语言的控制过程中,作品背后的观念所制造的“关系”和“影响”。一方面接受依赖于某个系统,另一方面又在从其内部对它发起挑战,这样一个有些矛盾的局面。
ARTINFO:这组装置作品的标题尤其具有意味:“许可,循环的允诺”;“意志的软弱, 对社会的恐惧”;“与生俱来的敬畏和恐惧之中的爱”;“同某种安逸相关联着的此起彼伏的欲望”。它们既具有提示性、又带来了更加模糊的外延。在你的创作过程中,标题和作品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黄然:我的工作方式不是很固定,标题和作品并没有一定的先后关系。标题通常比较主观,是我在这过程中对待这个问题的想法。以《意志的软弱,对社会的恐惧》为例,我是有比较明确的意向的,那件装置从结构上来看存在着某种危险,很有可能会掉下来,同时下面的泵产生震动,既强化了这种可能性和不安全感,也有通过形态隐喻广场上的喷泉这样一种荣光的象征的用意,这是很古典的表现方式。我的装置中这一点以某种“愚蠢”的形式体现——“喷泉”喷不起来,于是也表达着一种矛盾:在希望某种结构瓦解、并且想要建立某种超然的新系统的同时,当从原有系统内部出发时,意志上的软弱也体现在对于社会结构的恐惧和被动依赖上,也就是说没有足够强大的愿望来将之推翻, 因为尝试颠覆的对象也正是依存的对象。
ARTINFO:再来看这件与展览同名的电影作品,其中(在影像中缺席的)父亲的意象却是时常在场的,这一角色的安排有怎样的意味?
黄然:父辈在文化里一直都作为某种权力至高无上的形象出现。里面涉及到了很多欲望,对于一个权力标准的欲望,恐惧,信任,以及依赖,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包含了某种挑战,背叛,试图脱离某种权力结构和势力范围。
其实我还埋藏了一条非常深的线,几乎无从发现:二战结束后在欧洲有很多失去家人朋友的精神病人,1950、60年代,欧洲很多国家的牙医在各地的精神病院做了很多实验。他们每天给这些病人吃特制的太妃糖,然后通过很多年长时间观察他们的牙齿病变,现代牙医医学的很多临床知识都得益于当时的实验。当然,观众有没有发现这条线并不重要,我也极力在隐藏这条线,不想让它成为某种历史参考,甚至在去除某种固有内疚感和罪恶感。我所提供的图像在背后隐藏着其本质上的揶揄——被自身极力否定的固有不安全感所保护着。
观众对于这个历史事件、以及对于作品的理解,对我来说不重要;真的要达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甚至用不着做艺术作品、直接复制历史材料就可以。在影像中我想要做的是提供某种经验性的体验,并不是要提供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而是想让你处于这么一个世界当中、在排斥怀疑图像内容的同时, 图像的肤浅性也在建立对于本质上的不安全感的信任和依赖。
ARTINFO:这是否属于影像的特质?
黄然:我觉得是整个文化的特质。若是提到一个表面的层面,可以说历史、经济、政治都包含在内了。文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将不安全感安全化的东西。当代文化本身就是混乱的,而且我们很依赖于这种混乱,我们所依赖的有时很可能是想要反对的东西,也就是说,欲望所建立的基点、很多时候也正是所排斥的东西。艺术从未真正意义上关心过某事某物,它所真正在乎的或许只是关心事物时所激发的片刻沉醉情感和体验。
ARTINFO:我注意到你经常在影像作品中有去背景化的倾向,譬如《下一轮才是真实的生活》《假动作逼真》都用了黑色背景以突出人物及其行为,同样,《愉悦悲剧》与目前这件新作尽管丰富得多,也给人以背景不明的印象。你是怎样考虑的?
黄然:你提到的黑色背景的两件,我更将视其为录像;后面两件更多的是电影。二者是不同的。录像更多时候,对我而言更像是绘画,画面涵义、画面表现显得更重要;但在电影中,很多时候是在与图像的肤浅性打交道——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影响观众情绪的机制,即便单独的图像本身没有太多内涵。在电影中我会更多地想如何出发,如何去影响观众的情绪, 然后把某种谋算埋藏在观众放松警惕后对于图像的信任之中。
ARTINFO:这触及到电影与录像的区别,而你是如何发现这样的区别的?录像是否更具观念性?
黄然:是在工作中慢慢发现的。《假动作逼真》那件作品,最初是想做成录像,但现在看来,算是我从录像到电影的一个尝试,是我从图像本身出发来考虑可以怎样做。而电影有一个特点让我觉得挺有意思:哪怕是再无趣的电影,五分钟后都能让人跟着它的内容走。所以到了这件作品,我就有意尝试做得更像电影。而此前的几件都算是录像,思考的角度、策略都不太一样。
电影对我来讲也有很强的观念性,根本上来讲,是关于如何接近观众、如何来定位(locate)观众的思绪。
影像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包含了时间,真实的时间进程,它不断地处于消逝的过程中,这让我们面对影像时需要更加关注图像本身,同时这也是最接近于幻想中的真实的,电影工业对整个文化的影响,多少也来源于此。
ARTINFO:具体到其中的电影语言,你在这次电影新作《破坏性的欲望,镇定剂,遗失的清晰》中插入了不少空镜头,而且人物的对话都是通过无声、配以字幕的形式。有怎样的用意?
黄然:字幕的安排,是从一个平等的出发点出发的,尽管我不会去考虑谁需要看字幕、谁不需要这样的问题。这与阅读习惯有关,当我们阅读对话的时候,脑子里不可能没有声音出现,在个体欲望的作用下,每个人得到的声音都是不同的,整个片子都是关于欲望的。我并不想做一则“电影论文”,阐述、或是讲道理这些我都没有兴趣。
ARTINFO:那么在你看来,艺术之中你看重的是什么?
黄然: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但我觉得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多少都有改变什么东西的期望——譬如,改变社会、改变文化,都有觉得艺术高于其他社会层面这样的看法。我对这一点很有疑问。我还是认为艺术是一件很懦弱的行为,因为始终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框架内、包括各种欲望在内,并没有挑战到什么极限。但同时,我也还是很希望艺术成为一种具有力量的东西,这也就关系到自己在其中采取怎样的策略。
ARTINFO:一直以来,你在创作中关注的东西具体是怎样的?
黄然:我想应该是我对于道德美学无解坍塌所产生的诱惑和沉迷状态的兴奋和不安。我从没试图去解释或者说制造理解性的作品,我想某种程度上制造同等质量的混乱,同我们自身的美学价值以及道德意志的某种不可能性进行交流的冲动,但是同时也在从内部否定这种内容上的交织。我的创作并不寻求吸附于哲学或者批评思考以便从中思考我们自身的条件。它更像是某种被挑战的欲望本身,满载着可能性但是也处于对自身不经久的安全感的恐慌之中。
我想我一直都在尝试验证某一个转折点,在那里我们自愿被安全化后的美学不安全感所阉割。如同身处宗教狂热,我们选择的是某种美学实用主义而不是理解那与生俱来的缺陷和无解。理解在这里显得不仅柔弱无力而且滞后。我更希望这可以是一个被挑战的欲望本身。我的很多作品都涉及到同一概念。只是我选择了不同的策略。这个策略包含了我和媒介语言的关系,我和整个行业的关系。
ARTINFO:这次展出的新作,在策略上有怎样的推进?
黄然:这次的影像作品就比以前的普通了很多,从图像上看,没有了暴力、色情这样的东西。在拍之前我就想,是否有可能拍很普通的东西,在没有直观呈现的情况下带出暴力、色情等这些所有的元素,这样会更有力量。乔装的宁静画面,自我矛盾地试图同精神错乱以及狂热的混乱状态发生关联。这种来自内部本身的矛盾取代了关于违反戒律的实体图像,在一个极端可疑的浪漫主义及表现主义色彩下,挑战着我们道德美学的边缘。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