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katerina Degot
叶卡捷琳娜·迪哥特(Ekaterina Degot,1958- ),生于莫斯科,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现生活、工作于莫斯科。毕业于俄罗斯美术学院,艺术史学博士,专攻俄罗斯20世纪艺术史和俄罗斯当代艺术。曾任多家知名报刊、机构的资深主编和策展人。现任教于亚历山大·罗德琴科摄影与新媒体学院。
文/叶卡捷琳娜·迪哥特︱译/莫愁(陈嘉莹)
Ⅰ.摄影师Vs. 艺术家:一个关于殖民的故事|Photographers Vs. Artists: A Colonial Story
在这里,我将以一个策展人、一个作者、以及最重要的以教师(因为我曾在学院带过很多年摄影系和艺术系的学生)的眼光,讨论一些摄影和所谓的当代艺术之间复杂关系的内在悖论,这种探索我认为有必要以破碎的途径(fragmented way)去实践。说句题外话:莫斯科罗德琴科(Rodchenko)摄影以及多媒体艺术学院是一所研究型学院,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个另类的艺术学院。它身处的这个国家,在专业艺术教育中仍在培育十九世纪时期的学院派画家。摄影被广泛提起,但只局限于商业广告的领域。我看着这些年轻人在他们各自作为摄影师和艺术家生涯的惶惶无措的开端,让我在这两个最终会变得模糊不清的系别之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那就是,不管这两个专业在最后有多少重叠,学生在开始时是非常不同的。
摄影师之流经常看起来天真且朴实。好比他们会用“将美和喜悦带进人们的生活”这样的修辞,但我会痛心地告诉他们如果带着这样的期望对摄影生涯是毫无帮助的,相反,他们应该选一个大相径庭的词对摄影做出描述。我建议他们承诺去“惹怒”(disturb)和“挫败”(frustrate)一些无知观众,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改变自己所创造的图像(PeterFischli和David Weiss就把猫和花拍的十分沮丧无助)。至于那些已经尝过当代艺术滋味的摄影师们,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对无知大众表现出漠不关心的蔑视。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对社会是有益的|sociallyuseful|——这个声明是用极端复杂的语言做了最准确的描述。随之,当代艺术以类似的修辞技巧出现——一个解释所行之事的工具——而这些则是摄影师之流不擅长的,但摄影师们所做的事多多少少刚好和日益膨胀的当代艺术框架相符。
在他们对观众疑惑的漠不关心中,专注的当代艺术家似乎被个别消费者独特的逻辑对象所保护着。这一对象虽然离他们的录像装置很远,却仍处在艺术家的范畴当中。数码摄影师或是非数码摄影师都乐于分享和交流。他们对成为“艺术家的艺术家”不抱太大希望,也没有准备刻意向虚构的观众呈现费解的艺术。并且,这并没有使年轻摄影师在数量上比立志成为杰出艺术家的人更左派,事实上,反之却然。
我们学院曾被认为是“纯摄影”学院,这一形象在近几年转变了很多,但也并没有完全转向多媒体艺术学院。这也是我们的学生所走的道路:在第二学年末(总共有三个学年),一半声称自己是摄影师的学生决定完全戒掉媒介的瘾而满腹激情地转向录像和表演艺术。可能是我们作为老师的,经常向他们反馈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一种令人恐惧的怀疑——这种怀疑认为摄影学院、摄影画廊、摄影博物馆或是摄影双年展是自我欺骗的犹太集中营。谁能忍受一个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创办的水彩画学院呢?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困境。选择摄影还是当代艺术在逻辑上是不通的。难道摄影不就是当代艺术么?(现在还有什么能比按快门这一行为更当代?)有时候,事实的确如此,但有时候,摄影沦落为“当代”却和“艺术”沾不上边,只是作为艺术领域之外的某种承载物(像是护照相片或是一份文件拷贝)。如苏珊·桑塔格的那句名言所说,摄影基本上是一种可以传递任何意义的通用语言。不像水彩画,摄影是等测成像的,它的概念小于艺术(因为他是当代艺术的其中一种媒介)又大于艺术(因为它在艺术和非艺术领域都会被用到)。而当我的摄影系学生为自己还不够格成为艺术家而感到自卑的时候,在当代艺术的逻辑中,他们其实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拥有当代艺术家身上罕有的东西——一个不往艺术方向偏颇的态度以及一种对真相的诉求(虽然这种诉求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然而,虽然二十世纪的摄影经常被看作像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那样的先锋派艺术家作为企图逃脱“学院派”艺术陷阱的途径,当今的摄影术却成为一个相当“古老”的学科(数码摄影已经被化入其中,更不用说早期的化学照相术)。艺术的残留物正是隐藏在这里。至少在我的那群摄影系学生当中,技术被再次强调,传统的态度保留了下来,个人的审美得到赞赏,创作者往往看重传统和风格而不是作品的商业价值。
我的摄影一年级生一般都痴迷于稚嫩的“街景拍摄”并十分推崇美景(vision)。我的艺术系学生则将艺术看作陈旧的先锋派媒体批判和反视觉(anti-retinal)的实验(简单地说,就是你什么也看不到,或者,你看到的一切都不相干)。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智慧上,甚至是阶级上的不平等,甚至类似于殖民统治的关系。艺术喜欢摄影这一媒介,因为它十分“简单”,不“矫揉造作”(non-artsy),十分“直接”。出于同样的原因,艺术也不总是看好摄影的,因为摄影师开始渐渐厌恶自身以及自己所声称的“返璞归真”。艺术家之流从很早就开始讨论使用让摄影师感到神经紧张的摄影术。艺术家在建立他们众多的“研究装置”和“图像拼接”时,充当了策展人的身份。摄影师们则怀疑他们自身很快就会被他们的同年级艺术生客体化(objectified)以及器具化(instrumentalized)。
典型的年轻摄影师相信要成为当代艺术家需要一个“补充”——空间的(某种特别的装置:一本书,在其他物之间)或是时间的(将照片变成序列的幻灯片,加上音效或是文本)。而其中最紧要的是重新获得展示以及叙事的控制权。这难道不像自我殖民和自我剥削么(摄影师也正开始使用自己的快照)?是否这里面也有去殖民化的策略?在艺术和艺术展览里面直接的摄影到底能够拥有怎样的位置?毕竟,当代艺术最先是受摄影启发的,是库尔贝式的现实主义。这样直接且带民主倾向的图像,被先锋派和媒体批判的态度夺去了光彩。摄影现在还有机会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么?
Ⅱ.照片Vs. 当代艺术:超越快乐原则|Photographers Vs. Artists: Pleasure Principle

© Martin Parr
我必须为这么久的沉寂道歉,前段时间一直在旅行交友。时常与外界交涉导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更别说写作了。如果我是经营摄影而非博客,这样的生活其实对创作更有帮助。我可以拍成百上千的照片(甚至是在演讲的时候给自己来张自拍—为什么不呢,这可能很讨人喜欢!),然后发在Instagram上。像博客的共同作者Casey Smallwood所说:“参与到‘轻松的’艺术创作当中——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按她这个理论,写博客要比写学术论文更接近摄影和传播摄影的当代过程。但是,这仍然不一样。唯一最接近这一当代过程的行为是不间断的用录音机记录自己和他人的话并上传至YouTube——奇怪的是,我们从来不这么做。因为与友人在惬意的晚上聊天,其内容大多并不重要,但却容易记住,至少比记得他们的穿着容易一些。
当代摄影所产生的作品,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一样,都带着自身的索引性质,仍然停留在“(事物被拍成)什么样”的美学追求上:然而,现在的当代艺术则更倾向于“非视网膜”层面的“意义”。这听起来似乎过于简单。虽然我特意指出是“现在”的当代艺术,但是现在仍有很多以具体对象「object」为基础的艺术只为了得到观众的注视(他们在艺术市场上十分成功)。现今,它们并不在双年展和盛名的群展「prestigiousgroup」聚光灯下。相反的,现在受关注的是物象更少,文章更多的当代艺术。一段文字,一些理论,与大量的媒介,都被展示在“研究装置”「research installation」中;并且,摄影也可以被应用其中,但是,它只是被使用,而并没有得到其“自治权”。
艺术家将摄影用作媒介,并发现摄影的可触摸性,策展人亦然。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样的摄影更容易在知名的群展中出现,我认为是最不艺术的一种——“淳朴”的“直接”的那种——甚至是那些完全在艺术的自治领域之外的。一个设计过的快照和报刊上的照片可能更接近于此。这一直就是像Hans-Peter这样的艺术家所做的,但是现在策展人看起来的也改变了他们在这个方向的兴趣。作为一个策展人,我深刻知道当你处于数不清的艺术作品之间,试图从它们之间区分开来并表达自己的意图;这时,你手上最好有一系列简明的摄影作品——照片可以做出明确的政治陈述(有时要比摄影师本身所想表达的还要直接)。将社会类型的直白面貌(如August-Sander拍的)和费解的装置放在一起,作用十分显著;它们提醒了我们有关战争、冲突和阶级利益的所有——都隐藏在更抽象的雕塑形态背后。Thomas Ruff的艺术恰当的对几乎任何事物做出了评论,虽然年老的脸能达到更好的效果「agesfaces work better」。景观「landscape」和内部,如果足够具体化,也可以不厌其烦的进行谈论。这看起来,艺术(尤其是涉及社会政治的艺术)需要具象化的支持「representationalsupport」——“意义”在其中不那么跃跃欲试(虽然这可能只是假象)。艺术需要非艺术或是不那么艺术向的艺术(纯粹的文档或是纪实摄影),这为它在“纯粹的艺术领域”预留了威望。矛盾的是,非艺术成为了一个为那些能够欣赏的人所建立的新自治区。
这个有趣的非艺术的傲慢曾经给了我一个教训。当时我正在地中海的一个国家旅行,因为想一睹那儿的一个教堂建筑,就跑去了一个远山上。由于天气很好等各种原因,我在野餐的时候沉浸在这一美景当中。突然,我的旅行同伴也过来凑热闹,并且疯狂地拍照。当她注意到我时,瞬间改变了态度——不自然的严肃甚至自大的表情。她看起来是被迫拍照的,并且这一过程让她十分不快。或许她是艺术史家之流,努力想表现出她的行为是出于专业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图一时之快。
这使我们出现了阶级的区别,不过是何种阶级关系呢?她是不是试图告诉我她的眼光是出于“冷漠的”贵族高雅艺术,这种高雅艺术要高于我这一介旅客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对的。但在另一方面,她看起来十分坚持自己“严肃”(学术)的创作并将“快乐”的尺度排除在外,对她来说,这是为了保留满足感「gratification」。她的照相机只是功能的附属品,并没有艺术意志;矛盾的是,照相机又给她带来权利以及贵族的霸权。这是一个有趣的康德/反康德「Kantian/anti-Kantian」的时刻。事实上,摄影时常预示着康德(而不是罗兰巴特)的到来。
众所周知,根据康德所说,美学的范畴超越“惬意的”「agreeable」和“满意的”「gratifying」的概念;这是一个纯粹的领域,无法经过理性推算,因此更大程度上来自本能。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他的名著《摄影:中产趣味艺术》<Photography:A Middle-Brow Art>写到:“在解读摄影时,‘大众审美’和 ‘高雅艺术’、特权社会以及道德感都相反。”当布迪厄在1965年编辑这个卷本的时候,这种工人阶级的态度被边缘化成一个无知群众的失常表现。但是,从1968年起,人们对道德感以及社会意义的追求持续增长,直接的摄影渐渐获得了一种莫名的非纯艺术的地位——也正因此,它才是真正的“高雅艺术”「highlyartistic」.
Ⅲ.摄影Vs.当代艺术:演讲表演的案例 | The Case of the Lecture Performance

© El Lissitzky
现在的摄影术(和摄影师)越来越少在当代艺术展中出现,然而展览中的照片却日益增多。照片是我们借之观看当下世界的镜头,它在无数次复制过后来到我们面前。几乎我们目前所见过的每个静态图像都可以算是摄影,因为甚至艺术批评家都很少能够接触原作。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摄影充满于“研究装置”和各类的文档展示中;他们以一系列的相片展示,像是电影的剧照。但是近来,他们甚至开始出现在表演中——例如,在日益热门的“演讲表演”中。
在表演中牵连到摄影看起来或许很矛盾。因为象征性和技术性的本质因素,照片总是被人看作是一些旧事的再现,无论真实与否。然而表演,按定义而言必定是“此时此刻”的事件,即使他其实是“当时的此时此刻”事件(当我们看到它们被记录)。事实上,“表演档案”[performance documentation] 的现象(也就是一个表演的存档),是我们长期熟悉的。不那么好理解的是“档案式的表演” [documentation performance],这是一种展示文献 [documentation and documents] 并连带着艺术家批评的实时表演。即使我们排除以身体语言和言辞(而不是图像)为基础的演讲表演(好比Xavier Le Roy 或是 Andrea Fraser的),仍会有很多艺术家存在于这一领域(比如Hito Steyerl、Walid Raad、Rabih Mroué、Boris Ondreička、Uriel Orlow和Haig Aivazian等等)。这些讲话并不依附于而是构建于筛选过的图像:数码照片(摄影师自己的、别人的或是不知名的他者的作品)。这是相对新的现象,虽然艺术史家已经做了好几年类似的事。但是现在这个领域已经是人山人海了。表演者现在正从不同方向带着不同目的涌入这个领域:研究者乐于在他们的演讲中添加艺术性的剩余价值,摄影师以序列幻灯片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图像并将此转化为基于时间的艺术,艺术家将他们的研究装置(或是电影)变成现场演讲以保证他们言行的表现(并为自身传记式的参与买单)。
许多因素潜藏在这场大量往演讲表演领域移民的潮流之下。我们一直有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通过演讲人的身体去掉自我和艺术作品的疏离感。学术圈有种不稳定性以及不安感,因此我们被推向了放荡不羁的“艺术性”。据说在叙事和故事上日益见长的兴趣或许有助于停留在非历史的(至少还有一点黑暗)的时间上,那时我们充满了政治绝望。我们也不应该不去考虑艺术经济从独特事物的私人市场往流行音乐中以收费和由演唱会为组织的经济(摄影师实际知道的东西,按小时收费)。
但是我们现在把图像的产生、传播以及展示看作扎根于一个单一过程的行为(有时只发生在一架设备当中),而不是带有不同中介、不同制度的空间领域。
而艺术的领域现在是在展示而不是生产。
控制他/她的作品展示使得一个摄影师变为艺术家,一个艺术家变为装置艺术家,这就与拥有最大展示控制权的策展人接近。最重要的是,这个展示在当代构思并表演式的呈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阶层。改变展示方式的想法就曾在一些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脑中出现,包括我。展示方式现在不仅是以空间而是以时间去构思的。
数字时代是否造成了图像生产和展示时间的增长?今天,我们经常在屏幕上看到图片,但是展示是线性发展而不是同时发生的多屏再现(虽然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一个传统的空间展览提供了更多从不同方面(正反面以及与外界的比较)去观察事物的机会,这辩证地倾向了俄罗斯的先锋派(包括El Lissitzky 和 Alexander Rodchenko)所针对的对象。一个数码图像自身也是一个表演,如Boris Groys最近说到的,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计算机文件的一个版本,在不同的设备和网络中呈现,每次都显示了不一样的质量。这使得数码摄影变得具有行动力 [performative],即使按下快门的一霎那并没有摄影师的参与。但是为什么要在表演的再现中揭示隐密的表演呢?
这也攸关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和时刻包围着我们的全球市场,这样的全球市场带着势在必行的推动力以及永不停歇的循环流动。在许多人都拥有相机和手机的文化中,图像的过度生产当然和消费品的过度生产有关。大多数这样的照片都如商品一样,从来没有被看见过更不用说曝光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场演讲中评论——即使图像是平庸的,特别当它们平庸又不起眼时——意味着暂停了循环流动和“对极致的追求”,至少在那一时刻是如此。这使得重读档案的艺术家象征性的成为了一个消费者——一个获得“语义通行证”[semantic license] 的人,就如Allan Sekula富有见地的说道。
艺术作为表演的姿态从图像生产到图像传播的转变已经在先锋派早期就显而易见了。然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则说过不一样的话:未来的艺术家将会成为自己作品的作曲人——而不是在音乐的意义上,被其他人强加配乐的表演者。这使得向店员或是产业授权艺术商品成为可能,艺术家仍然掌控者“配乐”——所以这使得先锋派艺术家有可能在他者的摄影中制造蒙太奇。
这就是著名的后福特主义概念性的转向艺术的开端,但是这并不以艺术家呈现空洞的理念为终止。我们现在遇到的是,艺术家表演他们自己(知识)的艺术作品。每个媒介——包括装置尤其是演讲,越来越明白表演行为日益增长的地位,作为一个在其再现时候的表演 [a performance in the moment of its presentation] 。事实上,这正是康定斯基所说的意思。他在1910年代“发现”抽象绘画并不是为了发明某些并不存在的事物。众所周知,结果他用简洁的表述行为姿态做了展示:康定斯基将他的自画像旋转90度(可以说是展示给他自己看),然后突然觉得它是抽象的。同样的,杜尚颠覆了他的小便池来作为新的艺术作品展示。
这种“表演性的变化”或者说是“展示性的变化”——我们仍在当代艺术中处理的——不再被认为是无形生产,因为无形的领域被“认知资本主义” [cognitive capitalism] 所殖民。
摄影一直是现代艺术的副本,以非艺术作为决定性的艺术政策。对于历史性的先锋派来说,和摄影相关的是由技术产生的图像——在这些图像中,艺术的主题变得世俗化。对于概念上的1970年代,这是符号学中摄影后福特主义的无形物和参与。今天,真正重要并且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数字快照的恒流以及随之向无限展示的转向。
Ⅳ.摄影师 VS. 当代艺术家:谁的危机更大?|Whose Crisis Is Deeper?

© Jeff Wall
摄影和当代艺术都还处于一个权利悬而未决的纠缠关系中。从本质而言,摄影是艺术的其中一种媒介,而艺术则是摄影的其中一种应用。这刚好导致二者纠缠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无止争论中。确实,即使摄影明显要比艺术的出现晚很多,但当代艺术可能仍然要比摄影要晚——这取决于我们怎么定义当代艺术的开始。
一些人,包括我,会认为摄影和当代艺术诞生于同一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学科至今仍有很多共同点,并相互支撑着对方暂时还算相处愉快的原因。但是一个人很难对摄影师和艺术家说这样的话:那些有关当代文化情境的描述完全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其实十分互不信任。
众所周知,那些用照片作为作品的当代艺术家无一例外地否认自己的摄影师身份,即使展览的正是自己拍的照片,他们倾向于在作品中投入大量的个人时间有时候甚至包括自己的手工艺。摄影师有时会以艺术家毫无技巧的作品贬低他们。艺术家声称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评论那些令人费解的准宗教禁忌,这种禁忌认为申请加入双年展获得佣金,或者为自己的个人展出钱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他们对最终展示出来的作品都表现了或多或少的容忍。相反地,摄影师却不认为付费的评审或是获得佣金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们可能很难接受纪实摄影的数字化,冒充“真实生活”的摆拍照片,或是违反那些美学领域之外伦理领域之内的规则。
两者之间到底是谁在经历着更严重的身份危机呢?当代艺术家还是摄影师?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于外行而言,当代艺术仍是一个十分高深莫测的东西——“正常人”会发现很难去定义它的范畴以及它存在的理由。但是艺术圈内的人会在他们不确定的身份中感到安定和舒适。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在实践中(而不是通过书籍)学习的很快,他们之为艺术家的原因是他们能够和个别机构打好关系(非盈利的艺术空间、双年展、驻留项目或是国际策展人),他们的工作可以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甚至做到无实体化。当代艺术家十分知道他们的身份。
相比之下,摄影师们,看起来是在生产十分简单也容易辨识(谁不能发现一张照片呢?)的作品,但是他们仍在无数个不同行业中迷失自我。当你介绍某人是“专业摄影师”时可能会引起很多误会。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拍照的时代(并且最重要的是,每个人也都在这么做),“专业摄影师”看起来自然应该是那些可以从他们的照片中获利的人,被杂志、摄影机构甚至是私人(那些把自己的结婚照外包给“专业人士”的人)雇佣。
相关的批判摄影 [critical photography] 会发现自身处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被包围着,岌岌可危。一边是拥有iphone的“自拍瘾者”,另一边则是服务行业(但哪一边都不算是“左派”)。我们越来越难以用简单的方法解释Allan Sekula, Boris Mikhailov或是Wolfgang Tillmans的摄影和娱乐杂志或是时尚杂志的摄影有多么不同。仍坚持这个名字的批判摄影师 [critical photographers] (其实并没有多少人仍在坚持)现正经历着语言困境,这一困境使他们回想起早期先锋派的困境——艺术家必须承认他们的学科不是浮夸的学院派画家所谓的“艺术”而是其他别的还未被定义的东西。一些这样的艺术家试图为他们所行之事发明其他的名字——而有时候这个名字恰恰是“摄影”……
所以,当艺术家们,甚至是批判性艺术家 [critical artists] 仍在享受半个世纪以前的制度和路线时,我们还能说一个批判性摄影师的境况是处于弱势么(可能是多产的弱势)?当一些摄影师放弃了摄影时,他们或许会这样想;但是艺术家的稳定身份也在以一种全新的途径变得日益危险。
如上所述,批判性摄影师 [critical photographers]可能是业余的也可能是专业的。而艺术家直到最近才有这样的划分。 像“周日艺术”或是幼稚的当代艺术这样的东西长期被认为是一种自身之外不可能存在的矛盾:艺术毫无疑问需要一定的思想深度、坚定的决心和对艺术史的了解。另一方面,从实现雇佣式艺术的意义上来说,专业化并不被看作是真正的危险或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即使是那些完全投身政治的艺术家仍一直强调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
但是这些关于当代艺术家的假设——关于他们完全的自觉性以及完全的自主性——被动摇了。像现在这样的“业余”当代艺术被“民间概念化” [folk conceptualism] 并充满着社交网络。而像“大众当代艺术” [masscontemporary art] 这样易识别的(大部分是数字化的)语言经常被广告、商务演示或是网页设计所挪用。“委托的当代艺术” [commissioned contemporary art] 则是出现于在废弃大工厂空间中举办的艺术展览。在这样的空间中,很多策展人会要求(或者他们梦想能够要求)艺术家做一个“巨大的并微暗的中央椎体构成”或是画一幅“在五米凹墙上的鲜亮壁画”。
当代艺术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挑战,这个挑战要求他们自身和器具化的 [instrumentalized] “新应用艺术” [new applied art] 甚至是和某种视觉服务撇清关系。而这种视觉服务却是批判摄影师们已经从事很久的事情。
Ⅴ.摄影 VS. 当代艺术:下一步怎么走?|What's N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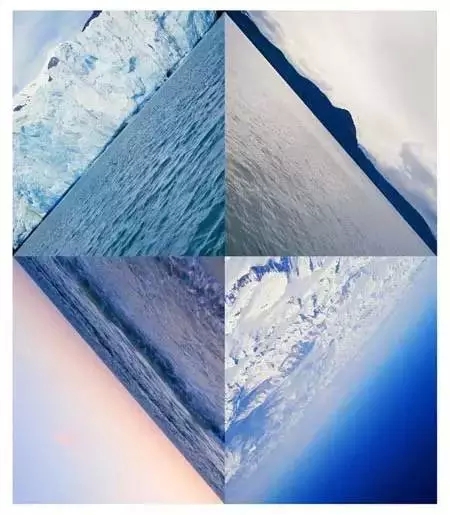
© Dug Aitken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艺术家来说,摄影代表着对新路径诉求的终极渴望。构成主义评论家Ossip Brik,在他1926年至1928年间所书写的开篇文章中(《摄影VS.绘画》以及《从绘画到摄影》),由于各种原因将摄影看作“绘画的替代物”,因为它“准确、快速并且廉价”,和“真实”更直接相关,更需要智慧(因为当时的摄影是黑白的,所以要求观者动用他们的想象力去欣赏摄影)、更具社会责任感,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更“反艺术”。根据Brik所说,摄影师总是在社会环境下工作并且再现他们,而艺术家所创作的每一幅画都是围绕着环境之外的一个客体建立的。
今天,许多事都改变了。摄影仍然速成并且廉价,但是Brik所提到的情境化伦理已经不复存在:当代的快照甚至是过时的类似物都正在或者已经被分崩离析,而这其中有着一股强大的去语境化的动力隐藏在当代快速的图像生产背后。奇怪的是,在当下,画家和影像合作(像Marlene Dumas),将历史和语境的维度重新注入影像源的随机奇点——通过添加主观触觉还有时间的维度。
对二十世纪的理论家来说(这显然包括Walter Benjamin),摄影(和与之次要的说明标签)展现了其意识形态、语境、信息和语义,但是艺术处在“纯画面”的危险向上。在新的千禧年,局势发生了转换。现在我们习惯关注于摄影的表象,而对当代艺术,因为带有其不可争议(或者说是还未被争议)的观念残留,我们偏向于它的内在含义,因此可以享受让年轻摄影家感到沮丧的优越感(虽然这个感觉不是一直都有)。
然而,摄影和绘画的困境是错误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最近被叫做“后网络情境”(“post-Internet condition”)的世界里,在这里摄影和绘画的对抗被有效稀释了。现在,任何东西只要变成数码摄影都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即使它现在不是,将来总有一天它也会是,当它们被杂志或者更多地被网站一再重现时。结果导致我们对媒体漠不关心,甚至是一种无视,我们经常不能实在记起自己看到的是一张画还是一幅摄影作品时。我们的视觉记忆经常会忽略对象的媒介。
基本上,网络传播的数码影像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艺术形式,但这并没有使专业摄影师的生活比生活在书面印刷发明之后的专业抄书员更容易。但是,更为复杂的说法是,网络传播图像的体制结构还未完全完善,并且就现在而言,这一传播途径对摄影师或是艺术家都不算有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杂志新闻开始渐渐萧条之后,纪实摄影师(至少是一部分)开始转向艺术领域或是艺术体制(市场、艺术收藏、展览、策展人和批评家)。现在,当代艺术的典型框架也同样以图像传播的新面貌在消逝,网络和社交媒体首当其冲。这些模式既保证不了原创来源的稳定性也无法保证经济利益。如Susanne von Falkenhausen最近在Frieze上所说的关于社交媒体中艺术的看法:“然而乌托邦的反资本主义者以及反消费主义者的结论性改变可能是,他们对艺术家自身是没有经济利益的。资产最有可能被数码迷社群的首都所取代。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说,艺术家试图通过对研究装置和演讲表演的巨大投入来控制数字化和展览传播的崩塌。这两者都是通过收费模式为基础的“门票经济”而不是收藏家经济来运作的。摄影师大多沉迷于另一个危险的种类——书籍,它的经济对我来说是个谜(虽然我怀疑这其中的经济运作可能都大相径庭,因为这些书广泛到从艺术家的独特设备到光面照片,并且这些骄傲的符号被主要的出版商广泛发行)。无论如何,虽然后数字时代的艺术和摄影制度的未来很模糊,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必定是需要依靠“引文索引”的,(社交媒体中“喜欢、分享的索引”),而不仅是靠市场或是艺术史(这直到现在都是种终极审判)的力量。
摄影和艺术在这样的不确定的未来面前,可以互相共享一些资源。摄影必须义无反顾的离开纯视觉领域,这需要概念和理念,需要回归到”说明标签“,需要可以同时展示他们文字和图像的书籍。首先,这需要自我反省,特别是因为这样的生产模式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而不仅是艺术的中心。近来对摄影物质性(尽管这包含数字化)的扭曲和社会/政治的暗示并没有因此变得足够重要而引起理论家的兴趣——Hito Steyerl多产的作品是一个显著且影响深远的例外。
在另一方面,艺术需要如“真相”那般简单又复杂的东西,如同在现实当中超越媒介批判这种纸上谈兵的兴趣,而这就是摄影(至少)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锚能够相关的。最近,艺术在绝对批判态度中失去了信仰,或许是为了自身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也导致了某种激进的艺术式的谦卑:提高自身的工具化,有意识的削弱了艺术的社会和政治功效,并且向科学投降。然而对“真实”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不是一种假装——仍然以摄影的视野呈现。这种呈现或许对这一挑战来说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答案。而艺术的批判精神将不会像现在发生的那样轻易抛弃它的敌人。
译者简介
莫愁,原名陈嘉莹,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兰卡斯特大学当代艺术咨询专业。现工作于上海。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