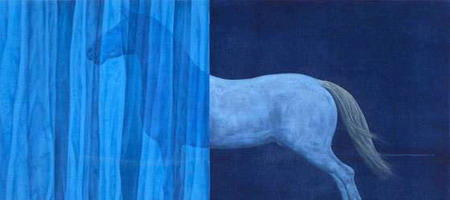摘要:如果说“新文人画”的社会学意义的转型属于相对消极姿态的话,那么,“现代水墨画”的姿态则是积极的,进取的。若是将这两大块面(两路大军)加在一起,力量就更为可观,就会在一个社会学转型的大方向上,基本扭转了由“庸俗社会学”所控制和影响的大格局。由此可见,在水墨画领域内社会学转型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中国美术三十年”论文
毫无疑问,在建国以后,庸俗社会学及其左倾教条主义思想逐渐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加上“行政命令”、“政策条文”、“长官意志”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对文艺(包括文艺家在内)的危害,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严重程度,其恶劣影响,直到如今,都远未清除干净。
如今一谈起社会学转型的问题,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可能神经过敏地回忆或联想到庸俗社会学这头恶魔,这是非常正常的,也不难理解。
庸俗社会学与艺术的社会学转型之间,究竟有何瓜连?二者之间的区别有多大?这些都是当今的社会学者必须去思考并作出回答的。
可以这么认为,在艺术社会学层面上,直到如今,还从未对庸俗社会学进行过思想上、理论上的彻底清算(在这方面有一篇文章值得大家一读:栗宪庭写的《“毛泽东艺术模式”概说》,完成于1995年,并未公开发表,后收入他2000年出版的文集:《重要的不是艺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后来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也并非是全面和彻底的,还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都未能真正地深入进行下去。像许多类似的“中国问题”一样,又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但本文的意图并不想在社会学的理论层面上讨论问题,而是想在艺术史的现状与现象学的层面上,揭示出这种转型的事实或曰依据,而且,仅限于水墨艺术的领域。直到如今,还很少有人从这角度去把事实梳理清楚。
水墨艺术领域(包括中国画、现代水墨画、观念水墨艺术等项)内的社会学转型靠的是什幺?又是如何发生的?回答曰:靠的竟是一种艺术家的良知和“集体的自觉”。时间则发生在“文革”动乱结束以后,亦即改革、开放之初(1978-1979)。当然,不能作“一刀切”,良知发现的早晚和“集体自觉”的程度各不相同,事实的本身则远比逻辑推理要复杂得多。
改革、开放美术史的起始点,美术史家们往往把它放在了“伤痕美术”和“星星画会”的展览事件。但不管是“伤痕美术”,还是“星星画会”,与中国画抑或水墨画的关系似乎都不大。遗憾的是,史家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是与中国画抑或水墨画直接相关的一个起始点——“草草社”及其第一回展。
1979年10月,由一个不起眼的青年人——仇德树率先提出了“独立精神、独特技法、独创风格”的“三独”纲领,并把它写进了后来的“草草社宣言”。仇德树对“独立精神”的理解是:“艺术家必须持久地在孤独中奋斗,在最关键时,唯一能依赖的正是自己。只有自己的内力才是艺术的本源”。一个常识告诉我们:一旦强调了艺术中的独立精神,一旦自觉到艺术的本源之一是来自艺术家的内心,那么任何庸俗社会学的教条和“律令”都将土崩瓦解、不起作用,而艺术的社会学转型也将成为一种必然。
参加由仇德树发起的“草草社”的十几位艺术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水墨画家,诸如:仇德树、袁颂珉、姜德溥、戴敦邦、曾宓、陈家泠、陈巨源等。1980年2月,“草草社作品联展”在上海卢湾区文化馆举行。这也是“草草社”唯一的一次画展(后来就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无疾而终”了)。展出的水墨作品或受抽象构成的影响,或受表现主义的影响,大致可以归入“现代水墨画”一路。由此可以认为,“草草社作品联展”乃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水墨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美术史家没有理由让这棵虽不太起眼、但却充满了生机且无比顽强的“小草”,淹没在美术史的长河里。
与“草草社”联展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是由吴冠中挑起的关于“绘画抽象美”的论战。
吴冠中的“抽象美”主张及其结合了东方式意象、西方式抽象的艺术实践(无论是其油画还是水墨画),其直接的矛头指向了庸俗社会学近三十年来所大力倡导的“新中国画”和“苏派”油画,间接的矛头则指向了艺术上的僵化思维、教条主义文艺观。总之,是在艺术史层面上的一次强烈反拨。由吴冠中所挑起的这场论战既活跃了艺术思想和艺术观念,也活跃了艺术创作,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又一次启蒙(旧中国的三十年代就曾发生过一次)。
在艺术的观念层面上真正埋葬庸俗社会学及其教条主义文艺思想的应是’85年美术新潮运动(’85美术新潮运动的余波延至1989年2月的“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85美术新潮运动最主要的文化价值有两项:其一是它的批判意义。在一个文化批判的层面上,它不仅颠覆了传统艺术,也颠覆了庸俗社会学及其教条主义文艺思想。其二是启蒙意义。在一个现代性启蒙的层面上,它不仅唤醒了艺术中的人文主义意识和终极情怀,也吸引来了西方的现代抑或后现代艺术思潮。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85美术新潮运动是庸俗社会学与艺术的社会学转型之间的一个转捩点。
这个转捩点还与全国性的“中国画大讨论”密切相关。1985年7月,《江苏画刊》以她的远见卓识与大胆魄略适时地组织、发表了李小山的一篇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即所谓“中国画的‘穷途末日论’”。文章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场波及全国,历时一、二年的中国画大论战,虽然没有催发出什么直接的成果,在理论上也并无实质性的建树,但对庸俗社会学及其教条主义文艺思想的冲击却是广泛而深刻的。
遗憾的是,在整个’85美术新潮运动中,真正出色的水墨画作品(包括风云人物在内),却是屈指可数。大家的关注点似乎都放到了油画、综合材料、艺术行为等方面。水墨艺术领域,比较值得一提有:谷文达、任戬、宋陵、沈勤、黑鬼、邹建平、阎秉会、李津、段秀苍、郑重宾、李知宝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展览是谷文达1986年6月 在西安做的“书法——绘画”作品展。影响较大的作品除了谷文达的“文字系列”外,还有徐冰的《析世鉴》和任戬的《元化——封闭系列实证三界》等。任戬的这件尺幅超常的巨作在“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件作品用相对写实的方法完成,与后来的现代水墨画似乎关系不大,要归也只能归入所谓的观念水墨作品。徐冰的《析世鉴》则毫无疑问是一件杰出的观念作品。
在“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栗宪庭组织了一次赴日“现代水墨画展”,上面提到的一些新潮水墨画家第一次走出了国门。这是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
新潮水墨艺术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对水墨艺术领域内的社会学转型仍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这里有两个突出点引人注目:一个是艺术创作的原点(原动力)由社会本位转移到了个体本位。“自我表现”成了新潮美术家的一个流行概念。另一个是形式上的原创性冲动,即所谓实验性倾向,这种实验性倾向冲破了建国以后逐步形成的“统一模式”(有人称它为“毛模式”)。由于以上两个突出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时并不十分起眼的新潮水墨创作却成为了在这一领域内社会学转型的真正发轫期(这与上述的转捩点之说是一致的)。
与新潮水墨创作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艺术现象是“新文人画”。
“新文人画”这一名称究竟为何人首创?虽已说不清楚,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清楚不过的。那就是在行将停办的1989年第7期的《中国美术报》上,刊出了由栗宪庭所撰写的一篇短文:《“南线”与“北皴”——“新文人画”两种风格的大致形成》。这篇后来影响颇大的短文把“新文人画”确认为是“近若干年出现”的事实,并认为它有“南方”、“北方”两个大块面。“南方”以董欣宾、朱新建、王孟奇(其实在他们三位中,王孟奇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笔者)为代表,“北方”以陈平、龙瑞、贾又福等为代表。栗宪庭在短文中指出:“新文人画”跨越了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水墨画革命的历史,直接认同任伯年、黄宾虹诸家并从这里起步。“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水墨画革命”与庸俗社会学及其教条主义文艺思想之间,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种种干系(这需要有人去做专门的清理)。所以“新文人画”的诸干将们敢于超越它,在当时还真是需要一定勇气和胆识的。也正是在这一突出点上,“新文人画”同样成为了水墨艺术领域内“社会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依据或曰事实。
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主要是艺术市场的追捧),“新文人画”现象在九十年代终于蔚为大观,并逐步进入主流美术。“新文人画”的代表性画家也不再限于栗宪庭所提到的几位,其队伍竟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至今已不下百余位。地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杭州、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广州……几乎到处都出现了“新文人画”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文人画”已拥有了当今中国画的“半壁江山”。
我曾撰文把“新文人画”基本旨趣分为了两大类:一类属于“笔墨加情趣的新的文人画”(即传统中国画);另一类属于“以渐进、稳健姿态出现的可以划入现代水墨领域的‘新文人’的画”。当然,还有介于两类之间的。不管哪一类倾向的“新文人画”,它们都可以归入“自我本位”的创作思路,普遍所关心的是自我个性的凸现和内心深处的表达。
当然,沉迷于个人的温情之乡或是古人所谓的“笔墨正宗”,同样会陷入新的误区,从而逃避社会所赋予艺术家的一种正当而又必须的社会担当,并丧失一种应有的良知,而这正是存在于“新文人画”现象之中的深层次危机。
新潮美术运动戛然而止。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水墨艺术领域内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最令人关注的艺术现象又是什么?
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现代水墨画”(即所谓“实验水墨”)的全面崛起。它是足以与“新文人画”、“新中国画”相抗衡的一种作用力,如今已与后者一起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但这个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不同观点的争议至今都存在。其中个别的先驱人物,至死都还没有得应有的肯定,例如燕柳林等。
关于“现代水墨画”,笔者已写过许多文章加以论析,此处不再赘述。本文要补充的是与社会学转型有关的几个话题:
其一,表现性冲动。主要反映在表现性水墨画方面,代表人物如晁海、邢庆仁、张立柱、王炎林、陈铁军、王彦萍、海日汗、刘进安、李孝萱、刘庆和等。他们在关注生命存在、表达人文情感、宣示精神品格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可以说,他们所完成的是当代人心灵史的写照。
其二,形而上的终极冲动。主要反映在抽象性水墨画方面,代表人物如李华生、陈光武、阎秉会、张羽、张浩、刘子建、石果、洛齐等。他们更关注的是超越了个体生命和现实生活的人类普遍的命运问题,乃至宇宙和时空的意义问题。可以说,他们所完成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史的写照。
其三,形式冲动,即原创性冲动。主要反映在观念性水墨作品方面。代表人物如仇德树、胡又笨、陈心懋、王天德、潘缨、杨志麟、黄一瀚、南溪等。他们既“革毛笔的命”,甚至也“革宣纸的命”,将水墨、宣纸、毛笔均作为媒材或媒介对待,并采用了一些新的媒材或媒介,从而大大拓展了水墨画的表达空间和可能性,打造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所完成的是当代人观念史的写照。
其四,都市表达冲动。传统中国画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除了《清明河上图》等极少数作品外,“山水”、“人物”、“花鸟”三科中都很少涉及都市题材。这种状况在建国以后,已有所改观。但由于庸俗社会学及其教条主义文艺思想的严重干扰,都市题材的创作并未真正进入艺术表达的深层次,大都浮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表面,例如硬生生地去画上一些锅炉、钢水、高楼大厦之类。在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逐步加速了都市化的进程,尤其是在九十年代,都市建设真可谓是日新月异。都市化步伐的加快,自然就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例如农民工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平衡问题,乃至心理上的失落、焦虑、困惑等等。这一切,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铺垫,使得都市题材的深层次表达终于成为了一种可能。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还变成了事实。所谓“都市山水画”(又称“城市山水画”)、“都市人物画”终于形成气候。而在创作思路上,二者几乎都是在延续着“现代水墨画”的路数。目前而言,“都市山水画”的建树还不很突出(尚待时日),较为突出的是“都市人物画”,代表人物如李孝萱、李津、刘庆和、叶文夫、李桐、靳卫红、雷子人、郑强、曹宝泉、蔡广斌、刘西洁、袁进华、吕鹏等。上述各位,在把握都市心态和精神诉求等方面,各有妙招,艺术语言也相对成熟。正是他们,揭示出了“都市生存”背后鲜为人知的种种心灵的真实,为“都市”这个现代化的庞然大物勾画出了入木三分的“肖像”,并折射出了这个大时代的精神状况。如今的“都市人物画”与以往一味地歌功颂德的“工人阶级人物画”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几乎就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都市人物画”的成就在整个当代艺术的大范围之内,都可以看作是社会学转型所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且还在不断地被扩大。
如果说“新文人画”的社会学意义的转型属于相对消极姿态的话,那么,“现代水墨画”的姿态则是积极的,进取的。若是将这两大块面(两路大军)加在一起,力量就更为可观,就会在一个社会学转型的大方向上,基本扭转了由“庸俗社会学”所控制和影响的大格局。由此可见,在水墨画领域内社会学转型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更为可观的社会学转型事实出现在“边缘性水墨现象”(包括水墨装置、水墨影象和水墨行为等)方面。关于这方面的现象,笔者也曾做过专门的梳理(参见《试论“观念水墨”》,刊《美术界》,1997年第4期),兹不赘述。如今看来,这一类更为先锋的水墨艺术创作思路,其基本点乃是后现代的解构方法(在这一点上,与“现代水墨画”之间已有着很大的区别或曰距离)。所以,它们所要抛弃的不仅是庸俗社会学及其教条主义文艺思想,而且是整个旧社会学的“目的论”和“本质论”。它们从解构的立场出发,把一切的现象都看作是所谓的“镜片”或曰“碎片”,并认为唯有这些“镜片”或曰“碎片”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因此,它们既要解构“目的”和“本质”,也要解构传统,而将艺术作为“符号”或“类像”来处理,伴随而来的还有行为过程。代表人物如谷文达、王川、王天德、杨诘苍、邱志杰等,更年轻的如吴少英等。可以预见,这一类现象还会越来越多,作品也完全有可能越来越成熟、可观。也许,这将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最终、也是最有可能重铸辉煌的出路之一。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与社会学转型结伴而行的是艺术形态学的转型,最终才是整个价值观的转型。这一切,目前都应还在进行之中,各种干扰也都还存在,倒退的可能亦难避免。只有假以时日,才有可能最终完成这种转型。
不进则退。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
2008年5月20日—25日,初稿。于南京•草履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