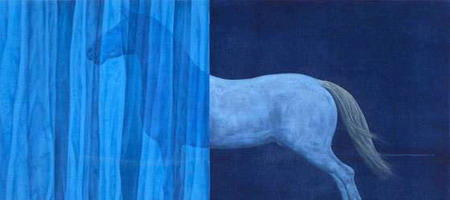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当代水墨:必然?抑或偶遇?》是2010年12月31日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举办的“透过风景+面对人群:刘永涛和李周卫双个展”时的开幕演讲,现已发表于《画刊》2011年第2期。

《艺术必须死亡》王南溟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年
在2000以后的现代水墨画现场中,刘国松一再地重复他的一句话,只有现代水墨画才是正宗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行为、装置,影像和油画的中国当代艺术都是跟着西方人后面走的,所以他对中国的美术馆要变身为现代水墨馆倾向特别的赞美,他还会不停地拿着黄河清的《艺术的阴谋》来说告诫大家不要上美国的当,就像他一直不停地嘲笑当年台湾的超级现实主义红了一会儿后,西方人就不理了那样,而他的现代水墨画还在为美国的美术馆所收藏,其实这不是刘松国一个的逻辑混乱,而是中国民族主义文化的逻辑混乱,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五月画会,刘国松这个艺术斗士,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到美国后,由于华人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低人一等,由于中国人还被日本人所鄙视,说虽然日本文化是从中国来的,对中国的文化是靠日本复兴的等等,而愤然强调中国的身份,所以艺术斗士要在本土而不能在异国,地域一转,身份地位一转,什么都会变样,从一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诉求而向望西方到回国鼓吹文化保守主义,不只是刘国松一个人是这样的,那些整天在叫嚷着21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危机,要用中国文化去拯救的可笑论调,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十年了还在重复,新儒学就是这样的一种立论,文化与物质被他们作了两分,西方是物质发达,中国是文化发达。当我们谈论艺术中的新儒学,刘国松是我不会放弃的一个案例。
有关新儒学与中国现代水墨的关系在我的《艺术必须死亡:从中国画到现代水墨画》有所贯穿,刘国松的现象当然也是这本书中所回避不了的,仇德树也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他在1990年代频繁与刘国松之间的合作,而与刘国松他们有着共同的诉求,这种诉求如果要获得立锥之地无可非议,而要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只能是这样的艺术,那是有碍中国文化的发展,我在讨论仇德树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例案,来说明一个艺术家在中国身份问题的挤压下是如何从现代化理论转向新儒学的, 2007年11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开馆展“’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的系列讲座中,我以《从现代化理论到新儒学:思想的陷阱》为讲题,以仇德树的水墨实践为背景,区分他的现代水墨两个阶段,即现代化理论的阶段和新儒学阶段,尽管仇德树依然在从事着水墨创作,但由于理论背景变了,其作品的价值系统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在《艺术必须死亡》一书中对仇德树的概括,从中国画的现代化诉求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儒学价值的诉求,这也是整个现代水墨领域出现的一个变化,我称仇德树是水墨领域的新儒学急先锋,以至形成了他的两组作品不同的作品,一做是裂痕形式画面,一组是用裂痕技法画的山水画,前一组要裂变,后一组要天人合一。而我对仇德树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下的现代中国画创新作了回顾性评论, 2005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艺术史的回顾性研究和展览的项目,首先选择的是“文革后”和“85新潮”前的上海实验艺术,因为史料研究和展览策划工作量大, 2007年上海多伦现代馆的新水墨大展中策划了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就是“仇德树:草草社之后的十年”,这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现代水墨实践者,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水墨在85新潮美术之前的状况,2008年是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办的 “转向抽象:1976-1985上海实验艺术回顾展”中也有仇德树和他的草草社,这个案例然后在但仇德树对我的这个评价大为不满,理由如他说的,他没有读过新儒学的书,但我的回答很简单,没有读过新儒学的书不等于没有接受过新儒学的影响,只要新儒学的论调在广为传播,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而且仇德树本人对作品的解释都有问题,要“天人合一”,就不能强调“裂变”,所以以“裂变”解释山水画就很荒唐,仇德树到现在还在重复他的“三独精神”,所谓的“独立精神,独特技法,独创风格”,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当时艺术家都有“三独精神”,不唯独仇德树一个,其实仇德树早年的“裂变”系列可以用更好的解释系统,那就是文革后的“伤痕美术”,而现在的山水画,只能用他那似懂非懂的新儒学来解释,如果连新儒学都没有了,那很不幸,仇德树就是一个画装饰画的画家了。
把水墨作为一个赞美的对象还是对水墨作为一个问题情境,而用艺术的方式对它进行讨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也会有不同的创作方法,第三个案例是刘超,1998年在北京德国大使馆旧馆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展名叫“反思传统”,刘超拿了他的《机器书法》作品参加了这次展览,在这个二十多年中,知道刘超的人很少,尽管我在他的作品展览后就写过评论文章《刘超的“机器书法”与徐冰的“新英主文书法”》是其中的一篇,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举办的2010新水墨大展中我策划的子项目“水墨的边缘”展中就有刘超的《机器书法》作品的回顾展示。刘超在北大读计算机专业的时候参与朱青生的现代书法活动,也是一个以计算机工程师的身份介入艺术的一个艺术家,在《机器书法》是,刘超将颜真卿的法书用计算机程序编码,从电脑中以人书写的速度,一笔一画地将颜字临摹出来。刘超用的是计算机,但针对的是水墨问题,它突破了做与水墨有关的观念艺术一定要用水墨材料的传统,所以说,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水墨领域,如果我们还需要这个领域的话,它不是画种,而是一种观念指向,可以有水墨材料,也可以没有水墨材料,这样水墨从某一个角度就被卷入到其媒体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中,正像我在1990年代早期就开始讨论的这种观念艺术中的水墨问题。
假如水墨不再作为材料决定论的而是创作中被使用的泛材料的一种,那就有可能扩大它的实验的可能性。第四个案例是张健君,2004年在深圳水墨双年展的高名潞策划的“水墨空间”子项目中,张健君参展的作品是太湖石的行为和影像。作品的过程是在墙上将一张宣纸覆盖在一张黑卡纸上,然后拿毛笔醮清水在宣纸上画太湖石,由于宣纸的特性,清水划过后,背后垫的黑卡纸就渗透出来变成了太湖石的轮廓线,等宣纸上的水痕干了,太湖石的轮廓线就消失,而又还原为一张白宣纸。整个过程以影像记录,行为结束后就以影像的方式展示这个过程。在当时的展览现场,我就跟和张健君讨论,用这个方式换话题可以做不同的作品,这是一个有关记忆与中国现实的观念创作,张健君所用的材料和方法正好能呈现这种观念,比如,现在的城市规划把老区都拆成清一色的新区,而各个年代的建筑实物大多消失,而这种建筑的消失就可以用勾勒各个年代建筑的轮廓线而消失的结果来呈现;事实上张健君的这种方法可做的作品还很多,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政治人物,但很多政治人物由于各种原因被沫掉而不为后人所知晓,这像是一个历史记忆却失的国度,如果用张健君上面的创作程序,一个历史人物的画像画上去宣纸马上干了成一张白纸,又一个历史人物的画像画上去宣纸马上干了又成一张白纸,这样水墨材料不再是一种与传统文化题材相关的创作,而是为观念的媒材,即用这种性能的材料可以表达历史一次次成白纸状况。
案例分析方法一直在我的艺术评论中占了主流,我举这四个案例,想说的就是,其一、水墨作为图像,远比水墨本身要复杂得多,我们看到的是水墨,但影响我们或者说对这种水墨的价值认定却是水墨背后的意义系统,没有一个纯水墨的水墨画,其二,水墨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品种,而是一种讨论问题需要的方式,这就是说水墨是被我们所选择的,而不是水墨本身选择了我们。但我们目前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水墨现象明明是被意识形态所操控而不知道这是意识形态,我们明明可以将水墨作为一种问题加以讨论,或者明明在观念艺术中水墨只是观念艺术的泛媒体的一种的时候,现在的水墨好象都要服从水墨这个画种论,这就意味着我在这里重提水墨话题时,还有必要重提我这本著作封面上的一句话——艺术必须死亡。当然这个“艺术必须死亡”不能望文生义地去理解,这个水墨的死亡意味着水墨从语言转向了的话语。《艺术必须死亡:从中国画到现代水墨画》出版于2006年,是我的水墨评论的专著,包括了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写的论文。这本书可以作为我对水墨语言批判的结束和对水墨话语检讨的开始,也因此使得水墨领域的复杂性和问题的交织面超过以往任何的时代。
我们来看这些年来的水墨动向,《艺术时代》杂志在2009年第4期发表了曾玉兰的一组访谈稿,作为很重要的史料,发表时在每个艺术家的访谈上加了一个总标题为《现代水墨与民族性话语》,这组访谈稿最初是为张平杰策划的“水墨演义”展览而做的,发表在《艺术时代》时重点挑选的艺术家有刘国松、萧勤、仇德树、谷文达、宋钢、广曜,这些作者时间跨度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开始,中国内地的“文革后”中国画现代化直到当下的中国画领域的思想演变,而且这些艺术家的共同特征是首先在本土从事现代中国画,然后出国去欧美,或者出国后回国。他们还有共同的特征,早期都是**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然后不管留在欧美还是回到了中国,又差不多回到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尽管他们做的水墨是现代水墨或者突破了平面的水墨。针对这一现象,《今日美术》杂志在2010年第2期,发表了张娜的评论文章《现代水墨与民族性话语:希望还是死结?》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到了2010年5月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与朱屺瞻艺术馆联合的每年一度的新水墨大展直接用“水墨时代”作为展览总主题,而将这样一个学术话题推到风口浪尖上去。同时这次“水墨时代”展还推出了一个批评家论坛,水墨时代的到来成为了这次论坛的高调。然后《画刊》杂志2010年第6期又迅速发表了张娜对这次论坛的述评《“水墨时代”还需要到来吗?》。这些文献可以从某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的水墨话语现象,当然这种话语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更大的文化诉求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JDP世界第二,奥运会在北京,世博会在上海,大国崛起,新儒学本来就有中国文化复兴论的传统,而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的长篇演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并发表在《文汇报》2010年8月28日上,同样也在这样的时间点上说着与新儒学同样的话,也可见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再次呼吁,张汝伦在这次演讲的结尾说: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演讲现场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现在仍然可以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志气和抱负。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人类。人类今天也面临着有史以来的空前危机,西方文化不可能带领人类起出这个危机;相反,这个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具有最伟大的人道理想,只有这种人道理想,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张汝伦只是一个知识界的案例,张汝伦的这种言论归属于一个知识群体,在当前又形成了显赫的意识形态,水墨领域的文化复兴,也与张汝伦所属的知识界一样,用水墨精神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拯救人类文化的危机。当然,视觉领域远比知识界鲜活而具体,水墨与展览在今天的强劲就是一个证明,谷文达水墨展与“炼金术”阐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种文化推动力中的合力,其中所释放出来的话题,可以让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讨论。
当然在《艺术必须死亡》这本专著中,中国式后现代与新儒学的文化态度在水墨中的呈现成为了我的批判的对象,也是我介入水墨领域时对水墨作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作为肯定性的水墨,以水墨来肯定中国文化价值,一种是批判性的水墨,以水墨作为话题,用以反思水墨的旧有文化价值,这两种水墨创作范围扩大到装置和影像后也是一样,就装置和影像的水墨中也分为肯定性的水墨和反思性的水墨,肯定性的水墨,不管是水墨材料还是新媒体,都是为了展示水墨文化的魅力,道禅宇宙,玄学精神,而反思性的水墨,其实首先不是水墨,而是以这种水墨的问题情境为出发点,继而讨论这些问题。它是介入到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新的观点的,而不是反映已有中国文化符号的创作。
还是回到我开头举的四个例案,它至少告诉了我们,自从当代艺术的概念介入水墨领域后,水墨的所有系统,包括旧传统水墨与现代水墨系统都受到了挑战,随之而来的争论也会是无休止的,这种争论现在已经不是传统中国画与现代水墨水的争论,而是现代水墨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争论,甚至是当代艺术与当代水墨之间的争论,争论的内容也由单线条变成了多重性,原来是画种论的形态史争论,即跨中西的形态史争论,但进入当代艺术系统后,是关于要不要水墨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仅是有关水墨语言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也扩大到文化身份的问题,乃至水墨——包括现代水墨到当代水墨,在文化后殖民情境中构成了一种本土的焦虑符号,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种焦虑的升级导致了大大小小的被称之为当代水墨的展览,也在这个领域,水墨本身最直接地变成了文化身份的话语方式,而远远超出了作为审美的艺术这个范围,从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水墨领域,看似在为艺术而艺术,而其实是与民族身份政治结合得最紧密一个领域,尽管对艺术家来说,这种结合是在不知不觉中呈现的。
像张汝伦那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很容易催生这种水墨文化的复兴论,所以水墨就成为了新一轮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工具,事实上这种新一轮的文化保守主义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没有断过,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给新儒学的幻象以沉重的打击,像刘国松一再重复说,西方艺术把人搞得都不是人了,中国水墨艺术才是人的艺术。转头又要说,西方人要看中国自己艺术,这个艺术只有现代水墨能代表,又拿出事例说,西方也开始关心中国水墨了,像是久旱逢 甘露那样,这是一幕表面的民族民主,其实是最看西方脸色的一种行为。当然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前,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接受确实有所变化,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以来有着三次推进,西方最早介入中国当代艺术,是从政治波普和泼皮主义开始的,这是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解读的艺术,改变了以前汉学家热衷研究的东方神秘主义与传统艺术的系统,第二次对中国当代艺术跟进的是1990年代后期,对东方神秘主义的装置等空间艺术投以关注,艺术也从中国脸到中国文化符号。2000年以后,西方有意无地地开始对以水墨趣味和水墨材质为核心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认定,然后造成了现在的影响是,西方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水墨,这种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东方学解读的不断升级,从中国政治,到泛艺术的东方神秘主义,再到画种上的中国艺术,表面上进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深处,其实很容易把中国当代艺术在这种重视中不知不觉地降为土著艺术。所以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态度的这种变化,也使中国水墨也很快地被卷进了后殖民的漩涡之中,其实越来越缩小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范围,即假如说今天的水墨成为一种中国世纪的文化的话,那也是一种退缩性民族主义对后殖民秩序拥抱的意识形态。当然,这是我要强调的,对反思性的当代水墨来说,这种意识形态同样要纳入到其讨论的范围之内,当下的水墨现状多停留在肯定性的当代水墨之中,这种肯定又结合了西方态度的支撑后被放大而显得特别地强势,说水墨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其实是西方再一次在圈定中国当代艺术的类型和范围。
“主动现代化”与“被动后殖民”,“挣扎水墨”与“贴面水墨”都是我二十年来水墨评论中论述和区分两种不同水墨的关键词,前者当然是反思性水墨,后者当然是肯定性水墨,当然它同样涉及到身份的多重性和身份的固定性的区分,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方向就是要用身份的多重性来抵抗被规定的固定身份,如中国身份和中国艺术的身份,全球化与身份的跨国之后,身份的意识形态也变得错综复杂,而使得我们看到的是当代水墨,其实左右它的就是这种全球化后的中国身份及其处境。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墨状况,它能引起的反思是,我们能否在身份政治之外找到水墨(或者不叫水墨)的超越之路呢?说到底能否有一种离开画种论的主体介入而让水墨离开它的这种焦虑呢?针对这样的思考,我要说的是,当画种论的水墨已经终结了,水墨话语才更加复杂地展开,它到底会是怎样地展开,谁都无法预计,也许它根本就不需要预计,而只需要展开,展开到哪怕它不再是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