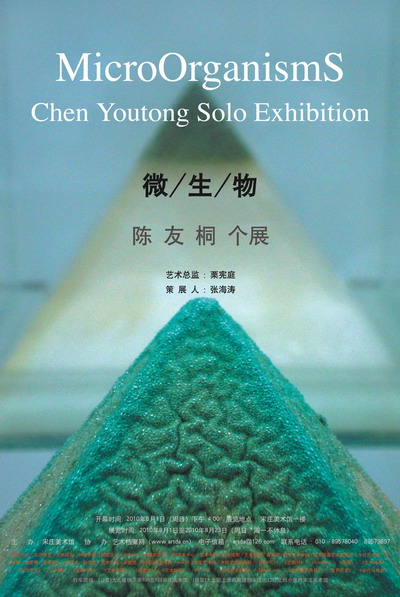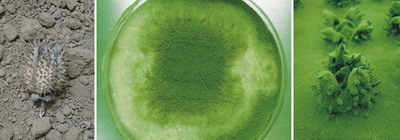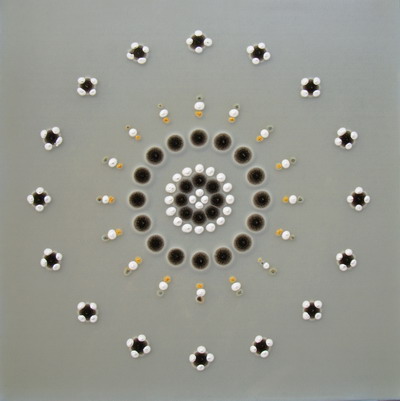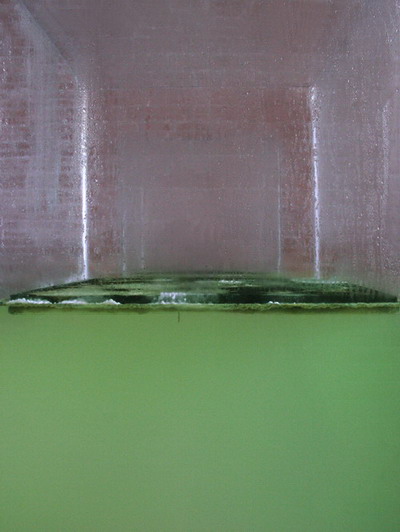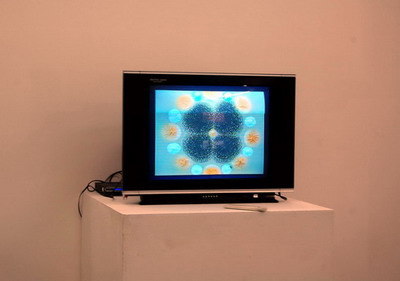Flowers Do Waves Thrash, Heroes Do Sands Smash
Interview with Song Yonghong
浪花淘尽多少英雄:宋永红访谈
时间:2008年3月3日
地点:广州汇豪社
人物:宋永红(当代艺术家)
何金芳(《画廊》杂志总监)
Thanks to Song Yonghong’s solo exhibition “Desire Plaza” shown in Guangdong Museum of Art, we could get a closer look at this *85 warrior. During the two-hour interview, Song threw his thoughts back to his bewildered youth, his struggling transitional phase and his refreshed perspective, which has reminded me a famous song form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The Great river rolls to sea, flowers do waves thrash, heroes do sands smash. When all the dreams drain, same are loss and gain”. As Song says: “I don’t want to push myself. After all those hustle and bustle, people will finally discover your true value.”
3月4号早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宋永红展览的开幕式在广东美术馆大堂举行。馆长王璜生亲自主持,而出席的嘉宾不乏当今最热的艺术大腕张晓刚、岳敏君、曾梵志等,还有张颂仁、黄燎原和张子康等其他大家熟悉的面孔。每人上台都简单而诙谐地讲一句话,可以说是开幕式最短的发言,引起大家一阵阵开心的笑语,气氛轻松而热烈。如今,大家在这繁忙的年代专程从北京飞到广州看展览,可以说是给足宋永红面子,同时也可见宋永红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
春节朋友聚会时听说画“洗澡”题材的宋永红要到广州来做展览,甚是兴奋。因为早在2002年因工作需要通过几次电话却没见过面,但“慰藉”系列作品神情诡异的人物,却让我浮想联翩。所以,听说宋永红到广州来了,赶紧约时间见面。两个多小时的交流,宋永红侃侃而谈。作为“85思潮”的老将,他一点也不回避历史,很真诚、坦然地谈到自己怎样游离艺术大潮,又是怎样走近让大家认可的“慰藉”系列,现在又是怎样走出“慰藉”,进行一次新的蜕变。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喧嚣之后,人们还是会发现你的价值”。
何金芳(以下简称何):这次在广东美术馆做的“欲望广场”可以说是你个人的回顾展吧,展出后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通过作品我们发现你的艺术历程里有几次重大转变,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惑?你是以什么心态去面对的?
宋永红(以下简称宋):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这是一个坚持的结果。当然前提是你要喜欢这个东西,这样就算在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也可以去面对,自然会想出解决的办法。
何:说起来好像挺轻松,只要去面对,自然就会想出解决办法。其实,2000年就像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你画了很多,但那种个人符号性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强烈,跟当时流行的艺术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呢?
宋: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创作的趋同方式,但我的想法其实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我要关注人,从主观的角度出发。像当时在搞毕业创作的时候,大家都画一个很边缘的或跟自己生活没关系的东西,画农村题材、西藏题材或新疆题材等,这就是当时的时尚。另外“85思潮”还在流行当中,大家就做一些很抽象、很哲学的大主题,我想从这两者中抽离出来,表达我所感觉到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以个人角度来感受的一个场面。我觉得艺术家应该从这里面走出来,不要和风潮有关系,如果非得有关系,那至少是作为引领者。
何:之前你也有过一段时间做不同的尝试,比如装置或其他一些观念性的创作,而且你的专业又是版画,为什么你一直坚持做油画?当时很多艺术家都愿意去进行这么一种探索,在语言、材料上面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当你坚守油画时,你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呢?
宋:油画只是一个工具,我需要表达的是我自己。如果我对摄影感兴趣的话,我可能会去拍照。我也没有去想它到底是一个传统的或是现代的媒介,只是觉得通过它,可以直接地表达我的感觉。艺术创作的本质是能表达你的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何:之后你有没有再做过版画?
宋:其实毕业后也想尝试做版画,但是没条件,因为做铜版需要一个工作室、机器以及各种酸剂等等。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木版我也不愿意碰,那样会特别折腾,会把你弄成技术工人。
实际上,版画这个材料不太好操作,要表达得好的话,就有一个技术问题,我希望我选择的材料是直接的,对我是有效的。
何:如果说直接的话,版画不是更有优势吗?毕竟你大学四年学的都是这个专业。为什么你会放弃版画而选择油画呢?
宋:版画所要求的技术性太强了。我选的是铜版印刷,其中技术要求很多,同时创作过程中有很多细节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会消磨你的情绪,你必须很理性地控制这个效果。但油画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虽然素描更直接,但素描所带来的感觉好像没有油画那么丰富。
何:我发现这是一个现象,很多艺术家都是从版画专业转到其他材料的,但这些人往往看起来会更有成就一点。
宋:上世纪80年代末实际上还有一个所谓“地道的油画”的说法,而版画系当时在学院里面正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专业,我觉得其实它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合并到选修课里面。这种尴尬的背景其实成就了很多人,你可以不带成见地自由创作。很多油画系的学生还在追求笔触、质感和油画的味道,我们却不受约束地瞎画,反而比较好。比如徐冰他早已不被材料所控制了,后来连“尘埃”都可以做成一件很出色的作品。
何:我看你《随笔》里面也很强调技术的处理问题,这个跟你的版画训练有关系吗?
宋:我觉得没多大关系。因为每一种材料都有它的技术性,而这种技术性是靠个人感觉去把握的,不是一种标准的技术性,也许这种技术性可能看上去会很糟,与传统相抵触,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何:其实这个过程挺难的,像你刚才所说的,有几年时间根本就无人问津,你坚持了几年的东西,大家还是不太在意,那段时间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宋:90年代末期时,整体局面并不是那么乐观。行为、装置艺术或者绘画,大家都处于消沉状态,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我记得那时我的小孩周岁庆祝,来了一百五十多人,那段时间大家都闲着呢。当时国内并没有那么多人去接纳这个东西,去国外的参展机会少,影响也不大。但2000年以后要搞个聚会可就难啦,能来15个人就算不错了。近几年开始名利双收了,大家才开始忙碌起来。
何:虽然你说那时候是一个大环境的消沉状况,但我从黄燎原写的序言了解到,那几年你也不怎么跟大家玩。你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受他们的影响呢?
宋:也不是,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和大家一起玩的。在1995之后那几年,出现了新媒体艺术,例如影像、装置和行为等,跟国际的风潮接轨了,同时也出现了那种所谓的“策展人”的展览,由策展人提出一个概念,艺术家们围绕这个命题来创作,在这点上,绘画就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绘画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挥而就。当时有很多新媒体艺术家活跃起来,绘画就有点渐渐被放凉了的感觉,自己也觉得有点被放凉了,因为别人的关注少了,展览也少了。而且那时搬到市中心去了,离大家比较远,所以我也犹豫了两三年时间。实际上是1996年以后从市中心搬到花家地,跟四川这群艺术家混在一起,才开始又有了一些艺术上的“碰撞”。
最后我也从困惑中走出来,明白绘画本身没有问题,它只是一个手段,跟摄像机或者其他媒体都没什么区别,我最终是想要表达自己的一种语言和态度。
何:其实那段时间对你整个艺术人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随笔》中,你也始终强调一点,对于“人”的认知,一定要通过生活中在一起的交流,这样的认知才是实实在在的。你在花家地这段生活,究竟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使你形成了2002年之后的那种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认同的风格?你又是怎样通过跟大家的交流,去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实现在回看过去,我觉得那可以说是一种危机。
宋:对,就是有了危机,才想冲破这个危机。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直觉得没问题的话,恐怕也不会改变自己。到了1999年的边缘时期,其实人是挺绝望的,觉得自己毁了,完全不行了,每天都在画室里徘徊、迷茫,却什么也画不出来。那时晓刚已经住过来了,有一次他指着一张“洗澡”的画,有意无意地说:“我挺喜欢这张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这色调挺单纯的,没有那么多东西,你的东西其实挺好的,但就是内容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的,你在画面里能不能就让人集中看一个东西”。我就说:“那色彩也可以简化了吧”。“是啊,其实色彩用一、两种颜色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是和素描有关系,就是很单纯地去表达一个东西,只不过它是用毛笔沾着油画颜色,在画布上去画。我已经接触了这种材料十几年了,技术上是没问题了,只不过是稍加改变思路,形象就呈现出来了,第二天就发生了令我惊奇的变化。这种主观化的东西是不需要参照现实的,我的作品90%都是想象出来的,这种靠记忆和主观概念处理的东西,使我一下子就自由了,之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画了。也不用去制造一个图式,只要是你主观上有感觉。比如看到一个人就幻想他在浴室里的一种情绪,一种状态,实际上就是自己的想法,觉得这人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会是什么样的,再把他主观化,视觉化。比如水,其实我在早期素描那一套时就已经开始画了,水从头上浇下来的时候有一种超现实的语言,现在再把这东西拿过来,揉到你当前的经验里面,就把它画活了,色彩上就自由了,任意选择一两种颜色,就可以很轻松地把握它。很简单,很单纯,只要表达一个东西就够了。画完之后大家都说不错,这样的作品很有意思。
何:这样说来张晓刚的话对你有点醍醐灌顶的作用?
宋:没错,在实践经验上他确实比我丰富很多,他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方法,他要的是民间化那种感觉,不追求经典。而且在语言上他转化了一个大背景,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他把意识形态的东西穿插到画面上,这是一个大手笔。
何:这个也涉及到艺术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管你用的是什么工具或方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张晓刚给你的启示就是艺术是需要提炼的,一方面是生活的提炼,另一方面是画面本身的提炼。这是需要长时间的,所以当我听你说这个转变是瞬间的,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宋:这是积累四年或更长时间的了。绘画其实有很多的文学性,我在做毕业创作的时候,有一本小说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百年孤独》小说里面魔幻现实的场景、时空交错以及名称的故意混乱等等都对我影响特别大,这个影响一直贯穿到1999年。但是,到了画“洗澡”这个系列的时候,这些就转化为材料本身的纯视觉的美感,没有了超现实性和文学性,就在那一刻把以前所背负的东西全都给甩掉了。它把之前思考过的所有问题通通卸掉,只是集中到视觉本身。但很奇怪的是,卸掉了这些以后,它反而把应该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了,既抽象,又具体,既跟人有距离,又是大家所熟悉的。找到这个切入点觉得很兴奋,一下子就组合出来了。刚开始时甚至每天都睡得很少,一直持续了二十天左右,特别亢奋。当时大家聚在一起,交流也容易,所以创作也特别兴奋。我没有固定一个符号,每一次的构图和画面都充满了偶然性,中间也画了很多失败的草图,大概有三四百张吧。
何:你为什么会选择“洗澡”这一个题材呢?比如说方立钧画的是大头形象,张晓刚画的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形象,他们这些题材都具有一个普遍意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中国特色的元素,以我看来,你的作品具有普遍性,但却没有一个很鲜明的中国特点,你是怎样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宋:我恰好就是要回避这一点。首先要找到进入的途径,这样前提就有了,之后我选择了一个自己在每一个创作阶段都会出现的东西。我发现“洗澡”跟我当时的状态特别吻合,我更重视个人的体验,而不想去执着于所谓的“中国的符号性”。比如我们今天看卡夫卡的小说,也没有认为他只是欧洲符号化的作家,主要还是看作品能不能打动人。黄燎原说我这样的选择很吃亏,但从长远来看我一点都不吃亏。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被抽离掉,剩下的只是画面,我们只会记得画面本身的魅力,而忘记了历史背景。
何: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好的作品除了画面本身,还有一个历史的厚度。比如说方立钧和张晓刚,除了看到他们的画面魅力,我们也可以通过作品来看时代,甚至是时代后面更多的东西。
宋:这一点对我来说真的不太重要。有些人是做历史的或搞哲学的,那种不是直接跟艺术有关系的人,他们可能会更关心画面背后的意义。但我个人认为,画面本身的审美直接给你的印象和反映才是最重要的。“洗澡”出来后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学术圈的人看了之后也产生了各种意见。老栗(栗宪庭)是很兴奋的,他说我对你有信心,其实你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出来,以前你的作品创作容易跟现实主义相混淆,图像太多。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一个大展里面,你的画让人一眼看见,在它面前停一分钟,你就成功了。比如你以前有些好的东西,就像看孔雀开屏,别人都在看前面,你就看到后面去,总是想找一个别人不太注意的角度,所以你的东西是成立的,不过我更期待你以后的东西。他的文章里面也有说到一点,这不是象征的东西,更多的是意象。好像唐诗里面表达的一种意境,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借景抒情,说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我的绘画不去直接反应社会和意识形态,但它是有这些因素包含在内的。人在社会上价值标准的混乱,精神上的迷茫,我切身体会到这些东西。当时我父母相继去世,人生无常的感觉,一种绝望,听起来像一个故事,实际上是经历生和死的一种感受。那时我的小孩又出生了,你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复制和延续,那种兴奋就像画了一张新画一样。那时候我也会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也影响到我的思考方式。
何:从近两年的创作来看,你慢慢地想放弃大家所认识的“洗澡”系列的创作主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宋:我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自己拴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自由度和丰富性对艺术家来说很重要。其实“洗澡”也画了五年时间了,一百多张,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也会枯竭的。绘画的主题就是这样,不是计划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回顾展”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是挺恐怖的,但又给我一个现场检视自己的创作历程的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有意义。
何:“慰藉”系列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琢磨出来的,画了五年以后又开始转型,你有没有考虑过外界对你的反应?收藏家又是怎么看待这个变化的呢?
宋:我不太管这个。也不是说以后就不画“洗澡”了,但除非还有什么新东西去刺激你才会去继续画。其实画这批新画比“洗澡”的难度大多了,很费劲,特别累,其实又开始焦灼了。
何:但我个人感觉你转变之后的新作品反而比“洗澡”更有意思了。你从意象的方面去理解,好像更多的东西可玩了。
宋:其实这是我的强项,透过画面去反映今天人们迷失的状态。我画画更多的是靠直觉和本能,我感受到了今天的广州和我第一次来看到的广州是不一样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广州是什么,这种东西你只有用更丰富的语言,才能表达得比较完整。
何:我们再问个敏感一点的话题,第一张画是什么时候卖出去的呢?
宋:最早卖画的时候应该是毕业创作的铜版画。当时浙美和旧金山的一个学院是姊妹学院,有一批外国的学生老师过来交流活动,看到有意思的作品就会买。当时是唐宋帮我联系的,大概是250元外汇券,买两张。第一次卖油画是1989年的“艺术大展”,一张叫“无人售票”的画,典型的超现实的感觉,一个美国人买了。当时卖画的人也不多,我的这张画卖了5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是两千块钱左右。那时候刚毕业没钱,基本工资加上代课费一个月也只有一百多块, 而且刚毕业时还借了好多老师的钱,所以拿回来的钱我立刻先把债还了,之后还给我妈寄了四百多块钱,我妈特激动,她说接到这个钱时还哭了!
何:你第一个合作的是什么画廊?
宋:第一个合作的画廊其实是汉雅轩。
何:张颂仁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当代艺术了吧!
宋:我听别人说,他最早的时候与一个东北的画廊合作,后来他认识了老栗,老栗就把他带到了当时内地当代艺术这个圈子,他们一起策划了一个展览,就是“后89艺术展”。
何:在这插一句,曾梵志对九十年代初的首届广州双年展念念不忘的,因为他获奖了。你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宋:那一次本来我也可能获奖,不过因为题材太敏感了,就只获得了提名。1993年我还错过了一次本来应该参加的威尼斯双年展,听说老栗当时和奥利瓦(国际知名的大师级策展人阿其烈•伯尼托•奥利瓦)都吵起来了。那天下午奥利瓦来选择艺术家,老栗说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现状,你不能只选择那种所谓带中国符号的东西。那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听了还是挺感动的。但我就是这样,不会很有谋略地去迎合主流,我是一个比较游离的状态,但游离之余你也要有值得别人注意的地方。喧嚣之后,人们还是会发现你的价值。
何:也难怪黄燎原要为你打抱不平。你们当初那批艺术家现在的拍卖价格很多都突破了百万、千万雄关,相比之下,你的价格还是比较低迷的。对此,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公平?
宋:没有,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的产量很少,这十几年的时间,我总共卖出一百多张画,价格上升不是很快,但我心里很踏实,这就够了。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一个本能的艺术家,重要的是呈现自己的作品的。
何:换句话说,也正是这种心态,伴随你一路走过,包括艺术创作和人生历程所遇到的困难。而与此同时,也因为你的真诚与执着,赢得了众多朋友的喜爱和尊重,是不是?
宋:我很“真”吗?哈哈...
评论摘选
黄燎原(现在画廊负责人)
当中国艺术大环境处于政治波普、玩世风潮的时候,宋永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能保持他个人的视角,这在当时是比较独特的。从1985到1990年这段时间,他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艺术家,但就是没有搭上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快车,这是他被边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张皓铭(收藏家)
在创作和正式的活动中,宋永红表现得腼腆、害羞、不善言谈,但私底下十分风趣机智。因此他才能在喧嚣的艺术市场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理念。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先锋人物,这是非常难得的。
张晓刚(艺术家)
宋永红从年轻时就是一个敏感的人,对生活的观察很细微,同时他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善于从生活中寻找细节,并把这些细节与他的个人想象结合在一起。2000年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那个时候的宋永红也在思考个人性与时代之间的联系,经过这些困惑和思考他的作品渐渐得到了超越,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他自己的东西。而这批新作表面上像旧有风格的回归,实际上是更深入地表达了个人的心理空间,是他对现实的个人性的重新解读。
选自《画廊》200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