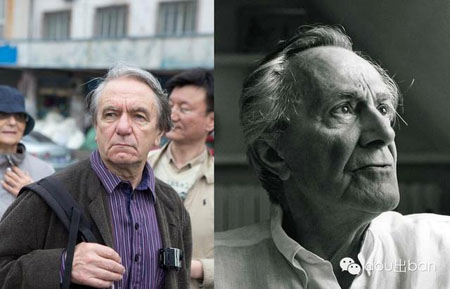
文/雅克·朗西埃︱译/蓝江
“一个世纪以来,艺术并没有将美作为其主要因素,它只有来自于崇高的东西”[1]。这个句子可以看作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关于艺术、先锋艺术及其未来的论文集《非人》(L’Inhumain)的论点的总结。这个句子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两种类型美学做出了彻底的区分。一方面,存在着美的美学,这种美学宣扬的是趣味判断的古典世界和大美的理想。但一种新的走向公众的展览和沙龙的出现,它们无视艺术的规则和趣味的原则,这实际上公开地废除了整个美的世界的合法性,这迫使康德的批判不得不考虑一些奇异的概念:没有概念的普遍性,没有终点的目的性,没有兴趣的快乐。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崇高美学考察了艺术可感材料和概念法则之间的矛盾。利奥塔甚至认为,这种美学提供了一种可维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先锋音乐和绘画的特有任务:去见证那些无法展现的东西。他将这个消极的任务,与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证主义的虚无主义做了对比,那种话语,在文化的名义下,在文明的业已废弃的理想中取乐。对利奥塔而言,美学上的美的虚无主义与作为见证崇高的艺术之剑的持续不断的冲突,是通过恢复绘画中的形象描绘(figuratif)或混合了抽象形式的形象描绘(正如我们可以在某些超先锋(trans-avant-gardisme)艺术或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nisme)艺术作品可以看到的那样)来实现的。
利奥塔引述康德的崇高概念,立即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地阐述这个问题。从康德的角度来看,崇高艺术的观念似乎是矛盾的。在康德那里,崇高并不决定艺术实践的产物。即便我们站立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前,或者站在吉萨的金字塔前,所体会到的崇高感并不会指向米开朗基罗或埃及建筑家的作品。它仅仅转达了这样的感觉,我们无法想象如何去把握作为总体的纪念物。不能想象如何符合理性地展现总体性,与在自然的苍莽面前的这种孱弱无力的感觉相比,会立刻将我们从美学的维度带向了道德的维度。这个一个标记,让我们想起了凌驾在自然之上的最高权力的事实上的理性,它也是在超感性秩序中的正当使命。于是,如何在理论上奠基一种崇高的艺术?相对比而言,如何界定这样一种艺术的特征,这种艺术超越了艺术的维度,进入到伦理的空间之中?
很明显,利奥塔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提出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去压制这个问题。他说道,“崇高,不过是在美学领域中伦理的牺牲宣言。”[2]而由此,他演绎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种灾难的背景下,什么是艺术,绘画和音乐,一种艺术而不是道德实践?”[3]我们下面来谈谈“牺牲”和“灾难”的问题。不过,首先你们要注意到,他正是通过这种概括问题的方法,来进行这样特别的歪曲。这个问题或许应当这样来想: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崇高的艺术?利奥塔用另一个问题取而代之:哪种类型的艺术会对应于这个范畴?一种作为“灾难的艺术”的崇高艺术的属性是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预料之内的回答。这个回答进一步实体化了崇高艺术的观念。
毫无疑问,将崇高感转化为艺术形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黑格尔已经通过将崇高变成艺术的属性,从而将康德的崇高实体化了。他不仅定义了一种崇高艺术,而且将感性表达的观念与能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一种原则,而他又将这个原则说成是象征艺术的原则:即艺术的观念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规定,而足以让其变成感性质料。即便如此,黑格尔的这种崇高的歧异(désaccord)就是康德根源中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的是各种“技能”之间的歧异,它指的是艺术家试图将之转化为言辞或石材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利奥塔的崇高,不同于此前的崇高。利奥塔指出,其力量就是感性本身的力量。美的艺术试图将观念施加于材料,而崇高艺术则在于去接近材料,“接近在场(la présence)而毋须求助于表达手段”[4]。于是,关键在于去直接面对感性材料本身的异质性(altérité)的问题。如何去思考这种异质性?利奥塔赋予其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材料就是纯粹的差异(différence)。这就意味着有一种不由任何概念上的规定性来决定的差异,如音色和色调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独特性对立于演奏的差异和主宰着音乐作曲或色彩和谐的规定性的差异。利奥塔给这种无法化约的材料上的差异一个意想不到的名称:他称之为“非物质性”(immatérialité)。
“非物质性的物质”(matière immatérielle)并非没有先例。这会让人们想起贯穿了从象征主义时代到未来主义的整个艺术思想的一个宏大主题:材料的问题变成了纯粹的能量,类似于思想的非物质性的能力,大观念的光芒与电的闪光融合在一起。我们也会记得,现象学会强调在那里(il y a)的光芒,强调即将出现的不可见的事件。但利奥塔的分析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目的。他旨在将康德赋予形式的属性转嫁给物质性事件。现在,在康德的“美的分析”[5]中,形式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无法获得的。美学判断所指的形式并非一种将自己的统一性强加于感性多样性之上的概念形式。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知识的对象,不会让感觉听从于理解的法则,也不是欲望的对象,即让理性听从于感觉的无序(anarchie)。这种既不……也不……的结构吗,对于理解和欲望这两种技能来说,都是不可获得的,这迫使主体,只有通过让那些技能的自由演艺,才能体验到一种新的自律形式。
利奥塔声称,对于音质和色彩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对康德而言,音质和色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判定,这是我们诸感觉振动所产生纯粹感官上的快感,还是依赖于其规律性的形式感觉的快感?利奥塔将他自己的思考作为对这个难题的最彻底的回答。他非常简要的指出,这就是对于所有音质和色彩都无法获得的美学形式。利奥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起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现代主义正宗派坚持主张一种与再现对立的可感物在场的独特性。那么,材质仅仅是“一小块皮革或一片木材,以及香料的芬芳,分泌物或一块肉的味道,也有音质和色彩”。不过很快这些东西看起来并非如此。“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交换的”,利奥塔说,“它们都决定了一个情感事件,一次遭遇,我们的内心对此并没有准备好,对之感到不安,这个事件对心灵来说留下的只有感觉,焦虑和狂喜,一种懵懂的亏欠。”[6]这-就是材料的第二种特征:这并不是材料的独特性,而是它有能力造成遭遇(faire pâtir)。它的“非物质性”并不在任何特殊的可感质性当中。它仅仅存在于所有可感材料的共同性之中:它们一并构成了“情感事件”。音质或色差的各自特有的质性,一块皮革或香料的芬芳的质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共同的力量,这种共同的力量让心灵无所适从,让心灵感到亏欠。
当利奥塔从康德对美的分析中借用了第一种属性,即非物质性时,这第二种属性很明显来自于康德的崇高分析。在赋予了音质和色差以某种形式上的自律之后,利奥塔也赋予了它们无形式(informe)的破坏性的力量,这是崇高体验特有的一种不谐的力量。那么,感受(aisthēton)就是统一的两个事物。它既是一个物质,也是一个符号。感官事件的纯情感就是我们因而需要去认识的真实的符号。音乐上的音质和色彩上的色差,就是康德认为金字塔或浩瀚无边的大海所具有的东西。它们标志着我们内心无法去把握这个对象。但这种不可能性的逻辑,在康德作品中,正好对立于既已存在的所是之物。对康德而言,这是一种想象,它揭示出我们在理解我们所面对的可感物的力量在形式上或在例外性上的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想象,我们没法去再现那个理性所需要展现的整体。所以,“感觉最大的能力”背弃了它在赋予理性大观念某种可感形式上无能为力。然而,在这个方面,它两次证明了理性的力量:理想可以穿透感性经验的局限,它也向想象要求想象本身所不能给予的东西。主体在感觉上所体验到的无能为力,证明了主体之中“无界限的能力”[7](faculté sans bornes)的出现。陷入无所适从的想象让心灵进入到一个超感性的使命当中。这种让自己从各种能力在美学上的自由演艺的自律性上升到一种最高的自律性:这就是在超感性的道德秩序中的正当理性的自律性。
利奥塔严格将这种逻辑套用在自己头上。在崇高体验中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是理性所承受的感觉。它体会到它无法“接触材料”,换句话说,它不能理解这种彼此依赖的感性事件。这种崇高体验告诉我们:“灵魂成为了依赖于可感物的存在,因而可以被践踏,被羞辱。美学的前提就是受制于感受,没有这种感受就是麻痹。要么因对他者的震撼而觉醒,要么被彻底消灭……灵魂被囚禁在濒临死亡的恐惧与饱受奴役的存活之间。”[8]然而,我们必须理解的是,这种感觉限制,并不是它施加的唯一限制。正如在康德那里,崇高的感性经验是其他东西的标志。它引入的是主体同规律的关系。在康德那里,想象的失败不会带来合法化心灵的自律规则。在利奥塔那里,其逻辑正好被颠倒过来:屈从于感受标志着听从于多样性的法则。感性情感就是“亏欠”的体验。伦理经验就是一种不诉诸大他者的法则的屈服。它展现了思想相对于内在于和先于心灵的力量的受制状态,而心灵根本无力去理解这种力量。
或许得出利奥塔误读或误解了康德是无关紧要的。但首要的问题毋宁是:为什么他需要康德?他为什么要在康德的文本中寻找在那些文本中很难找到的东西:例如先锋艺术理论,并期望在这种先锋派理论中证明主体的可悲,证明一种作为异质多样性法则的道德法则的观念?事实上,这就是利奥塔崇高理论所提出的悖论。这个理论是作为现代主义传统的延续而提出的,因为它赋予了先锋派一个任务,去捍卫艺术上的新,而反对恢复某种过时的表达形式,和与商业化的美学妥协的形式。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利奥塔而言,界定先锋派艺术的,就是对折中主义(éclectisme)的拒绝,这种拒绝在新绘画潮流中展现出来,画家在画布上综合了形象和抽象的主旨。然而,他赋予先锋派的新任务基于这样一种艺术观念,即这种观念证明了人类心灵自古以来就依赖于无法把握的当下,和拉康一样,利奥塔将这个当下称之为“大事物”(la Chose)。
我们如何思考这种悖谬的衔接?一方面是艺术的革命,它的高歌猛进宣布回到艺术的旧形式上,另一方面是他指派给艺术的任务,即证明了我们心灵无法超越切自古以来就遭受的奴役。为了理解其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考察利奥塔的主张,即他所反对的,被他视为是无耻的在绘画中混杂了抽象和形象主旨的形式,即超-先锋派:“在同一个层面上混杂了新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与抽象、抒情或概念主旨,这意味着一切都是等价的,因为一切都有利于消费。这是一种新的企图,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趣味’,并对之加以赞赏。这种趣味根本就不是趣味。折中主义所号召的东西,就是杂志读者习以为常的东西,就是标准工业形象的消费者的需求,这是一种超级市场顾客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博物馆和画廊的老板,通过批评,对艺术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后现代主义在于,让绘画的探索与事实上的‘文化’ 状态保持一致,并取消了艺术家们在探索不可展现之物的问题上的职责。如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才是唯一值得研究的问题,它是即将来临的世纪的生命和思想中的关键问题。”[9]
究竟是什么让他有可能判定,这样的趣味并非一种真正的趣味?利奥塔回答如下:如果它是一种趣味,我们必将失去艺术的历史责任,以及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世纪的思考的任务。简言之,它之所以不是趣味,是因为它不应成为一种趣味。这个主张很容易理解,它直接来自于阿多诺。利奥塔反对绘画折中主义的主张,正好就是阿多诺反对音乐折中主义的主张。他的话回应了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Philosophie de la nouvellemusique)谈到的减七和弦[10](accord de septième diminuée),在音乐上,这是耳朵所不能承受的和弦,“除非一切都是欺骗”。在宣布了不可能在绘画中将形象主旨与抽象主旨融合在一起之后,利奥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最著名的就是阿多诺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11](Clement Greenberg),他们将彻底的艺术自律与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诺言结合联系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传统经常被捍卫,来反对一种传统的对立,即在为艺术而艺术与艺术关涉政治之间对立:我们知道,艺术之所以是政治的,因为它仅仅是艺术。艺术仅仅是这样,通过其可感的构造以及对其特有的理解方式,它生产出某种完全不同于消费对象状态的对象。
之所以诉诸康德,正是为了通过这种差异,在可感物的状态中进行思考。康德主张,美必须与善分离开来,善既来自于概念,也来自于令人惬意舒适,而美则属于感觉。无论是阿多诺还是利奥塔,在他们的立场上,坚持认为艺术作品不应是令人愉悦的。艺术作品是欲望所不能获得的东西,而欲望本身会将所获得的东西加以消费。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不可获得性,这些作品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善。艺术是一种异议(dissensus)的实践。通过异议,并不是在一个因果关系中排列其位置,在这个因果关系中,艺术作品获得了其特有的质性,并与一个外在的善相关联:未来的解放(阿多诺)或对新世纪规定的要求作出回应(利奥塔)。
在阿多诺和利奥塔之间,发生了一次逆转。阿多诺将这些异议称之为“矛盾”。内在矛盾就是产生了艺术产品和主宰商业美学的折中主义之间的对立。它赋予了艺术作品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是力量,另一方面是缺少力量:一方面是自足的力量,它与商业上的异质性针锋相对,而另一方面是缺乏力量,这种不足阻碍其在自足中得到满足,并证明了将劳动和消费分隔开来的构成性异化。在利奥塔那里也是如此,艺术的任务仍然在于构成一个特殊的可感世界,这个世界分离于由市场法则所支配的世界。但在这里所涉及的异议,不再是矛盾。它现在被命名为“灾难”,这个灾难是“原初性的”:它证明了异化不再是那种面对资本主义将快乐和快感分离开来的东西,而是专属于人类动物的依赖性的命运。而先锋艺术唯一的责任,就是在无限期地记住它。
这让我们可以理解,利奥塔的对康德的反读,他将康德的崇高变成了将艺术上的先锋派与异质性的伦理法则衔接起来的东西。为了完整地理解其意义,就必须要重构其解释的链条,而这就是这个链条上最终的一环。反过来,我们需要将其理解为一种誊写,即他为了抹除第一次对康德的读解,也抹除了他的作品的内在的“政治”。按照这个说法,他分配给艺术的任务在于,记录下感受的震撼(choc),而这种震撼是“奴役条件”的不可磨灭的证据,而这正是对席勒在“审美状态”(état esthétique)的悬置中所看到的自由的新承诺的颠倒。
这个《审美教育书简》(Lettres surl’éducationesthétique de l’homme)的核心论点在于同样的双重否定,而这个双重否定中正是康德美学判断的特征。可以说,康德的美学判断既不从属于理解力的规则,它将概念上的规定强加于感性经验,也不从属于感性规则,它需要一个欲望的对象。审美经验同时悬置了所有的法则。所以,它也悬置了通常会架构认知、行为、欲望主体的经验的权力关系。对于席勒来说,这意味着在审美经验中,是各种技能之间的“协调一致”(accord),并不是利奥塔所宣称的形式与材料的古老和谐关系。相反,它是与这种古老主张的决裂,它是一种真正的支配形式。在它自身中,在认知和想象之间的“自由协调”(libreaccord)本身就是一种不谐或异议。根本不需要看到对尺寸、力量或恐惧的崇高体验,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思想和感性之间的不谐关系,或在吸引和排斥的游戏中奠定现代艺术的激进性。在康德从既不……也不……出发的美学判断理解中,美的体验已经由吸引和排斥的双重关系所概括。它在于对立的两项之间的张力关系,我们知道,魅力产生了吸引,而敬意让我们与之保持距离。席勒说,雕塑的自由表现同时既吸引着我们,又通过它本身自足的庄严,让我们与之保持距离。同时发生的反作用力运动将我们同时置于完全宁静和极度的亢奋状态之中[12]。那么,在美的美学和崇高的美学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断裂。异议,思想和感性之间协调的断裂,已经处在美学和谐和安宁的最核心之处。
和谐和不谐之间的同一性正是席勒赋予“审美状态”以一种凌驾于康德的共通感(senscommun)所包含的社会中介的承诺之上的政治意蕴,康德指望用共通感将精英的阳春白雪与百姓们的下里巴人统一起来[13]。对席勒而言,美学上的共通感,也就是异议的共通感。它并不会倾向于将差异巨大的阶级凝聚在一起。它挑战了产生这种巨大距离的可感物的分配。为什么女神的雕像会同时吸引着我和排斥着我?因为它展现出某种神圣的特征,席勒说,这也是人性的圆满:她并不劳作,她只是展出。她既不屈服,也不抵抗。她不处于命令的关系之中,同样,她也不处在顺从的关系中。不过,这种和谐状态与那种主宰着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立的,那种状态分配给每一个人一个地位,将那些发布命令的人与那些听从命令的人区分开来,将欣赏阳春白雪的人与欣赏下里巴人的人区分开来。审美经验的异议的共通感对立于传统秩序的和谐一致,也对立于法国大革命试图强加的和谐。法国大革命希望颠覆古代统治秩序。然而,它本身又生产出一种古代逻辑,根据这个逻辑,需要给那些被动的材料增加积极的智慧。反过来,对权力的悬置,专属于审美状态的既不……也不……,宣扬一种全新的革命:一种感性存在的革命,而不仅仅是颠覆国家的形式,这场革命不仅仅是接管权力,而且是将让权力得以实施的形式加以中和(neutralisation),既颠覆了其他权力,也颠覆了自己的权力。美学的自由演艺——或中和——界定了一种新的经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感性普遍性和平等的形成。

阿多诺的《美学理论》
阿多诺的美学和利奥塔的崇高反—美学所激活的张力关系,只有当我们回到其原初场景中,才能完全理解清楚,这个场景既用于奠基艺术的自律,也在一种例外的感觉经验中许诺解放人类,在那一刻,主宰着其他感觉经验形式的主动/被动和形式/材料之间的对立完全被废除了。这种张力关系必须理解为是对席勒的双重关系的延续,席勒将其置于他理解的康德意义上的各种技能协调一致关系的中心。其理由在于,这种双重关系确保了康德共通感所特有的媒介被转化为新存在形式的实际原则。由于这个双重关系,美学上的“自由演艺”不再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中间状态,或者是一个道德主体自我发现的舞台。相反,它成为了一种新自由的原则,它可以超越一切政治自由的自主性。在根本上它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元政治(métapolitique)原则,它对立于所有的颠覆国家的起义,它提出的是活生生的感性世界中的形式革命。
在阿多诺美学中的矛盾和利奥塔美学所宣称的“灾难”,恰恰应该被理解为美学-元政治的化身(avatars)。它们都有内在于“人的审美教育”观念之中的原始张力关系而引出的终极形式:这是在对审美状态特有活动的悬置与用来实现其诺言的自我教育活动之间的张力关系,是经验的差异性(altérité)和教育的自我性(ipséité)之间的张力关系,或者也是自由表象的自足性(auto-suffisance)和新人类的自我解放运动之间的张力关系,新人类渴望将表象同其自足性撕裂开来,并意图将其变成现实。席勒的最初情景已经包括了这个矛盾。雕塑自足的石块的差异性,预示着石块所是的状态的对立面。对于按照劳动分工、职业和等级来划分的人群来说,预示着有一个不再存在审美经验上的差异性的共同体降临,但在这个共同体中,艺术的形式会再一次变成它曾经所是的样子——或者它们曾经被认为的样子:一个未分化的集体生活的形式。在审美经验中的相遇,所遇到的他者不过是与他自身相分离的自我。因而,强调经验自主性的差异性和异质性被抹除了,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选项。既不……也不……的异议的共通感变成要么……要么……:要么永远将人类主体一分为二,要么恢复人类的总体性,要么是那种主体,他被动地思考如何用没有丝毫生命气息的大理石来进行丧失了总体性地进行再现;要么成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在真正的生命中来寻找如何重新获得自己,因而创造一个新的鲜活的世界,在那里,正如马列维奇(Malevich)所做的那样,规划新的集体生活,来取代“古希腊的老妇人”。要么异议被还原为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冲突,要么为了将艺术的表象转化为共同生活的现实,而形成一种新的和谐,换句话说,将这个世界变成人类活动的产物和镜像。
这样,为了恢复美学上的双重关系,就要制定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计划,一种可以取代主宰阿多诺美学的审美政治的形式,而利奥塔的美学矗立在阿多诺美学的头顶上。我们可以将这种反-运动的原则概括为两个基本要点。首先,要恢复美学的区分,或美学的奇异性,这可以让美学单独承担一个新的感性世界的诺言。如果最艰巨的艺术自律性的对手往往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因为在对艺术的热爱和社会解放的要求之间存在任何和解的精神或内在的冲突。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准备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相反,这就是两种彼此对立的审美元政治的形式。在这个对立中,解放的承诺与审美形式在感性上的异质性关联起来。这种异质性,重新激发了凌驾于被动材料智商的知识形式的权力,而这将再现性艺术的生产和理想同统治秩序关联起来。这就是包含在美学的既不……也不……之中的东西:当然这不是艺术的纯粹性,而是审美经验相对于权力游戏和统治形式而确立的纯粹距离。这并不是要把艺术的自律与政治的差异性对立起来。模仿的艺术在秩序中获得其自律性,这种秩序将其边界和等级与主流秩序联系起来。相反,美学时代的艺术宣布,它与主流经验的形式是不同的。但它是通过抛弃了将艺术对象和世界上的其他对象区分开的边界来做到的。所以,在自律性和异质性两种关联关系之间形成了对立。美学自律是一种艺术自律,在那里没有界限,将致力于创造高等艺术的画家的行为,同取悦民众的杂技演员的表演区分开来,也不会将创造了纯粹音乐语言的音乐家同致力于实现福特制生产线的工程师区分开来。如果在简单的国家主义表达“电气化+苏联”之下,生命-艺术(l’art-vie)的元政治消失了,那么维系这种异质多样性的元政治的选项,本身可以在这样的表达下来把握,即“十二音技法(dodécaphonisme)+卓别林的拐杖”:纯粹的音乐语言指向任何它自身法则之外的东西,以及在高等艺术中来提高演员的表演技能;而音乐材料从属于一个比福特制生产线更为严格的规则,一个夸张的流浪汉小丑,其行为姿态已经被自动化了,这些表演都表达了一种拒绝的情感,对机械化生活的“保守的”拒绝。
勋伯格与卓别林:那个拄着拐杖,八字脚走路的小丑,在井然有序的十二音中踽踽而行。这个表达或许可以总结阿多诺《美学理论》中的冗长而复杂的分析,即它也概括出这种反-美学的主要特征。其中,审美经验的双重关系成为了作品本身的内在矛盾。席勒的吸引和排斥的双重运动——即“优雅”和“尊贵”——成为了作品本身的自然趋势。其理由非常简单。阿多诺与席勒有着同样的中心前设:废除标志着劳动和快乐之分,受驱使之人与有教养之人之分的劳动分工。对于他而言,创作成为了在古希腊雕塑中,在最高的激情澎湃和心神宁静中自由表象所预示的东西:即有这样一个世界,西方理性的原初场景所象征的劳动和快乐的区分,被彻底抛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水手坐在长凳上,塞住他们的耳朵,不让自己受塞壬歌声的魅惑,而尤利西斯,将自己绑缚在桅杆上,独自欣赏这美妙的歌声,但他不能让自己的下属解开自己,让自己走向这些女妖。如果创作承诺要进行这种和解,只有通过不确定的延搁(différer),通过拒绝一切和解的形式来获得,在那些被拒绝的和解形式中,主流仍然隐匿地起作用。如果创作就是许诺,这并不是因为自足性包含着一(une)的生命形式的秘密。相反,这是因为它本身是分裂的,因为其自足性不得不在隐约中重复上演区分了被绑在桅杆上精于算计的主人和拒斥了听众的塞壬之间分裂的原初剧情。走向解放之路就是让这个分裂进一步恶化的道路,它所提出的美的表象是以不谐为代价的,其不明确地重新认可了异议的价值,也是通过拒斥了美与快乐之间所有调和形式来获得的。美学的场景,严格来说,就是不可调和之物的场景。
这些不可调和之物就是利奥塔所读到的东西,对不可调和的确证,就是美学的最高成就,它完全颠覆了美学的元政治。当然,这种颠覆不能在“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下来理解。在利奥塔的作品中,后现代不能作为一种艺术或理论的旗帜,它顶多只能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和一种诊断。这个诊断具有一个根本作用:从政治解放中将艺术现代主义解脱出来,释放出艺术是为了让艺术与另一种历史叙事相关联。利奥塔著名的对“宏大叙事”和“绝对的牺牲品”的驳斥,绝不意味着是他对细微叙事的诸多空间让步,去亲近多元文化的灵魂。它仅仅是“宏大叙事”和“绝对的牺牲品”的纯粹而简单的改变,按照这种改变,西方现代史不再被等同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而是等同于犹太人被有计划的灭绝的历史。
利奥塔也谈到了先锋派,让先锋派去追溯将艺术生产同其对象、影像和商业娱乐区分开来的线索。但在这种情形中的艺术的“自律”不再是证明需要被消灭的异化的矛盾情景。艺术家们所生产的不再是矛盾的游戏,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对震惊的刻画。震惊仍然是一种异化,但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异化。双重关系不再是创作的一部分。相反,它是一个前提的标志,即从属于可感物的前提的存在物的标志:要么从属于强制着我们的感受,要么就没有这种感受,亦即死亡。如果艺术就是将自己同商业区分开来,这仅仅是为了将商业消费所提供和承诺的东西,与听从于大他者的规则的心灵原初的 “悲怆”对立起来。这就是为了证明一个不可能减轻的异化,这种异化,任何试图从中解放出来的意愿,都会变成主人的意愿,让我们从消费的纸醉金迷的美梦般的生活中唤醒,而这只会将我们抛入到极权主义的命中注定的乌托邦之中。
所以,利奥塔的反读康德,是一种最理所当然的抹除审美经验的第一种政治解读的企图。他所要做的,就是抹除美学悬置和解放许诺之间的原初关系。他试图一次性地将既不……也不……颠覆为要么……要么……。在这一点上,席勒以此标示出一种例外的感性经验形式,相反,利奥塔要求我们读出一种共同前提的简单证据。与对主人形式的悬置不同,利奥塔要我们理解,我们受制于一个专横跋扈的主人。席勒将美学上的双重关系中的解放许诺,与“自由或死亡”革命性表达的切分对立起来。利奥塔通过颠倒为自己的形式“奴役或死亡”,从而改变了这种双重关系的切分。席勒自己在康德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主流统治的永恒与造反的野蛮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他重述了康德的观念,按照这个观念,审美经验指出了其他东西:分别是理性合法性或一种感性共同体的形式。利奥塔保留了符号的功能,但仅仅是为了颠倒它。审美经验成为了人类受奴役心灵的经验,心灵成为了感性的奴隶,而且也首先在对感性依赖性的考察中,它受制于大他者的法则。例外感觉的震惊感,在康德那里,是自由的一个符号,在席勒那里,是解放的承诺,在利奥塔那里,完全是相反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依赖性的符号。它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遵循自古以来的异化法则。如果先锋派使命是不明确地重新刻画出这个分割线,这是为了消弭解放的噩梦。这使得审美异议的意义需要重新概括,要么是一场灾难,要么是另一场灾难:要么是崇高的“灾难”,要么是相对于自古以来的大他者的法则在伦理上依赖性的“牺牲”宣言;要么这场灾难就是天生忘却灾难的灾难,解放承诺的灾难要么走向纳粹和苏联集中营中的野蛮,要么是商业文化和传播媒介的世界中的柔性的极权主义。
因此,艺术仍然需要在元政治的剧情中来刻画自己。但这个剧情的意义被完全反转过来。艺术不再带有任何承诺。为了纪念阿多诺,它仍然被视为一种“抵抗”形式。但这个词已经具有全新的意义。抵抗仅仅是“大事物”的记忆,在业已写就的字里行间中,在业已画成的画笔中,或在音乐的音质中,重新记述了从属于大他者的法则。要么听从于强加于我们之上的大他者的法则,要么纵情于自我的法则,让我们受到商业文化的奴役。要么是摩西的法则,要么是麦当劳的法则,这就是崇高美学对于美学上的元政治的最后的言辞。无法确定的是,这种新的摩西法则,是否真的对立于麦当劳的法则。但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在今天伦理学的名义下所实现的唯一法则下,它完成了对美学和政治的共同镇压[14]。
注释
[1] Jean-françoisLyotard, L’Inhumain, Galilée, 1988,p. 147.
[2] Jean-françoisLyotard,L’Inhumain, Galilée, 1988,p. 149.
[3] Jean-françoisLyotard,L’Inhumain, Galilée, 1988,p. 150.
[4] Jean-françoisLyotard,L’Inhumain, Galilée, 1988,p. 151.
[5] “美的分析”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第一卷——中译注。
[6] Jean-françoisLyotard,L’Inhumain, Galilée, 1988,p. 153.
[7] Emmanuel Kant, Critique dela faculté de juger, tr.fr. A. Philonenko, Vrin, 1979, p. 97-98.
[8] Jean-françoisLyotard, Moralitéspostmodernes,Galilée, 1993, p. 206.
[9] Jean-françoisLyotard,L’Inhumain, Galilée, 1988,p. 139.
[10]减七和弦是一个特殊的和声语言材料,它由四个连续小三度叠置而成,其特点是无明确的倾向性。根音到七音的减七度音程,有显著的悲哀忧郁的特质。这也就决定了减七和弦的色彩特点,它的一般的情绪效果是具戏剧性,富于热情,常带深度的悲怆性。减七和弦早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中已被引用。那不勒斯乐派首领A.斯卡拉蒂的一首康塔塔的开始部分,短促的、时断时续的变音旋律,加上飘摇不定的减七和弦音响,表现出—种愁苦不安的情调——中译注。
[11]克莱门特·格林伯格(1909-1994)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也许是该时期整个西方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由于他的主要观点代表了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法典化,他便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几乎所有同情或支持现代主义的人都为他辩护,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首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他。著有《艺术与文化》、《朴素的美学》、《格林伯格艺术批评文集》)等——中译注。
[12]Schiller, Lettres surl’éducation esthétiquedel’homme , tr. fr. P. Leroux, Aubier, 1943. p. 209.
[13] EmmanuelKant,Critiquede la faculté de juger,tr.fr. A. Philonenko,Vrin, 1979,p.177.
[14]这篇文章原版是英文版,是朗西埃在2002年3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埃文斯通分校召开的“康德判断力批判和政治思考”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