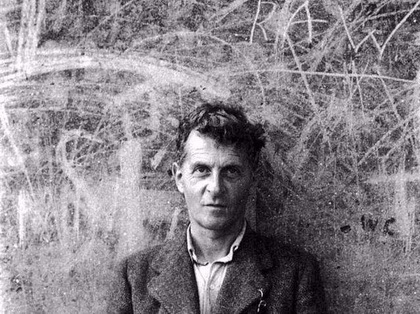
▲ 维特根斯坦
节选自“后现代哲学梳理”
许晟
后现代哲学显然不是由任何一位哲学家建立的。它更像是由各种出发点不同的,对西方既有哲学脉络的总体批判,以及批判思路本身的发展所构成。它往往由怀疑过往的定论开始,例如对古典哲学,历史叙事,或者文学写作的怀疑和分析;并常常重视不同因素之间相对化的关系或力量,强化个人化的论述方式。哲学家所讨论的往往不在是某种“真相”或“世界观”,而是将这些结论被建立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同时,不同的“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是相对的,它们的内涵需要由属于这些“主义”的,不同哲学家的论述来具体表现;可是,对这些哲学家阵营的划分和概括,也时常并非哲学的本意,而更像是为了论述方便而产生的归类法,这是在了解后现代哲学时需要注意的。同时,许多相关的概念并非由最早提出某种学说的哲学家本人所创造,而可能是被借用,或者在后世的追溯中被归功于某位哲学家的。因此,概念与学说的关系也是本文梳理的要点之一,它能尽可能还原概念背后的思想,避免概念化的归类法影响对学说的认知。

▲ 尼采
虽然“后现代思潮”主要开始于1960年代,但它的哲学脉络却可以追述至更早的时间。索伦·克尔凯格尔(Soren Kierkegaard)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写作开始于19世纪,他们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也因此被视作后现代哲学的先驱——虽然后现代的哲学家们在后来呈现了普遍的反存在主义倾向。克尔凯格尔最早提出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在此立场上,人必须靠自己的行动,感觉,和一切切实的经验,赋予自己确切的真实性;并通过建立在自由之上的选择,来确立自己的本质和身份。由此,人可以坚持任何无法被证明的信念。他也最早提出了世界的荒诞性,因为每个个体在获得经验之前,世界都是无意义的。同时,他还认为人的行为应该与自己的思考一致,这一点可以被看作是基于“知行合一”的要求;它可以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但也可以是一种践行理论的方法,或者说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
实际上,克尔凯格尔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是被追溯的。这一概念出现在后来的1940年代,被用于描述萨特(Jean-Paul Satre)的学说,而萨特也接受了这一名称。但史蒂文·克伦威尔(Steven Crowell)在后来的追述时却认为,这一学说源自克尔凯格尔,甚至可以在本质上追述至苏格拉底。萨特深受克尔凯格尔的影响,认为人不由造物主所创造,并且是完全自由的,因此,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基于“人性”的预设,而必须是由自己完全负责。他由此也提出:“存在主义”即是“人文主义”。萨特分析了人在生命历程中的总体经验与当下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由此完善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焦虑和绝望的本质,就在于人没有预设的价值与信念可参照,或者已知的参照已经失去意义。和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他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一种“糟糕的信仰”。由于最初就加入了尼采的虚无主义倾向,存在主义经常与虚无主义相结合,并对二战后的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存在主义”在艺术创作层面的影响,相比其学说本身,也许在后现代的思潮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 萨特
后现代思潮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20世纪早期的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受到亚洲哲学的影响,并首先于1927年前后,推翻了西方哲学关于“主观”和“客观”的基本观念,将自己的哲学置于与柏拉图相同的起点上,也因此被认为是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欧洲哲学传统对“本体”的一贯认识,将基于广义的,可感知的“现象”的经验,看作一切知识的基础。由此,他将“存在”重新放置在时间和感知中,将人放置于存在的核心——又并非决定性的——位置。也许是无意的,但他却打破了之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方式的论述,将其推进到新的层面:人的经验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一种过程,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正是重新认识“存在”本身的关键。他自然也推翻了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主义学说,指出真实来自被发现的过程,因此“思考”或“理性”也只是发现的方式之一。同时,海德格尔将语言称为“存在之屋(house of being)”的学说,十分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哲学的发展。
在随后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学说来自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理查德·罗尔蒂(Richard Rorty),心理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人;福柯(Michel Foucault)虽然常常被归入“后现代思潮”,而他个人是拒绝这一点的。其中,德里达,利奥塔,罗尔蒂,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都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当然,从学说的传承来说,这些人都不是海德格尔的学派继承者,只是受其启发,沿用了他的一些逻辑方式,并开辟了新的学说,这在认识欧洲哲学的基本关系中是很重要的一点。
维特根斯坦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他在自己于二十世纪初期完成的学说中认为,只要找到一种可以描述“命题”与“世界”的关系的逻辑,或者说,一种语言方式,就可以解决一切哲学问题。在二战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而这些直到他去世后两年,才在1953年出版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得以完整呈现。他将语言作为一种游戏,而语言自身在游戏的模式中发展并起作用。他认为哲学的问题在于,哲学家试图让词汇独立于它们的背景,存在于形而上的陌生环境中,而这会使语言失去作用。他认为语言必须回到各自的环境中,与环境经验共同发生作用,而这样会使哲学问题得以“消解”,而非被“解决”,因为最终的目标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消失。这相当于否定了自己早期的努力,甚至也否定了哲学研究本身。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并没有受到太多著名的非议,他所引发的争论往往在于对学说的解读方式。例如,“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理论认为,“哲学研究”中的论述是一种启发,而非任何实质性的哲学论述,只是为了让读者不受到思维陷阱的困然;然而汉斯·J·格罗克(Hans-Johann Glock)却认为,这违背了维特根斯坦自己所强调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洞察”。
在早期后现代思潮中,罗兰·巴特的思想转变更具有代表性。在1940年代,他延续了萨特(Jean-Paul Sartre)对写作的质疑,认为不断更新写作方式和避免风格化,是唯一的创造性写作。由此,他认为调查既有文本的写作方式,发现其中的转变与相互关系,要比理解文本的内容本身更能发现真相。而“前卫”写作正是通过写作方式所透露的,明确的主观痕迹,让读者保持了客观的视角。因此,他也主张艺术应该是对世界的批判和质疑,而非解释。之后,他通过结构主义的方式,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将它的价值观变成一种“客观真实”,普遍地灌输给整个社会,这似乎也在后来影响了鲍德里亚的学说。

▲ 罗兰·巴特
巴特在当时所沿用的结构主义逻辑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可以被看作是对存在主义学说的延续。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被看作是结构主义的主要奠基者,而这一概念似乎最早出现在人类学家克劳德·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研究中,并影响了这一思想运动。结构主义学说以语言的基本结构和模式为出发点,将人类文化,以及人的行为,思考,感知,感觉等等,都置于其相互关系,以及某种包含一切的抽象系统和逻辑当中。正如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所总结的,结构主义相信,人类生活的一切现象都只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被理解;而这些关系构成了固定的结构和规范,包含着一切具体的现象和文化。这一体系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评论,经济,建筑等领域都得到了实践,代表人物包括勒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等。
随着对结构主义的实践,巴特也发现,这一方法虽然可以将论述“格式化”,并由此进行对论述的分析,却并不足以是科学而可靠的。他对结构主义的逻辑关系所依赖的,符号和象征的固定关系的质疑,让他对“西方”文化对永恒结构的信念,以及对其它不同结构的文化的排斥性,都产生了质疑。他在1966年到达日本,发现日本文化并不追求某种永恒结构所必要的,超验的“能指”,而只是保持最“自然”的意义。他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则跳过了量化写作的努力,开始了他“中立化”的写作实践,不断试图改变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一种不依赖既有沟通系统的写作方式,这标志着他的思想朝着“后结构主义”转变。巴特受到的主要批评来自他对现代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的评价,他认为哲学家们都在回避思想与哲学的相对性,而这一观点被丹尼尔·戈登(Daniel Gordon)等人激烈地否定了。另外,他在六七十年到中国旅行时,对当时中国人生活的理解与态度,也被一些欧洲汉学家认为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漠不关心”——尽管这或许也是他“中立化”的实践之一。
同样在60年代,德里达延续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线索,而他的“解构”方法进一步明确了巴特的努力。他认为,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都建立在语言与真实的固定相对关系之上,这种对应也正是结构主义所依存的对应关系的基本点。但是,他指出:这种对应是未经检验的。他重新审视写作的基本要素,及其对哲学的普遍影响,并希望破坏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体系,也就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他甚至称自己为“历史学家”而非“哲学家”。 因此,德里达也被称为“解构之父”。在50年代末期,结构主义学说正有取代想象学的势头,因为结构主义学者认为,现象学所强调的经验,只能在“非经验”的结构当中才能产生效果。而德里达作为现象学的拥护者,犀利地指出,结构本身是无法有起源的——结构主义的弱点在于,必须依赖一套既有的,被规定的,封闭的语言体系,因此,建立在这一体系上的批判,是永远无法批判这一体系本身的。也就是说,除非假设有一种超验的,永恒的,普遍适用的语言系统,否则结构主义的论述就是空洞的。在1960年代后期,德里达阐明了自己将哲学作为一种文本批判形式——而非发现真理的形式——的态度,并批评了西方哲学推崇在场和理性,而不是他所强调的,抽离式的不在场和记号,或者书写。这与巴特后期的“中立”态度在本质上是很接近的。
以罗尔蒂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则认为,德里达以自己的原则所建立的写作方式是伪哲学和诡辩,因为德里达的论述并不以哲学为根据,而是建立在文学和其它人文学科之上的。而且,他的论述充满了刻意设置的误读和词汇背景的混淆,以至于无法以学科标准进行批判。然而,罗尔蒂也承认,这种模糊是有其哲学依据的,德里达的写作方式正是为了逃离哲学中固有的形而上命题。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代表了“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及60年代更加激进的后现代思潮的来临。后结构主义的学者普遍质疑结构主义,认为它只是一种自圆其说的体系,尤其质疑它针对语言的基本模式所提出的,语义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指出这一对立并非是天然和必要的,却被当作了符号的基本结构。这一质疑往往从语言的基本构成开始,延续到对文化和历史的书写方式,以及对整个社会的知识和真相的质疑。后结构主义的学说主要来自德里达(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阵营),福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布特勒(Judith Butler),拉康,鲍德里亚,以及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等人。如果说现象学认为,知识的基础在于经验;那么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知识的基础在于观念,语言,或符号的结构;而后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结构与经验都不能带来知识的基础,而且,这不是一种失败,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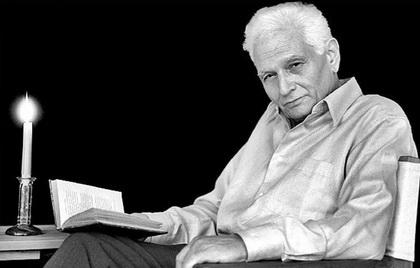
▲ 德里达
作为科学或者说科学哲学领域对这一批判的响应,大约在1962年前后,托马斯·库恩反思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将这种基础的快速变化归于同一领域的科学家们的临时合意,称之为“范例转移(paradigm shift)”。也就是说,他讨论的也是知识形成的过程。他指出,科学的真实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由科学团体所认定的框架所构成;不同的框架往往相互矛盾,却又无法比较,只能在自己的框架中成立。因此,科学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由参与者的主观态度和世界观所决定。同时,科学的进步往往不一定是真的在发展,而可能只是使用不同概念框架的研究群体之间的,不同的理论范例的相互替代而已(波粒二象性实验就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不同的科研“范式”之间的碰撞)。这一论述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科学的言说结构的质疑,或者说,是后结构主义范畴内的。库恩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他对麦克·波兰伊(Michael Polanyi)的学说可能存在的抄袭;至于学说本身,似乎可以被看作一种不同学说之间的调和剂,因此它受到的重视似乎并不高。
例如,“范例转移”就可以是看待在稍早之前诞生的,拉康的精神分析主义的一种中立方式。拉康结合了索绪尔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精神分析的症候本质在于语言。在1950年代,他提出“无意识”也拥有语言式的结构,而并非心智的基础部分。同时,语言并不受自我或者说“主体”的控制,而是来自外在的“他者(Other)”。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进入自我,发现真实的,“无意识”层面的欲望;分析的完成则在于“欲望的净化”。同时,他认为精神分析是唯一能质疑科学与哲学之不足的方法。 经由对一系列概念的发明或重新阐述,尤其对“主体”与“他者”这对二元关系的强调,他建立了典型的结构主义体系。因此,他虽然并非一位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家”,却对结构主义思潮颇有影响。同时,他新浪漫主义式的观点(例如认为疯狂是“痉挛的美”);对弗洛伊德的“15 分钟”诊疗规则的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颇具经验主义,甚至“禅学公案”意味的临床实践;对非理性和挑衅的强调(并将挑衅用到了临床实践当中);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既有理论结构的“范例转移”式的改变;以及对激进左派社会运动的支持,又使得他常常被归入一个更加广义的“后结构主义”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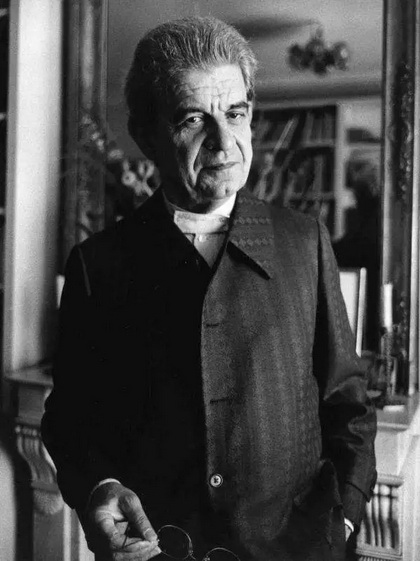
▲ 拉康
拉康并未得到欧陆或分析哲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他被认为是“含混”的评判体系。另外,在1960年代还出现了“反精神病学”思潮,主要就体现在对精神分析法本身的批判上。胡塞尔对精神分析主义的总体批判很具哲学层面的代表性:他认为,精神分析主义对公式和逻辑的运用是“先入为主”的,其原因主要在于,混淆了先验的中立逻辑和预设的评判逻辑——从追求真理的方式来说,一种评判必须符合评判之外的逻辑,而非评判自身预设的标准,以及仅仅由这些标准所建立的结构。同理,精神分析中的“真实”并没有提供一个更加可靠的,精神分析之外的根基,而只是依靠经验的“显然的”真实,却试图建立一个非经验的理性框架。这实际上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有非常类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关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一个是针对宏观的语言及其与真实的关系。
福柯也不认为自己的“后结构主义”立场是自发的,而把自己看作是结构主义传统的一员——毕竟,“后结构主义”这一概念是由北美学者在了解他们的理论之后才发明的。他深受尼采的影响,在1960年代,他以自己后来称为“知识考古”的方式,引入史料编撰法,分析了以语言叙述为基础的,社会,历史,以及知识的演变,其中也反映出明确的结构主义思路。他认为,人类被知识主宰了,而每个时代的所谓真实都只能建立在特定的潜在条件中,这些条件决定了在特定的时代,哪些论述可以被接受为“合理的”。而且,在每个特定的文化或者每个特定的时刻,这些条件只会有一种组合方式,即特定的,却又不被指明的认识方法。与库恩的“范例转移”相比,福柯将“范例”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认识领域,科学也只是其中一个类别而已。并且,库恩认为“范例转移”来自研究群体的有意识行为,而福柯则认为,认识方法的转移是建立在非常基础的,以至于被人在执行的同时所忽视的,社会无意识层面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1960年代,福柯还与萨特的存在主义阵营展开论战。福柯认为,萨特的学说只适合存在于十九世纪,就像鱼只能活在水里一样——这一看似普通的比喻,实际上也是他对上述理论的一次最为浅显的应用。
他的学说在1975年前后成熟,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他评价了“散漫”的力量。他将圆形监狱作为范本,并提出“语言即是压迫”——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不被压迫,而不说此种语言的人就受压迫。最终,他的学说归结为对知识与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批判:社会作为主体,使用知识的力量,将自身的主观需要客观化了。由此,知识变成了社会结构所需要的压迫手段,例如对“疯狂”,“疾病”,“正义”或其它实体现象的定义,以及对性和身体的规范等等。因此,他最终留下了后结构主义式的主张。对他学说的正面评价来自批评领域的方法贡献,例如对哲学如何发现“控制与被控制”的方法贡献,以及为读者所争取到的,基于知识论述的自由接受的权力。这些几乎是唯一可发现的,福柯为哲学带来的正面情绪。因此,再次以罗尔蒂为代表的批评声则认为,福柯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理论或任何正面的解决办法,仅仅是推翻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原则,让知识所捍卫的“自由”与“正义”走向了虚无;并且,“如果他说论述不可能是客观的,那么这个说法本身可能客观吗?”

▲ 福柯
利奥塔与福柯一样走向极致的怀疑与解构。他的主要学说出现在1970年代,他从逻辑学出发,激烈地反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普遍性和“元叙述”,也就是反对各种被作为前提而存在的论述,尤其反对被作为前提的潜在逻辑和因果关系。他认为,现代哲学对所谓的真实的肯定,是以被普遍接受,却又缺乏检验的,关于知识和世界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即所有的历史,知识,社会等叙事,及其合理性所依存的根本——为基础的。可是,这种“元叙事”既没有严格的逻辑,也没有严格的经验。他把这一现象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s)”相比较:随着现代主义以来的基本叙事的崩塌,人类开始了一种新的“语言游戏”——不再追求绝对的真实,而是只能接受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当下关系,并依赖这些关系当中的相对性。同时,这种关系是随着经验不断改变的。由此不难理解,他很早就评价马克思(Karl Max)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关于政治,经济,以及治疗学的理论都是“外行话”,只能靠“独断和霸道而流行”。同时,他相信,二战以来的科学都只能用“微叙事(little narratives)”取代,包括科研,也必须找到新的目标,取代对“真实”的追求。作为这一思考的延续,他预言了数据化的信息处理将会到来,而科技将取代智慧主宰世界。
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不同观点的哲学家都对利奥塔的论述提出了批评。其中主要是针对他论述的基础,即“语言的无效性”。很显然,他自己的论述仍然是基于语言的“有效性”,以及“语言游戏”本身的。他所反对的,对语言和叙事的共识,以及基本的“合理性”,也正是他自己的论述被表达的方式。同时,利奥塔对康德(Immanuel Kant)所论述的“崇高”的反对,相当于反对了哲学本身:即验证自身及其所论述的对象。那么,利奥塔也就推翻了自己的论述——或者说,他的论述就变成了另一种与福柯相似的自相矛盾的行为:用“常识”去反抗“常识”所形成的基础。另外,作为从逻辑学出发的讨论,利奥塔的论述被认为严重缺乏严谨性,包括对“真实”的定义本身都显得“苍白”。这些并不妨碍以他为代表的,逻辑——尤其是宏观层面——的断裂甚至消亡,以及基于“微观叙事”的独立价值观的自我凸显,成为后现代以来的文化及艺术批评的重要部分。
理查德·罗尔蒂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两人都认为应当消解传统的哲学问题;同时,他也批评了福柯的论述让一切研究都成为了虚无。在这一立场之上,他提出了“反基础”和“反本质”的思想,并重新强调了经验的重要性。1979年前后,他延续了“范例转移”的思考,认为哲学错误地模仿了科学的方法论,不应去追求一种普遍而恒定的逻辑结构,也不能被作为“自然的镜子”去看待:也就是说,哲学是不能用论述去“再现”世界的“真实”的——就像他所认为的,科学也无法真正“再现”这个世界。同时,他结合了维拉尔·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对综合分析法的批判,以及维尔弗里德·色拉尔(Wilfrid Sellars)对“已知的神话(Myth of the Given)”的批判,做出了与利奥塔相似的论述:消解了语言与“真实”之间的联系。但在这里,被消解的联系是叙事层面,而非逻辑层面的。这使得他的论述更具实用主义的主张性质。在这一点上,他吸收了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对观念和经验的二元论的批判,并提出:人的观念与世界的关系是由人所处的时代偶然决定的,任何描述世界的方式,在与其它时代的方式比较后,都将是不完整的(例如语言也只能根据特定时代的经验而被使用,古代语言有时无法翻译成现代语,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经验完全不同)。因此,“真实(truth)”不是能得到的正确结果,或可以被再现的“真相(reality)”,而只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人如果放弃了对世界的“再现”式的概括,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平静。
因此,罗尔蒂设定了一种大多数:他们只相信眼下的真实和既有的历史叙述,不考虑世界观层面的问题;而另一种少数则如英雄般孤独:他们无法知道更多,却关注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并且明白,自己的叙述也永远无法比大多数更接近真相。这些少数因此是自觉的,并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报以浪漫主义的“嘲讽”的态度。显然,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同时,罗尔蒂经常引用或解读其他哲学家的观点,而他对这些观点的使用被认为缺乏系统性,更像是文学评论对小说段落的随意摘录。由此,苏珊·哈克(Susan Haack)也抨击了罗尔蒂的思想,认为他的论述是“反哲学”,“反智力”的,并只会让人类“更加受到修辞的摆布”。
鲍德里亚也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受到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影响,发展了媒体和交流对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并且从历史进程的角度,重新论述了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相比福柯将知识的产生归结于力量之间的关系,鲍德里亚则认为,任何追求总体的知识,或者涵盖一切真实的论述,都终将落入幻象当中。在1981年前后完成的“模拟和拟像”一书中,他从当代社会如何制造虚拟的生活图景入手,最终论述了一个符号层面的核心:要彻底理解人类生活的每个细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理解都需要借助符号,以及符号的相互关系。那么最终,真实会在符号的交互变化中消失,只剩下符号本身;而人则活在符号的关系当中,看不到世界的真相。他认为,尤其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社会,符号已经像商品一样可供交换;社会对符号与意义的滥用,已经将真相都抹去了,变成一个依赖“象征”,而非事实的社会。于是,自由主义或任何乌托邦都不再被相信了,而例如恐怖主义这种典型的“象征式”的攻击,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效果。 他与利奥塔相似,对历史的“元叙事”持否定态度,并更进一步认为,历史本身将成为自己的垃圾箱而终结,而普世性只是一种逃离现实的虚假承诺,甚至连“终结”本身也不会被相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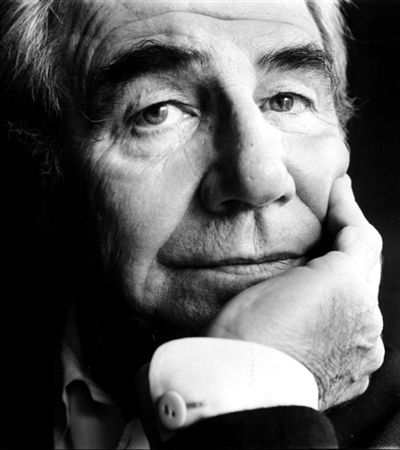
▲ 鲍德里亚
马克·普斯特(Mark Poster)则指出,鲍德里亚的写作是夸张和宣言式的,在关键点上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他将自己的观点扩大化了,并拒绝为模糊的论述划定边界;例如,他将电视,图像等经验的影响无限放大,从这些有限的证据中推断出灰暗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在鲍德里亚的宏观叙事中,人首先不再是公民,也不再处于任何阶级中;人只是消费者,由此才受到符号的摆布;而为什么人作为消费者的身份比作为公民的身份更加重要,并没有得到直接或间接的阐述。这样的宏观叙述是欠缺逻辑的。
注:篇幅所限,注释部分省略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