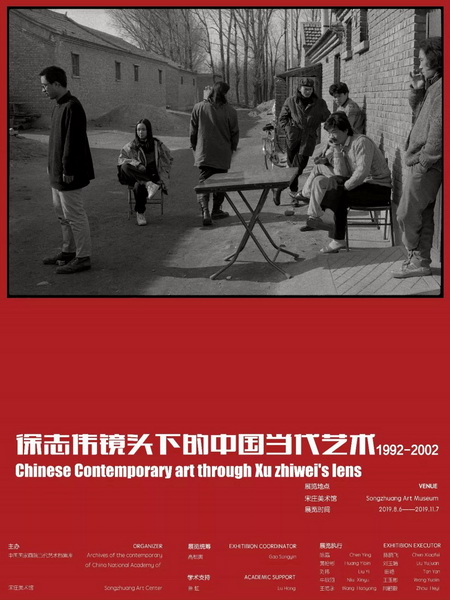▲ 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 1955年 版权归属文献展资料馆 君特·贝克
文︱刘乐
在艺术展览领域,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三大艺术展,其中,卡塞尔文献展尤以其“学术独立、思想深刻、艺术自由”为人称颂。从其创建之初,这个五年一届的展览便成为记录国际艺术尤其是西方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平台,经过60余年、13届的打磨和锤炼,它已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中的权威,成为全球艺术界乃至文化界最重要的盛事之一。除此之外,卡塞尔文献展还享有“国家文明的使者”、“城市文化的象征”等标签,诸多盛名不免让人惊奇这个在德国小镇举办的展览究竟为何蕴含着如此强大的能量。2017年3月1日,系统拆解这个神话的展览“文献展的神话——阿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卡塞尔文献展为国内所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展开,西方现当代艺术被大量引介,卡塞尔文献展也引起了中国艺术界的极大兴趣。但直到1997年第十届文献展邀请了艺术家汪建伟和冯梦波,中国才真正开始参与这个展览。之后,随着中国艺术家参展人数的日渐增多和影响的逐步扩大,国内的媒体和评论家们开始展开了对文献展的报道和分析,卡塞尔文献展在中国产生了日渐广泛的影响。要以展览的形式对一个具有60多年历史的世界级文献展进行呈现,其难度可想而知,此次“文献展的神话”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尝试。开幕当天,热闹程度远逊色于诸如基弗、大卫·霍克尼等明星艺术家展的情况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关于展览的展览的难读性。但是,在中国的当下,在一个学院美术馆举办这样一个费力却不易讨好的展览,其意义何在?策展人余丁先生指出了展览的要义——这个展览不是对卡塞尔文献展的宣传,而是对卡塞尔文献展的一次深度学术挖掘;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学术性的。

▲ 第十三届文献展,高什卡-马库加作品“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那就不是什么”,2012年 版权归属斯蒂芬·达姆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经历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更是日趋多样。随之而来的是大大小小的展览呈井喷式出现。近年来,从国家级的美术馆到私营的艺术空间和画廊,从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到各地兴起的大型艺术项目,每天都有大量的展览如走马灯般上演,但其中真正把握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内核,产生了影响、引发了争议以致能够被铭记的寥寥无几,更不用寄望这些展览能够引领和反作用于当代艺术以及文化的发展。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真正让展览发挥它在审美、文化以及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功能,这个关于卡塞尔文献展的展览及时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和学习的典范。
近年来,文献展[1]已经成为艺术展览中一种常见的形式,“文献展的神话”作为一个文献展的文献展,可以说是将文献展的要义发挥到了极致。策展人在深入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将13届展览整合为“重建、转型、一切皆可、国际话语”四个部分,明确而细致地展现了卡塞尔文献展60多年来从思维到视觉、从诞生发展再到变革、从德国本土到越来越全球化的语境大的发展历程。经由展示设计,四个部分以能够传达每个阶段时代精神的色彩进行区分,每个部分起始处以简练的文字进行介绍,各部分内每一届展览又以个体的面貌出现,以作品、文献实物、图片、影像等多层次的信息群有序地与观众进行交流。如此便有效地避免了文献展信息量大都过于枯燥的弊病,300多件文献和作品共同营造出某种情境,使得展览空间不再只是物理空间,而是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使观众产生沉浸式体验的无限关系空间。百年的历史时间和贯穿其中的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化及一般性空间都被折叠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二楼的展厅,在展厅中穿行,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空间的层层展开,无论是5分钟的匆匆浏览还是5小时的细细研读,都可以有所收获。

▲ 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海报
一个大型展览的成功需要很多因素,除了策展人、艺术家和作品等主导和显性因素外,展览的组织运作、艺术教育、传播和宣传机制等隐性部分也不可忽视,后者是前者得以呈现和最终发挥效用的基础和保障。无疑,卡塞尔文献展的很多隐性机制都值得我们深入解读和借鉴,这次“文献展的神话”展出的很多关于历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文献和档案资料也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提示。但是当这个展览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时,如何从这种整体的文脉中提取策展精神,探讨一个展览是如何把握艺术、艺术史和社会文化的潮流,并反作用于前者的更新,也就是“神话”的关键性内核,或许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最首要和最迫切的东西。
在展厅入口处的坡道上,五张历史照片以关键词的形式提示了卡塞尔文献展出现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一切都开始于二战期间被摧毁的卡塞尔城,也是“文献展之父”阿尔诺德·博德的故乡。20世纪50年代,在纳粹统治和二战结束10年后,在德国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已取得奇迹般的进展后,在传统的(西)欧洲重塑德国文化之国的形象显得日益迫切。重建的第一要义在于修正历史错误,恢复在德国纳粹统治期间曾遭禁毁的现代主义艺术成为展览的首要诉求,因而卡塞尔文献展从创立伊始便带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并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使命,有别于一般的博览会或流派展览。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前两届文献展(1955年和1959年)重新展示了从毕加索到康定斯基、从塞尚到包豪斯等老一辈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博德试图从一定历史距离之外,从某种潜在的权威的艺术史视角组织前两届文献展。

▲ 阿尔诺德·博德,1972年,版权归属文献展资料馆,弗洛瑞斯·诺伊胥斯

▲ “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览现场
针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美学特性和抽象艺术发展的持续性理论,博德重新对博物馆式的展示空间进行了变革。最为经典的案例是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对恩斯特·威廉·奈的巨幅《空间中三幅画》的布置。博德将三张作品用一个倾斜、交错排列的角度挂起来,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节奏并且试图营造一种“现代语境中的巴洛克艺术”。通过这种空间美学的创新,展览以其独有的空间参考体系帮助图像实现了为自己发声的使命,也推动了现代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的自主。正是从此开始,博德赋予了展览作为次级艺术的使命,也奠定了卡塞尔文献展由艺术总监全权负责的机制。之后历届的艺术总监也都以自己的趣味和思考推动着卡塞尔文献展的发展和变革,不断升华着“展览”这一艺术,这也是此次展览副标题取名为“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的原因所在。
1964年,题为“百日博物馆”的第三届文献展因其日渐“过时的艺术概念”[2]开始为人诟病,使它陷入第一次危机。要知道,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的重心仍为抽象艺术,而同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绘画大奖的则是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这一时期也恰逢西方爆发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冲突,此时,与现代艺术逐渐走向极端抽象相对立的是以观念艺术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的发生,其主要诉求是介入世界、介入生活,他们通过艺术计划、策划文本、宣言、记录、表演行为、影像等媒介进行创作。虽然第四届文献展上后知后觉地展出了大量的波普艺术,但更为多样的当代艺术如激浪派、偶发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及女性艺术的缺席扔招致了大量的不满,被排除在文献展之外的激浪派艺术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此时,各地的美术馆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的关照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不再需要特意去文献展感受和欣赏当代艺术,卡塞尔文献展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和定位。

▲ 第四届文献展,克里斯托作品“5600立方米包裹”设计手稿, 版权归属文献展资料馆,卡尔·奥斯卡·布拉泽
哈罗德·泽曼的出现开启了卡塞尔文献展向当代的转型,使卡塞尔文献展变成了当代艺术的实验场。泽曼是独立策展人出现的开端,在接手卡塞尔文献展之前,他策划了著名的“当态度成为形式:作品、观念、过程、定位、信息”展,反对现代主义以来艺术的固有形式,试图通过展览让强调态度、观念和过程、行为的当代艺术为人所知。泽曼将自己的理念带入到第五届文献展(1972年)中,文献展的题目不再是以往如“1945年以来的艺术”这样宏观的题目,而以“怀疑现实——今日图像世界” 为展览预设了一种潜在的提问与反思。展览设计了一个由多元图像世界构成的群岛,请观众自己通过“高”与“低”的并置决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3]。“文献展的神话”展厅里复原了这届文献展上豪斯·鲁克的作品《绿洲七号》——一个透明的气球综合装置悬挂在博物馆空间之外,象征着艺术开始走出博物馆空间、博物馆模式,而人们观展的方式也不再是敬畏式地欣赏,展览空间开始成为当代艺术激进的实验发生场,也成为观众体验、互动和思考的场域。这种新型的展览实践推动并且重新定义了当代艺术创作的观念。


▲“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览现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文化、反艺术的时代风潮中,泽曼以革命的姿态开启了卡塞尔文献展不同于博德的另一极,成为艺术和社会变革的转折点。接下来的文献展或多或少都处于博德和泽曼所代表的两极之间。两人作为文献展艺术总监的主观性与当代艺术客观趋势之间的吻合或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争议和变革为80年代的文献展奠定了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基调:艺术——媒介——现实。围绕着这三个关键词,卡塞尔文献展进入了相对温和的梳理、总结和沉思的阶段。恰逢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信息革命与大众消费文化同时出现。发端于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后现代思潮也日渐突出,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反对范式的超验性,提倡多元、多样和“他者性”。回顾展以“一切皆可”来形容这一时期卡塞尔文献展的面貌真是再切合不过了。观众既可以在博物馆空间中欣赏意大利超前卫派和德国新表现主义等重新回归的具象绘画,关涉艺术的自治,也可以在卡塞尔市的户外空间参与博伊斯的超大型公共艺术项目——为卡塞尔市种下7000棵橡树,体验“社会雕塑”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深意。
在后现代主义接近尾声之际,1992年杨·荷特掌舵的第九届文献展为这一阶段的文献展画上了句号。杨·荷特是另一名具有传奇色彩的策展人,他秉承了泽曼对于艺术总监角色的定位,赋予了文献展以鲜明的个人风格。作为一名前拳击选手,他将自己对艺术的感性理解融合进展览中,避免了展览的意识形态性或展览作为前卫艺术实验的战场,而是展现艺术作品包罗万象的“技术魅力”,并且强调艺术诉诸感官的力量,这种易接受性是本次文献展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之一。目前安放在火车站广场上的乔纳森·博罗夫斯基的作品《走向天空的人》就是在这届文献展上展出,受到市民的强烈喜爱,因而保留下来并成为城市地标的。杨·荷特再一次扩大了“策展人”的内涵,使策展人成为项目总监、展览督导、万能的协调者,致力于发挥艺术的社交、娱乐潜质,渴望实现令人打开眼界的艺术项目。从此,展览不再只是一种媒介,而成为一个社会事件。从这届展览开始,展览的文化维度开始显露,并在以后的文献展中越来越突出地显露出来。但本次展览成为艺术狂欢节的事实也为人诟病,杨·荷特之后的四位接班人都极力抵制这一趋势,试图将严肃思考重新带入卡塞尔文献展。


▲“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览现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急速扩张,全球和本土这一文化命题成为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些现象和后殖民、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这样的理论都开始进入艺术研究和讨论的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新艺术史的出现,开拓了人们看待艺术的角度和眼界。卡特琳·大卫是文献展历史上首位女策展人,她将第十届文献展变成了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个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与话语的空间。正是从她开始,策展人开始以知识分子精英的方式思考展览、反思当下。而第一个非洲裔的艺术总监奥格维·恩维佐则将第十一届文献展变为后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关于“艺术、政治与社会当前关系”的一场文化论坛。“文献展的神话”第四部分“国际话语”的开篇展出了一张艺术地图,统计了历届文献展参展艺术家的出处,可以明显地看出全球化和地方化与这一时期卡塞尔文献展的关系。之后的第十二、十三届文献展像是对过去的回顾和总结,更多形形色色的当代作品被介绍,更多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话题在这里被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没什么东西是完全崭新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激荡,那些萦绕着艺术、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已经能够得到更深刻和多层次的解答。文献展已经成为了审美体验场、文化与媒体的体验空间、社会事件空间,更重要的是成为了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场域。
从经典现代主义的展示空间到前卫艺术的试验场到艺术事件的发生场,再到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空间,在60多年的时间里,卡塞尔文献展在不断的自我更新过程中成为记录和反映艺术和时代文化的晴雨表,成为艺术前进乃至社会发展的发动机。贯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文献展在建立之初便奠定的自由、理性和批判精神,他们用制度保证了这一精神的延续,也促进了包括策展人、艺术家、展览组织者等艺术世界各个部分的共同合作和良性循环,共同成就了文献展的“神话”。

▲“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览现场多媒体互动区
“文献展的神话”在展览接近尾声的地方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公共教育实验室,利用交互设计的多媒体技术对历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资料进行呈现,观众可以通过动态数据图把握文献展的发展路径,也可以滑动触摸屏轻松获得自己感兴趣的详细资料。这种新技术的引入能有效引导观众对文献展的历史语境关系进行反思,并邀请观众对展览作深入和发散的反馈。可以说,“文献展的神话”在展览的学术梳理、展示设计、呈现方式和公共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希望以这个展览为契机,不仅可以加深对卡塞尔文献展的研究,更可以给中国的艺术界以新的启示,开启“中国的卡塞尔”的建设之路。
注释:
[1]这里的“文献”不同于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中的“文献(Documenta)”,后者原为拉丁词汇,具有“记录”、“记载”的意思,相关的含义还包括“总结”、“证明”、“展示”“呈现”或“见证”等,这些都是卡塞尔文献展展示艺术在时代中所处地位的方式和途径。而目前常见的文献展中的“文献”则指照片、文件、手稿等与作品有关,具有记录作用的历史物件。
[2]贾斯汀·霍夫曼关于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论文的评述。
[3]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介绍。
————————————————
展览名称: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
展览时间:2017年3月1日至3月31日
展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