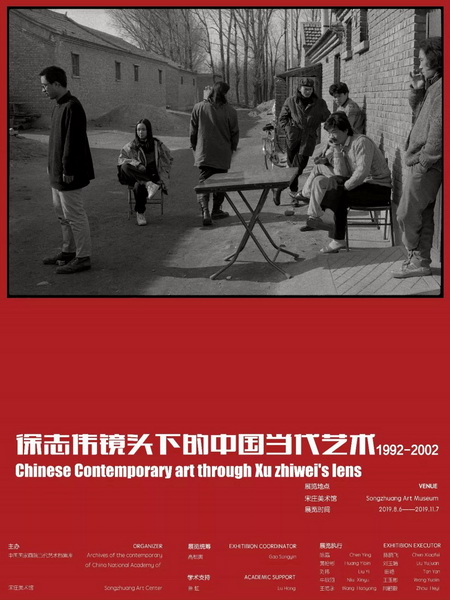自我意识的艺术
副标题:文化研究作为权力的批判
原作名: Die Kunst des Eigensinns: Cultural Studies als Kritik der Macht
译者:徐蕾
作者: [奥] 赖纳·温特
出版社:拜德雅︱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8
装帧:平装
丛书: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
ISBN:9787568914871
赖纳·温特/文
徐蕾/译
充满愤怒、矛盾和叛逆的朋克族与无政府主义的达达主义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居伊·德波和情境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秘密社团为何会成为两者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戈埃尔·马库斯在他令人着迷的《口红印迹》(Lipstick Traces,1992)一书中对此作出解释。他描述了20世纪地下文化潮流,这一潮流盘根错节的形态长期以来隐藏至深。它的目的是重组日常生活、改变寻常事物以及生活。它带来的变化并不是革命性的巨变或者潜在理智的大复苏,它往往是短暂的、有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自我授权的行为和逃避,以实现对自身和生活的改变。马库斯的兴趣在于通俗文化内部、自我认识、身份、社会关系、对世界的愿望和理解等领域中意义的转移。他通过制造背景来追溯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跨越与主导文化对立的亚文化和反文化实践中包含的顿悟、批判性事件、基本意义结构变化,直至生活艺术,或多或少实现一个自我管理下的存在的系统性表现。
本书中的议题都是文化研究运动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比如意义的改变、态度和价值取向、生活世界潜在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对权力的批判、自我授权的时刻——可能只是瞬间,却意义非凡。本书分析的核心是基于传媒的通俗文化,既没有从文化上将它贬得一文不值,也没有不加批判地将它捧高。通俗文化更多地被看作现代和后现代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作为经验的视野以及自身存在的媒介。媒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全球化以及无所不在的文化:图像、符号、话语、历史等,很多人通过它们建构自己的身份、形成对事物的政治观点、一起推动共同的文化。通俗文化不仅是对已存在事物的符号性融入,它也可以成为反对力量,在这个领域中,边缘化和从属化的人物可以提出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文化研究把文化看作一片充满斗争的土壤,在这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努力实现自己的要求、利益和意识形态。相比于对现存关系的再生产,它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的变迁。
从这个视角出发,文化并不等同于物品,不能把文化简化为文化机构生产和传播的对象。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意义和能量的流通、日常生活的移动性和可能性、创造性方面的发展、共同文化的创建,这些才是应该关注的主题。文化研究的兴趣不在于已完成的文化物品,而是在接受过程中的生产性以及在此后过程中的创造性。因此我们在本书中研究的主题,也是文化研究关注的文化社会学主题,即在社会秩序的环境下所强调的行动可能性。
文化研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单独的、创造性和唯我性的艺术生产和艺术享受经验上,而是关注嵌入世俗实践和日常生活使用中,在符号形式、文化物品和技术中的生产性,如何“违背原意”地被解读,如何与“解读说明”背道而驰。创造性始终对主导的社会思想和价值提出质疑。如同马库斯,文化研究也认为个体、群体和文化一起创造性地带来文化改变。这一进程并不依据某个程序来进行,也无法有意识地发起,比如情境主义者或者超现实主义。文化研究展示得更多的是文化作为日常生活中(偶发)创造性的潜力。这一创造性和生产性在社会实践中的展开决定了文化研究的项目。保罗·威利斯(1981,18页)写到,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实验室,在这里,各种实验得以开展,没人知道实验的结果会如何。意义在社会实践中被制造、实现和流通。雷蒙德·威廉斯(1977a)认为文化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主导的、反抗的、冗余的和附属的意义集合。文化研究的目标是文化的改变,尤其是冲突、斗争和权力关系的转移,其中从属者、边缘化人群和被排除在外的人群,他们拒绝权力提供的融入机会,或因各种原因无法融入。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亚文化、反文化、少数群体、另类潮流,以及他们的反抗形式、顽强不屈、符号的使用,还有小到甚至不被察觉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变化。受奥斯卡·内格特和亚历山大·克鲁格(1981)的影响,文化研究对《真正生活的阻碍》(Block des wirklichen Lebens)一书非常感兴趣,书中包含许多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文化研究不着眼于统治者的历史,而是着眼于反抗、多样化进程,以及如何对统治阶级的联系进行破坏、质疑和改造。
他们听从米歇尔·德·塞托(1988)的建议,聆听“社会的喃喃低语”,重视普通人变成匿名主角的场景和实践。这是一个文化影子经济的进程,将已经给定的和已经成形的想方设法变成自己的。这是创造性地对待充满矛盾的日常生活的活力,是在文化中和协商中对自己位置的坚守,简而言之:是自我意识的艺术,它并非在各种论点的斗争中得以施展,也不是一个普世理性的表达,它是在最普通实践中的亲身感受。在梅洛‒庞蒂(1986)眼中,这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理性,它创造意义并植根社会。
这类普遍的创造性(参见Kiwitz 1986)的目标是通过对权力的批判改变现存。但是它往往只能迈出很小的步子,几乎微不可见,在一个由结构决定和目标明确的社会行为中往往被忽视。米歇尔·德·塞托(1988,77页起)对此谈到了在功能性理性丛林中的战术、关于野生和拼凑的过程,以及“坐在两把椅子之间”的艺术。列斐伏尔在关于日常生活变化的思考中也考虑到了比如业余时间的生活艺术的可能性(Lefebvre 1977,50页),这对文化研究影响很大。文化是一个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创造性过程,文化研究思考和研究的方向不是传统,不是传递下来的意义和价值模式——尽管这些往往决定了社会文化概念,而是改变和改造文化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将再现和讨论文化研究在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一些研究项目,这些项目证实和促进了自我意识艺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对权力关系的分析、批判和改变。它并没有追求本质化,而是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出发对这一传统进行更加紧凑的表现和讨论。文化(行动力)是有生产性的,并不从属于结构,这对于社会学来说有着核心意义,因为社会学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学。所以文化研究可以作为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阿尔弗雷德·韦伯,以及其他社会学家在20世纪开始的宏大项目的继续。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