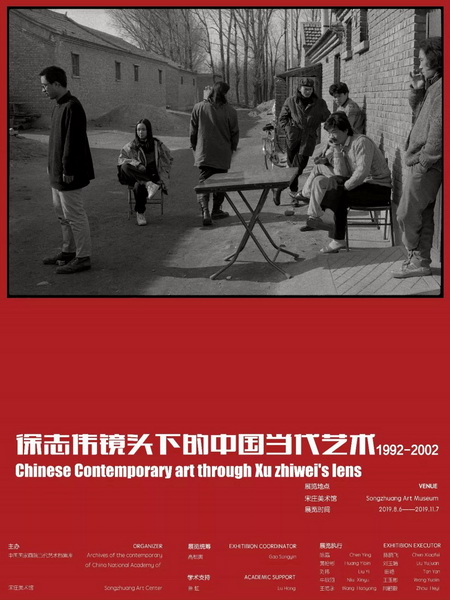(第一场)
时间:2010年1月23日
地点:东湖宾馆企辉厅
开幕式
主持人:孙振华(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艺术主持,深圳雕塑院院长)
致辞人:宋玉明(深圳美术馆馆长)
专题发言:《在文学史与当代文学之间》
主持人:鲁虹(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艺术主持,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
主讲人:李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孙振华: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现在开始。
前两年,今天在座的彭德先生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希望能够按照古代文人雅集的方式来开会,不要太正规,不要太严肃,这个想法后来没有实施,倒是启发了我们。我和鲁虹商量,认为深圳美术馆论坛要慢慢朝着一个轻松的、谈话式的、讨论式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这个论坛变得越来越去官方化、去仪式化,真正能够针对某一个学术问题请到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有研究的朋友,在一起说说话。
目前,在学术会议的形式上,中国人越来越强调国际规则、国际惯例。通常是一个人发言,发言以后限制多少分钟,然后又有评论员,还有提问、讨论;当然这是一个模式,还可以有另外的模式,就是更加散淡的,更加轻松的,同时又是更加亲切的模式。用朋友聚会的方式来讨论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讨论问题,而不是国际通行的模式。我们已经把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请到了一起,希望大家像电视里面的谈话节目一样来谈自己的想法,发言可以打断、可以插话,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强调和大家的互动,不要拿着稿子站在台上念。说到哪里算哪里,并不要求大家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其实就是大家各说各的,讨论一番,最后求同存异,把未决的问题留待以后。
所以,这个会议的开法和前几次有一些不同,我们根据收集到的论文,把它分几类,按照其中的类别,我们请主讲人上去,不一定讲自己的论文,而是用较短的时间讲自己的想法,讲完以后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大家讨论得很高兴、很激烈,我们可以不顾时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话可以进入下一节,希望大家在自由的氛围中真正碰撞出思想火花,从这个意义上回归到论坛的本意,通过论坛激发思想,产生一些思想成果。
按照惯例这届论坛也将大家的论文汇集在一起,出了一本书,大家可能都拿到了,就是《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这里特别感谢河北美术出版社,感谢冀少峰先生。以前老是说“深圳速度”,我们今天早上开玩笑,现在有了“石家庄速度”,只要把稿子给他,他可以在不可思议的时间内变成书,魔术一样的变出来,给你运到现场。在当代艺术的出版上,全国出版社里头他们做得最好。所以鲁虹说,只要和冀少峰一起合作,我们心里就有底,我觉得这是对他的最佳评价。
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纰漏,可能是赶时间没办法。原本书本的目录编排我们是分类的,一类是比较集中的谈艺术史写作主题的;还有一类就是结合个案,就是自己的写作,来具体讨论艺术史写作;还有一类文章偏重的不是谈艺术史的问题,而是一般的艺术理论的问题;最后还有一类是来稿,为论坛征集了一些稿件,挑选了一部分放在书里面,大致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我们的编排是有间隔的,但现在拿到的书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把间隔做出来,特别要做一个说明。
这是主持人说的罗嗦话,把背景跟大家说一下,下面进入正式程序。进入正式程序之前请各位与会的朋友,还有媒体朋友请把手机关闭或放到震动、静音状态,不要影响会议的进行。下面有请深圳美术馆馆长宋玉明先生致欢迎辞。
宋玉明: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主持人,上午好!首先我谨代表深圳美术馆全体工作人员对大家前来参加“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这次论坛我们邀请了多位活跃于当今学术界已经卓有成效的学者和深圳学术界的朋友,希望在这次论坛上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论坛的学术成果能够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将感到万分荣幸。
深圳美术馆的学术目标是关注当代艺术,关注本土艺术。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对当代和本土艺术的关注、引导、推介,两年一届的深圳美术馆论坛是我们关注当代艺术的重要品牌,到现在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了,我们愿意将深圳美术馆论坛办成一个重要的常设性论坛,将论坛打造成深圳的一张文化品牌、文化名片。
最后,请允许我向各位参加论坛的学者,以及为论坛成功举办付出辛勤努力的朋友们表示真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孙振华:另外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陈新亮先生本来要过来致辞的,但临时有会议来不了,表示说下午过来看望大家,与大家见面,所以他讲话的环节下午再过来说。
按照议程安排还有一个合影环节,但是如果刚刚开始又出去合影就很乱,我们把合影环节安排在下午,个别人员如果要先走的话,就像杨小彦上午要走,我们可以请一个电脑高手把他的头像做上去。现在继续开会,下面进入主题报告的环节,交由鲁虹主持。
鲁虹:谢谢大家,从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开始,每届深圳美术馆论坛都会围绕一个或若干主题进行跨学科的讨论,比如第二届请来了历史学家高华,还有文学评论家单世联、社会学家郑也夫、于长江。我们这一届还是想沿着这个模式继续来做。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对这30年的历史怎么书写,历史学界、文学界、艺术界、美术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按我们的设想,本来要请两个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专家。一是邀请了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来谈谈对改革开放30年来历史书写的问题,他已经准备好了报告内容,而且还跟我打过电话交流,很遗憾他最近癌症复发,做了手术,不能成行,在这里谨祝愿高华教授早日康复。另一个是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杨做一个专题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在文学史与当代文学之间》。李杨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文学史理论家,曾经有多种关于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出版,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对美术界当代艺术史有很大的启发,下面有请李杨教授做报告,大家欢迎!
李杨:各位来宾,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其实出现在这个论坛上,我的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我对于“艺术史和当代艺术”这个话题完全是外行,当初接到论坛邀请的时候,我还担心是不是搞错了?但孙振华、鲁虹说找的就是我。他们说进行跨学科对话是深圳论坛的特色。论坛每次都请一些非艺术学科的学者来抛砖引玉。遗憾的是,今年请的另一位学者,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因为生病临时取消了行程,我只好由双打改为单打,压力很大。不过这个创意是蛮不错的,高华先生是历史学教授,由他来谈论“历史”和“当代”之间的关系,我来谈“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的关系,确实能与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构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关系。
其实,文学和艺术算得上是一对孪生兄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属于一个学科,统称为“文艺学”。只是近年关系有些疏离了。艺术家一夜暴富,作家基本上仍是穷酸的书生,所以往来不多了。当代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在座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年轻的时候应该都做过文学青年,都喜欢过文学,但现在基本上都弃暗投明了。但当代文学是否真正没有什么价值呢?问题是这种价值到底指的是市场价值,还是艺术价值,或者文学史价值,或者这两个价值本来就应该是同一个东西,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这些做文学研究的人也非常困惑。最近大家都在骂《三枪》,搞文学的人骂得特别厉害,为什么骂呢?因为张艺谋瞧不起中国当代文学。他说中国当代已经找不到他看上眼的文学作品,所以只好购买科恩兄弟的《血迷宫》,结果拍成了一部千夫所指的电影。我们开玩笑说,如果张艺谋购买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绝不至于拍得这么差。其实张艺谋以前的代表作,主要都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现在他突然瞧不上他赖以成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了,是当代文学确实不行了,还是他自己出了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昨天我才看到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许多问题都很熟悉,因此觉得很亲切。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如果换一个关键词,把“艺术”换成“文学”,是完全适应的,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文学专业的一个讨论会。所以我想介绍一下文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思考。
在我们这个论文集里面,有一些学者,包括孙振华先生都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书写与艺术史的关系,还有的文章讨论了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书写问题,这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希望能在会议中做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一般倾向于将“文学史”理解为一个现代性范畴,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和“历史”这两个概念本身都来自西方,虽然中文里面早就有这两个词,但词意与来源于西文的Literature和History并不完全重合,文学史的功能也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应该说是从胡适和鲁迅这一代人创制的。最早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新文学史”的写作,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胡适1922年写下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算是第一部典型的“当代”文学史。1935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则是更为经典的“当代文学史”。《大系》由赵家璧主编,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文类,共10大卷,请著名的专家、学者作序,《大系》没有叫“文学史”,但承担的完全是文学史的功能。因为《大系》对经典作品的选择和认定,体现了选编者的立场和趣味,而且每一部选集都有一篇由著名学者写的序言,实际上是对所选作品所做的导读,这些由既是文学史家,又是当代的作家如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等人写作的导读,实际上确立了正确阅读新文学的方法,在文学的分类方面、在文学的分期方面都是按照文学史的规则来操作的。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新文学”其实就是“当代文学”,不过我们今天所谓的“当代文学史”却有着自己的特定含义,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因此有人又将其称为“共和国文学”。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是不是也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在1950年代,“当代文学”出现之后,原来的“当代文学”——“新文学”也就变成了“现代文学”。所以现在做文学研究的都知道,“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有着不同的指涉对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从50年代就开始了。尤其是到5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不过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峰是在文革结束以后。90年代中期,我们有个学生写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论文,据他的调查,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超过了100部。我工作的北大中文系一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重镇。80年代初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和洪子诚老师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尤其是洪老师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几年后发行量就超过100万册,成为国内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基本教材,前两年还由荷兰的Brill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由出版社约请了一位英国学者翻译成英文,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参考书。
文学史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其实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以前我们总是将文学史理解为对文学状况的客观记录,比如说好作品好作家已经存在在那里,文学史只是把这些历史记录下来。这种认识在最近10多年里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可能写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已经过去的历史,面对的是已经被经典化的作家,但当代文学不行。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接近2000部,你把其中的一部分写入文学史,另一部分不写入,理由是什么?尤其那些销量特别大,社会反响特别大的作品,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价值非常低的作品,是不是要写入文学史?这是非常大的困惑。所以不少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学史的权力问题。文学史的基本工作就是定义经典,但经典的标准由谁来确定呢?由文学史家来确定。戴燕前些年在北大出版社出过一本《文学史的权力》,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文学史其实是一种权力,是国家制度、教育制度、文学制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确定了经典、确定了规范,它对文学进行了规训,赋予文学以意义,实际上是在定义文学。文学史的历史说明了这一过程。比如说“新文学史”的写作是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服务的,左翼文学的年代,50—70年代,文学史是为阶级认同服务的;“新时期”或者说文革以后,文学史主要为“现代化”和“个体”认同服务。当然,现代化和个体可能以文学性为名,以艺术性为名,也就是汪晖说的“去政治的政治”,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
文学史的功能规约了文学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当然,也规约了文学史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家是为文学史写作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和洪子诚老师在北京香山开会。我发现他情绪有点低,问他为什么?他说最近王朔在骂我。我说,王朔骂你有什么奇怪,王朔经常骂人,这是常态,他总是通过骂人引起大家的关注。洪老师让我看王朔骂他的那份《北京青年报》,其实是记者做的一个访谈,王朔用他惯用的方式对文化界的一些现象进行批评,前边骂了许多人,后面就捎带骂上了洪子诚,骂了半天我也没看懂,为什么要骂他。我只好问他,洪老师,你认识王朔吗?他说我不认识。我知道洪子诚老师是一位非常纯正的学者,虽然一直研究当代文学,但几乎从来不做当代批评,基本不同作家打交道。这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文学史家与作家成了朋友,写文学史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和王朔不熟是很正常的。那王朔为什么骂他呢?我想了半天也不明白,后来突然觉悟,就问他:洪老师,你在你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面写他了吗?他一拍大腿说,哦,我把他忘了。我说,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骂你了吧。他说:不至于吧,他是王朔啊,王朔一直没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一直在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怎么会把文学史放在眼里呢?我说,很可能王朔恰恰就是通过骂知识分子来加入知识分子队伍的。由此可见,王朔还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有些想法我们还是能理解的。
如果说这个故事印证了什么,我想就是所谓的“文学史的权力”。如果连王朔这样的作家都抗拒不了文学史的诱惑,其他的作家就可想而知了。王朔是“新市民文学”的缔造者。他的作品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顽主”空间,这些顽主从传统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体制里面剥离出来,完全靠市场生存,反映了中国社会在80年代的一种非常深刻的变化,王朔自己也成为了这种新的文学——文化形象的代言人,称自己是个“码字工”,靠稿费生存。他的勇敢和才气让人耳目一新。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也不能完全摆脱文学史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不一定是在意识的层面,而是在潜意识层面展开的。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仍愿意将王朔看成我们的同代人,看成“知识分子”的一员,虽然可能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这种对文学史的敬意,在王朔之后,准确地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真正成为了历史。90后的作家(艺术家就更极端),主要靠市场生存,而不是靠文学史、艺术史生存,所以他们对文学史真的完全不在乎了。当然我们不是说以前作家的创作就与市场完全无关,只是那个时候,一定要通过文学史这个中介,通过文学史和艺术史完成经典化的过程,作家和艺术家因为经典化而获得象征资本,但现在市场直接把作品变成商品。当作家直接为市场写作的时候,他们没必要知道文学史怎么评价他们了。
大家都知道前些年网络上爆炒的“韩白之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位研究员白烨,在博客里面写文章批评韩寒,其实他不是批评韩寒,在主流的文学评论家中,白烨是很少的一直关注少年作家、网络作家的人,他在博客中说了许多赞扬韩寒们的话,然后继续鼓励他们,说这些年轻作家虽然有才华,但要继续努力,否则他们不能真正进入文坛。结果韩寒一点都不买帐,他在自己博客写了一篇评论回应,题目叫做“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B”。根本不把“文坛”放在眼里。这个“文坛”由什么东西构成呢?当然文学史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装置,但韩寒们根本不把这个装置当回事,所以韩寒肯定不会骂文学史家。因为他根本不看。他的书,在市场上卖得好就行了。根本不用进文坛,进文学史,成为经典文学。昨天的深圳特区报上有一个报道,郭敬明的《小世界2.0》,一个星期卖了120万册,打破了新中国当代文学长篇小说的销售记录,一个星期把印刷厂印的120万册全部卖光,现在只好加班加印,这样的场景,太吓人了。最近,韩寒、郭敬明都在自己办杂志,韩寒的《独唱团》,郭敬明的《最小说》等等,都直接介入了文学生产。面对这种当代文学现象,一直以民族国家认同为己任的文学史是缺乏解释能力的,它当然也会对大学的文学史教育带来冲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文学史的学院化,现代大学拥有自己的空间,以主要进行文学教育的中文系而言,虽然近年也在不断萎缩,但作为一个传统学科,加上这些年大学的扩招,数量仍然很大。像北大洪子诚老师的当代文学史,出版几年就能销量过百万,上海复旦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销量估计也不会比这个少,在学校编写和讲授文学史,完全能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文学史家主要是与学生打交道,而不必与当代作家打交道。因为不太差钱,如果再加上一点清高,就没有必要写文学批评文章了。同时,做文学史教育的学者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工作,就是在大学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在大学开一些面向非文学专业的公共课,这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将来并不从事文学有关的工作,他们学习文学,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学习哲学、历史知识一样。这样的文学史写作和教育,也就自然与当代文学关系不大了。
今天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很难以八十年代的方式对待文学。八十年代,我们理解的文学就是纯文学,今天,能对一般的读者甚至学生产生影响的主要媒介是网络和影视。纯文学、经典文学的销量在下降,读鲁迅的人越来越少,只有怀旧的、缺乏购买力的人还在读,作为市场主体的青少年是不读的。我想,这样的状况肯定也是艺术界的现状,甚至是更加激烈的现状。因为艺术品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比文学激烈得多,与此相应的艺术史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难以把握。我非常期待在能够从在座的同行和前辈这里获得启示。我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艺术史如何处理艺术市场上的天价作品?比如F4的艺术价值问题。我看到论文集里面有文章谈到这个问题,好像是北大艺术系的朱青生老师说,他们编《艺术年鉴》的时候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那就是努力做到不受商业影响和保持学术性。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政治正确,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因为要厘清“艺术”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作品的价值到底由艺术史家决定还是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定,这可能是永恒的争论。在座的有不少知名的当代艺术史的作者,我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各位决定在艺术史中对某些艺术家大书特书的时候,是因为你确实认为这些艺术品价值高,还是认为这些作品卖得好?如果是后者,那就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排名来写艺术史就行了,谁的作品买价高,谁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相反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独立于市场以外的价值判断是否可能,它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艺术史、文学史是不是可能在市场以外再确定一套价值标准?
再回到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艺术史与当代艺术”上来,虽然从当代文学史本身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但显然仍然不能化解我们对当代文学能否写史,当代艺术能否写史的疑问。这也是论文中大家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艺术史一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是“当代”就不应该是“历史”,“当代”就是永恒的当下,一旦当“永恒的当下”不得不把自己历史化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这使得当代史变成了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一方面当代艺术是反艺术史的,当代文学是反文学史的,文学艺术只能由艺术本身、文学本身来加以界定和确认,而不是由文学史艺术史来界定和确认。文学和艺术的存在状态就是行动、实践、冒险和探索,是一种对可能性、创造性的寻找,但另一方面,我们关于艺术关于文学的定义又不能不来自艺术史、文学史。因为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本身是无法呈现意义的,它只能被言说,被阐释。因此,文学和艺术又不得不在一种历史化的过程中获得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写当代文学史或当代艺术史的人,都是在从事一种悖论性的工作,扮演的是一种类似于堂吉诃德的角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文学史和当代文学之间,在艺术史和当代艺术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关系,是一种博弈甚至是一场战争。因为当我们用文学史进入文学的时候,用艺术史进入艺术的时候,文学史无法逃脱历史的宿命,强化了文学和艺术作为“他者”的“不可见”。但规训永远不会停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冲动,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这可能也正是人文学科或者人文知识分子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样一种角色,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文学史家的角色会不会终结于这样一个时代,这个由新媒介所改变的时代,这是我深感困惑的问题。昨晚我翻看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觉得这里面让我感兴趣的问题非常多,尤其难得的是今天会议的代表们不仅仅包括艺术理论家和知名的艺术批评家,还包括国内一些非常优秀的艺术史写作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围城》里面曾经调侃过做理论的人说:“理论是由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我自己做文学史研究,对这一点就感受很深。当我们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空间非常大,天马行空,但一进入到文学史写作,就会发现所有的理论都是空谈。现在有机会听到实践者来谈理论,我们有理由对今天的讨论充满期待。我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鲁虹:谢谢李杨教授的精彩演讲,我认为他的演讲肯定会对会议的与会者有很大的帮助,他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如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问题,艺术史与当下关系的问题,等等,都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下面请大家对李杨的报告进行提问。
吕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想了解一下文学、史学领域的讨论,面对当代文学的时候,每年有2000多部小说问世,肯定是读都读不完。刚才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经典?我觉得什么是经典并不重要,主要是写文学史的作者他怎么办?目前文学史里面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他怎么具体面对它,处理它,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他有没有一套标准,有没有一套工作程序,使我对每年2000多部作品进行消化。或者干脆说我消化不了,那我怎么过滤?过滤完了以后再完成写作,或者我干脆不写了,没法写,文学史里面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艺术史也面临这个问题,每天有如此多的艺术家做展览,杂志、媒体,看都看不完,展览也看不完,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艺术史?马上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具体化的难题,我想了解一下文学史的做法。
李杨:谢谢吕澎老师的问题。一年近2000部长篇小说,不可能都进文学史,你必须选择一部分,那么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我在阅读《论文集》的时候,发现很多老师都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那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纯粹客观的、大家认可的标准,这种标准到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呢?
老实说,80年代的时候,可能使受社会历史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影响,我们都倾向于相信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客观标准。但90年代以后,随着后学的兴起,对文学史理论的讨论越来越多,比如我前边谈到的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对现代文学的编纂史,当代文学的编纂史进行了一种知识系谱学的清理之后,我们就很难再相信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标准了。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文学史的“写作”。如果是一种“写作”,那么,以什么立场,什么标准来写文学史,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问题。
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为例。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但我们这种知识从何而来呢?来自文学史。建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这样写。但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位名叫夏志清的华裔学者用英文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熟悉的标准写。比如他认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是张爱玲,说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史中,他重新安排了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座次,给张爱玲的篇幅超过了鲁迅。除了张爱玲,他还给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很高的评价,而这些作家,在50-8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是根本看不到的。夏志清的这部文学史是第一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美国影响很大,后来在台湾香港出版,为两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在台湾和香港,人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张爱玲,甚至只知道张爱玲。张爱玲比鲁迅有名得多,也重要得多。
文学史是否存在永恒的标准,实际上说的是文学是否存在超历史的、永恒的标准。对这个问题,不同的文学理论有过不同的解答。比如社会历史批评就认为文学是现实/历史的反映,好的作品就是对现实/历史的真实反映,而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文学的价值体现在文学形式上,存在一种超历史超时代的文学性,文学史就是要记录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后结构主义,包括近年兴起的文化研究则主张从文本进入现实,反对永恒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认为任何文学观念都可以而且应该被历史化。所以,我们写文学史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在以何种方法写文学史。我记得在《论文集》中看到有的老师强调我们在判断艺术作品价值的时候“直觉”的重要性。其实我认为直觉从来都是靠不住的,直觉的后面就是知识。在批评家、文学史家和作品之间并不透明,而是存在着某种中介,可能是语言,也可能是方法和知识。如果我们可以完全靠直觉去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那大学教育就可以取消了,因为直觉都是天生的。中文系可以取消,艺术系也没有必要存在了。我们在决定把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写入文学史或艺术史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作家与艺术家符合我们的艺术标准。用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来说,就是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不是你评价这个作品,而是你使用某种方法评价这个作品。只是对这些方法,我们不一定能形成自觉意识罢了。如果承认这个问题,那我们对方法的追问、自我反省、自我意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鲁虹:谢谢李杨教授,因为时间比较紧张,这一环节只好停止。我们下面会有机会与李杨教授做更好的互动。接下来进行讨论的第一场,主持人是孙振华,发言人是吕澎、刘淳、靳卫红、杨小彦,请各位嘉宾上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