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尼被称为意大利电影之父,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费利尼更以他强烈的个人标记——“费利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他认为一个“精神型”的人,在其性格中总是保持着一种青春或是童心的强有力成分。

对于电影,我首先着迷于细节的氛围
费里尼访谈
问:吉迪恩·巴赫曼
答:费德里科·费里尼
您总是说您是一名故事讲述者。哪类故事能使您着迷,为什么?
这些故事产生于我自身、我的记忆、我的梦幻、我的想像。它们自发而来。我从不坐下来决定创作某个故事,这不是一种经过规划的活动。它往往是一种得自个人阅读或个人经历的启示。这些东西遇上了借口,它们在我的意念中遇上了某种引发性的东西,比如在地铁站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张脸庞或钻人我鼻孔的某种气味、突然发生的某种声音,它不知怎地引起了我的幻想,我就创造出了人物和情境。它们似乎自己各就其位,不用我积极干预便在我的意念中成形。然后我的职责就是顺从它们,和它们小聚一段时间,和它们结为友伴。这就是它们怎样转变为故事的过程。
使这一过程得以开始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您在地铁看见的人,又是怎么回事?
通常是某种打动我、感动我、使我惊讶、使我发笑的东西,人的所有东西、所有矛盾、所有成分的表现,它甚至可能就是某人身上的那种向你诉说有关他的一个故事的东西或是使你想要创造一个故事的东西。但在我看见的那个人和这事在我心中引发的故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它可能的作用就是帮助制造一种气氛。
从远处窗户反射而来的一道闪光、一线阳光会吸引你的注意。而当你走近窗户时你意识到窗户是街上和城市里的一个建筑物的一部分,你跟随着这道亮光就像跟随着一条引线,它带引你慢慢地但总是愈来愈深人地穿过那座城市、穿过你在那里遇到的人们的生活天地。
据我所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似乎有一种无法抑制的不断想像眼前所见以外的天地的倾向。我感到我的影片已经在那里等着让我以最自然的方式去一一会见它们了。这就像一列在已定的轨道上行进的火车,等着它的是一个个车站。现在回顾我的影片,我感到它们就像早就等着我到达的车站,而我必须做的——这正是我的工作——就是不要偏离那条轨道。要遵循这条路线、按原计划正点到达,同它们见面、按原计划把它们制作出来。
我真抱歉这听起来是如此玄奥。在这样一类的谈话中,人们总会发现自己在过分地讲求哲理和过分地耽于幻想,因为实际上事情要简单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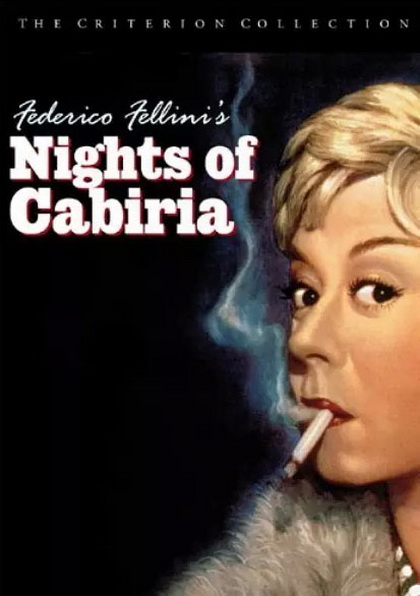
卡比利亚之夜 Le notti diCabiria(1957)
您怎样认出那闪光、那窗户的反照,您是被某种有形的东西所吸引吗?
我想领悟到情况已经发生、首次接触已经完成或至少你已同那座遥远的城市——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看见它——即同那部影片相距不远的信号,是一种欢愉的感觉。一种仿佛充满着你的整个机体的欢乐、一种意外的喜悦之情。这种喜悦之情是这部新作对我表示的问候,它通常包含着有关那部新电影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


《八部半》剧照
这样说来是否有待处理的就是一个形式和风格的问题,您怎样把幻想置于形象之中,即把那远方的城市放到银幕上去呢,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需要在你原先想要做的,换言之,在你的想像领域内自然呈现出来的那部电影和你现在实际制作的那部电影之间维持一种稳定不变的平衡——当然它经常有被打破的危险。所以,比如说我就不喜欢像我的大多数同事那样或像我开始搞电影时那样去看样片。当然情况不是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不是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噢,费里尼,他可从来不看样片的。”原因是我已认识到,看了样片你就开始看到了你正在制作的影片,而不是你原先想要制作的那部影片。到头来你会慢慢地按你实际的产品去修改你的意图。我却不然,我需要继续这样骗自己我还在继续拍着那部原先我脑子里产生的影片。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拍我理想的影片,就能把自己的幻想保留到最后一刻,而到那时,我就再也无能为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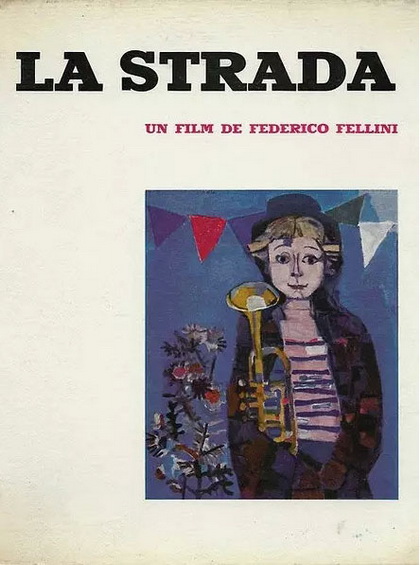
大路 La strada(1954)
如果您为了不去破坏您心目中的那部电影而对您所拍的电影佯作不知,那么当您面临电影制作过程必然会带来的那些必要妥协时又怎样维持您原先的见解呢?
我以为精神型的人——我们往往把这种人定名为创作者或艺术家——在其性格中总是保持着一种或是青春或是童心或是纯真的基本的、强有力的成分,因而他需要一个极有权威的管理人、顾客或老板拉着他走,真正地使他把他的梦幻具体化,实质上是把梦幻变成一种产品、一种可以传送之物,一种语言。在意大利,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这样的传统需要另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有时是精神权威,如教皇,有时是世俗的权威,如某大公、某皇帝、某国王向我们下令,去给他们作一幅弯顶绘画、创作一帧壁画、写一首短歌。
所以您所谓的电影制作过程必然会带来的那些妥协实际上是对我有用的,因为它们稍稍约束了我的全盘自由,即便我总是埋怨说它们会剥夺我的自由。我以为对于声称要向别人叙事、要描述世界、在故事里再现世界的那些人来说——当然尤其自称在从事现实的解释工作的那些人来说,全盘自由会很危险。幻想向你提供其形象的方式和你最终实现这些形象的方式不同,前者较后者暗示性强得多,有魅力得多,闪烁性大得多,所以银幕上难以抵制的一个诱惑是把一切表现得朦胧、飘忽和暖昧。把所有这些不可名状的、松散的想法具体化为形象是一件重活,所以我们需要旁人来促使我们去完成这事。
到头来,我认为,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位顾客、一个需要你的产品的人,以使创作得以实现、以引发你的意向——或让我们再次使用那个可憎的字眼你的灵感——与意向的具体化的实际行为之间的那种媒质般的相互作用。所谓媒质般的,我是指某种可感而不是已知的东西,某种我们认为必然存在但除了通过上述具体化之外又无法证明这种存在的东西。而具体化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又可能使它更难捉摸。由此可见,我们甚至都不能证明那个通过我们直觉产生的东西的存在,而且它也许永远只是一种梦幻、一种我可能在下一部影片中试图实现—或者我永远都不会实现—的东西。

《甜蜜的生活》剧照
您的电影完成之后成了您心目中的什么形象?儿子?女儿?父亲?母亲?情侣?
哪个都不是。事实上我并没有感觉同它们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对我来说它们似乎更像陌路人、素不相识者——我只是出于一连串神秘的理由感觉自己和它们有一阵短暂的亲近它们则声称已经选定我来赋予它们以形体与品格,并使它们有可能认出它们自己的模样。这仿佛是共同作一番气球旅行,处在同一个汽球下面,而这个大气球就要由我来设计、充气、确定其大小与品格。一旦我完成了这些职责,对我来说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它——影片——走它的路,它的面貌是我认为他要我给予它的那种面貌,它的身份是我感到它要我给它确定的那种身份,我也走我的路,寻找或等待另一个幻影,而果不其然,我会感到它在徐徐向我移来,无形地激励和促使我给它也造个脸庞、个性和故事。
这是否意味着您真的不大在乎您的影片此后的命运,而只在乎对它们的创作?
制作影片,即在沿路车站上的停留,对我来说仿佛是与居住在这些车站上的陌生人的一系列关系。他们一旦被认识、确认、具体化并似乎“被捉摸”透了之后便又离我远去,甚至连再见也不说一声。或许也可以说仿佛我和前站结清帐目之后继续向下一站前行。这也许就是我通常不再看我自己的影片的原因。对我来说,再次相遇似乎并非我们同居的过程的一部分,似乎影片的任务只是露面,我的任务只是加以具体化而已。

阿玛柯德 Amarcord (1973)
您说的激发起您的创造力的这一切东西本质上是您自己内在的东西,只有引发您创造力的刺激物才是来自外界的东西。难道您从未有过表达您生活的时世的某种东西的激情吗?您的电影中的主人公往往显得有点迷茫——这是否因为您在现代社会中也有此感?
我之所以常常被问及这类问题,我的影片之所以常常被人作出与时世有关的解释,是因为过去我影片中的中心人物曾——略显肤浅地——间或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其作者——我。《八部半》就是一例。这么说我感到略显大胆,但又显局限,因为我感到在作者的所有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出他来,而且不只是在人物身上,在布景、物体、音乐中都可以看出他在其中。在使人物具体化的过程中作者可以对某甲或某乙寄予更大的同情或好感他也可以挑选他的人物以便说——或让他们说——一些他在自己当时的幻觉中以为是表达他自己的心声——而不是他人的心声——的话,但在正常状态下,这种直接的关系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你不可能借你的某一人物之口把你自己的想法或你自己的哲学观说出来,然后还指望它成为最能表达那个人物的话,或指望它会真正传达出银幕上所表现的真情实感。相反,我感到最能表达作者的东西是最不易知觉的东西,那些最不受现实和概念化过程支配的东西。事实上,我认为正是在作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中的毫无意识之处,才最清楚地暴露了自己。
不过您的许多影片都是有明确的历史时代和背景的,这不可能全是下意识的吧?纵使您不作有意安排,您也在说着那些您对那个时代和那个背景所感受的事情啊!
既然你让我反思和寻找我工作中的有意编排的成分,也许你说的真有道理,因为我希望讲述我这一代人的一种多少有点发自内心、多少有点公开表露、多少有点矫饰的不快。很可能我多多少少在有意识地让我影片中的人物——通常是马尔切洛演的——说些这样的话这话能在上述意义上使我得到满足、能够表达一个人物的不安和忧郁——多多少少意识到的和发自内心的不安和忧郁——他感到自己已经濒临一个难以继续与他周围的现实保持合拍的时刻。而这种情形往往被解释为我的不安和我的忧郁。但如果这是我有意所为,这种直线条地看待人物的方式也只不过是一种故弄玄虚而已。我并不认为我所做的会跟我发生一种不由自主的等同关系。

《卡比利亚之夜》剧照
您内心所感受的不安会不会和电影制作过程本身有关呢?
在我即将开拍一部影片之时我确实感到不安,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很大的不安。我在拍摄一部影片的时候常常怀有几乎反感的情绪。这时我对影片产生了怨恨的情绪我开始认为拍它没有什么意义,我开始产生一种因个人被迫要去做某些事情而出现的恼怒情绪。但是我习惯了这种情绪,而且我知道实际上这种情绪乃是我的影片即将出世的征兆。这种反感、这种怨恨对我来说表明我必须着手进行。我到了如此不安的地步以致我必须拍这部影片,以摆脱这种情绪。我要脱身,我拍片,仿佛我在摆脱某种东西、仿佛我在逃跑,以便摆脱这种东西、释去这一重负。就像除病似的。我无意夸大创作活动的病态的一面,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位素不相识者、我前面说及的那位——他既非我子又非我父,而是催我给他以生命的一个蓦地出现在我近旁的身影——是一种传染病毒。
近来这些素不相识的身影变得益发令人不安了,因为它们迫使我处在一种令人无限心烦意乱的关系之中。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这种不安、操心和厌恶之感,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和下列简单、外在的事实有关。几十年来我的影片在获得开拍的机会以前都已经历了太长的、足以使我丧失热情的时间。当具体细节一一落实时,停车场上那种没完没了的等待就足以驱散我原先的激动。当制片人之间做着交易,根据他们的贪得无厌力图为影片制造财政经济上的机会之时,我却像一名三米跳板上的跳水员,经常得双手前举,保持起跳前的平衡,但又欲跳不能,因为他们还得把池子建起来、放水、招揽看客……最终你已经不是在做什么跳板跳水的动作了,而只是把自己甩出跳板,以了结此事。

《卡比利亚之夜》剧照
当您工作的时候,我从未感到您在影片拍摄的间歇期内的那种消沉。
这是因为其他事情的介入。尽管我患有这样的神经过敏症,但我一到摄影场就会重新开始迷上这个工作场地和它所包含的诱人的一切。我看到同事们都准备就绪,布景都已经全部搭好,然后,当灯光被打亮时,我就被这一切所组成的浪漫情调降伏了。我又复职当上了木偶剧表演者、牵线木偶的表演者、故事叙述者。而这一切突然又变得令人愉快起来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在这生活中认出了我自己。不安的心情也就随之消失。
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1.20—1993.10.30),意大利导演、编剧、演员。著名作品有《大路》、《八部半》、《阿玛珂德》等,五次获得奥斯卡金奖。费里尼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
本文节选自《电影季刊》第47卷第3期(1994春),肖模译。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