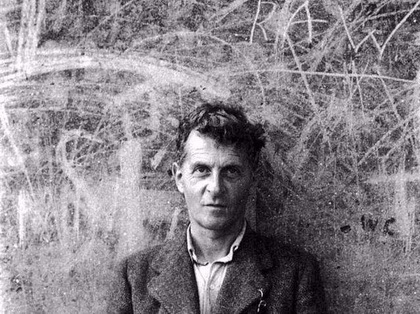一
我今天报告的标题采用了三个相近、相关的词语,如果把它们回译成德文原文就是:Transzendenz(超越)、transzendental(先验的)和transzendent(超验的)。这是我个人愿意采取的译法。众所周知现在汉语学术的译名有点混乱,有时简直让人不知所从。对于名词Transzendenz,人们没有太多分歧,通常把它译作“超越”,但也有“超越性”、“超越者”的译法,因上下文的不同都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出在另外两个形容词上。人们一般把transzendental译为“先验的”,但也有译为“超验的”;而把transzendent译为“超验的”,但也有译为“超越的”。我这里采取的“先验的-超验的”译法,有韦卓民先生在先,也有庞景仁先生的提倡。[2]
我考虑这几个译名以及相关的问题可谓由来已久,一直在琢磨这几个同根的词语。最近读到王炳文先生翻译的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3],引起了我的不安,才想起来要发表一点意见。王先生保留了Transzendenz(超越)和 transzendent(超越的)的旧译,但把transzendental改译为“超越论的”;此外还把a priori(通译“先天的”)改译为“先验的”。这种改动在我看来会引起大动乱。我就此问题请教过一些同行,比如倪梁康博士,后者说改得不错嘛,他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一书里就已经这样建议过了;但他也承认王炳文先生此次改动可能过于猛烈。[4]兹事体大了,非一般的译名之争可比。我们中国哲学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哲学基本理解眼看就要动摇了——我们一直都在思想的“先验问题”、“先验现象学”和“先验哲学”之类,现在却成了“超越论问题”、“超越论的现象学”和“超越论哲学”了!这是何等的震动!至少在我,是有一点不知所措了。
王炳文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他这次把transzendental改译成“超越论的”,说是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译法,也肯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我仍旧认为理由是不充分的。概括王炳文先生提供的理由,盖有三项。其一、当transzendental与Erfahrung在一起组成词组时(如在胡塞尔那里),译为“先验的经验”就好比“圆的方”或者“方的圆”。其二、通常把Transzendenz译为“超越”或“超越性”,把transzendent译为“超越的”,为什么非得把transzendental译为“先验的”(或者“超验的”)呢?其三、胡塞尔以transzendental一词指称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的、超出自然的世界的、超出生活和科学的自然的实证性的研究态度,故应当译为“超越论的”,如若把它译成“先验的”,就有可能混淆“超越论的”态度与“自然的”态度。[5]
关于第一个理由,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若要这么来想,那么,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也同样是“圆的方”或者“方的圆”—— 哪怕依照王炳文先生的改动,把它译为“先验综合判断”也仍是如此。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字面上的考虑,比较能成立,但也并不能支持“超越论的”这个译法。因为从词源上来看,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的意义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从拉丁文的动词transcendere派生出来的,而后者的意思是“超越、跨越、越界”(hinübersteigen)。[6]如此看来,若要统一,我们就得把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一律译为“超越的”,仍不至于推出“超越论的”这个译名。第三个理由涉及义理,我们可以同意王炳文先生的理解,但问题在于:“先验的”一词为什么就不能指称“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的、超出自然的世界的、超出生活和科学的自然的实证性的研究态度”呢?
至于日本学者的译法,我以为只能作为参考,并不构成真正切实的依据。
的确,如前所述,如果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用法来看,我们似乎有理由把这两个起源于拉丁文动词transcendere(超越)的形容词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统一译为“超越的”。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中世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的,而是在康德哲学以及后康德哲学意义上理解它们的。如我们所知,正是康德首先赋予这两个形容词不同的含义,认为不能把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混为一谈。[7]
另外,至少在康德的意义上,我们在翻译这两个词语时,似乎还不能轻松地放弃“验”这个组分,因为这两个词语在康德那里都是相对于“经验”来说的——尽管transzendental是“先行于”经验,而transzendent是“超出于”经验范围之外。这也正是我依然主张“先验的-超验的”这个译法的原因之一。“先验”之“先”固然没有很好地传达出“超”的意义,但只要用心,也许我们仍旧能够体会到它的“逻辑在先”意义上的“超”。
二
以上只还是引子。我的目的不止于讨论几个译名而已。尽管译名的澄清是正确理解义理的前提,但倒过来的说法似乎更能成立。本文的真正意图是要从这几个基本词语入手,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结构和问题方向。对此我已经做过一个题为“形而上学问题”的报告。在此报告中,我已经试图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思想,从问题提法的角度探讨形而上学的问题结构。这里有必要先作一综述。[8]
形而上学的问题似乎特别简单:存在者是什么?但从此问题中,我们可以引出如下两个并不简单的问题:一是“什么存在”(what-being)的问题,用希腊文表示就是to ti estin的问题。存在者是“什么”(Was),也就是存在者的“存在性”或“存在状态”,是形而上学首先要解答的问题。这个“什么”、“什么存在”(Was-sien),实即拉丁文的“本质”(essentia)。二是“如此存在”(that-being)的问题,用希腊文来表示就是hoti estin的问题。存在者“如何”(Wie)存在、存在者的“如此实情”(Da?),是形而上学进一步要关心的问题。这个“如何”、“如此”,实即拉丁文的“实存”(existentia)。
与形而上学的上述两个问题相应,形而上学的“超越”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什么存在”(to ti estin)方向上的“超越”,即向“本质”(essentia)的超逾,也就是作为“先验之物”(das Transzendentale)或“先验性质”(Transzendentalien)的“超越”。这是存在学要承担的任务。存在学在最普遍的特性意义上表象存在者整体(keinon),着眼于存在者的本质(essentia)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其二是“如此存在”(hoti estin)方向上的“超越”,即向“实存”(existentia)的超逾,也就是存在者的第一实存根据、作为“超验之物”(das Transzendente)的超越。这个“超验之物”具有神性指向,是神性的东西。正是在此意义上,“超越”(Transcendence)经常被解作“超越者”、神性者。这是神学要承担的任务。神学在最高的、神性的存在者意义上表象存在者整体(theion)。
于是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海德格尔下面这段总结性的议论了:
“如果我们再度回忆一下西方-欧洲思想史,我们就会了解到:存在之问题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是有双重形态的。它一方面问:存在者一般地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在哲学史进程中,在这个问题领域内的考察是在‘存在学’(Ontologie,旧译‘本体论’)这个名目下进行的。而另一方面,‘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也追问:何者是以及如何是最高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这就是对神性的东西和上帝的追问。这个问题的领域乃是神学(Theologie)。我们可以把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的双重形态概括在‘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这个名称之中。‘什么是存在者?’这个二重性的问题一方面是说:(究竟)什么是存在者?另一方面是说:什么(何者)是(绝对)存在者?”[9]
这段话的意思已十分显赫。海德格尔明确地把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区分为两个方向:一为“什么是存在者?”这是“存在学”的问题;二为“何者以及如何是最高存在者(绝对存在者)?”这是“神学”的问题。对于这个区分,如上所述,海德格尔也在字面上把它表述为“什么存在”(Was-sein)与“如此存在”(Da?-sein)的区分、“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的区分。
这也就是“先验问题”与“超验问题”之间的区分了。虽然“先验的”(transz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是近代哲学的语汇,但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它们指示的是西方形而上学的超越追问的两个平行的、相互区分又相互作用的方向,也即存在学与神学的方向。存在学试图达到形式的“普遍性”(先验的形式范畴),而神学试图达到实质的(等级的)“至高者”(超验的至高者、超越者)。
上述看法能不能在哲学史上得到印证呢?下面我们试图对此作一番讨论。我们的讨论显然只可能是粗线条的,出发点仍然是海德格尔,特别是海德格尔后期关于“存在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索。[10]如果上述看法能够得到哲学史意义上的支持,那么也就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证据,表明把transzendental(先验的)和transzendent(超验的)改译(理解)为“超越论的”和“超越的”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改译无法准确地传达出形而上学两个问题方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反而可能把两者混淆起来。
三
不少现代思想家(特别如尼采和海德格尔)把西方形而上学规定为“柏拉图主义”,可见柏拉图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导性意义。柏拉图的哲学是所谓“相论”。[11]在他看来,感官接触的具体世界是不真实的幻影世界,惟一真实的是“相”的世界。由此出现了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即虚假的个别事物的经验世界与真实的共相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众所周知柏拉图的处理是比较笨拙的,他提出了“摹仿说”、“分有说”:“相”是原型,个别事物是“摹本”,个别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分有”了“相”。进一步,柏拉图又用目的论来加以解释,以“善”为最高“相”的世界形成了一个目的论体系。
撇开这些老生常谈不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柏拉图的相论是不是合乎我们上面描述的形而上学问题结构呢?或者,形而上学的“先验之问”(存在学路向的追问)与“超验之问”(神学路向的追问)在柏拉图那里有何表现呢?
我们且来看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它经常被解释为一个教育譬喻,从《理想国》的语境来看,这种解释是不错的,但显然又是不够的。柏拉图的教育理想是以他的相论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在《理想国》第七卷开头,柏拉图写道:“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下述情形”。[12]这是通常的译解。海德格尔试图突破这种通常的见解,他建议把这段文字译作:“接下来让我们根据(下面描述的)情形来获得‘造形’以及无造形状态(的本质)的一个样子,后者(其实是共属一体的)关系到我们人的存在的根基”。[13]关键在于对其中的希腊文paideia(通译为“教育”)的翻译,海德格尔改译为“造形”或“赋形”(Bildung)。[14]“造形”是对人的本质位置的改变,后者又是与作为“无蔽”(aletheia)的真理的本质的转变相关联的。由此,海德格尔认为,“洞穴比喻”所描写的洞中囚徒、在洞中被解放者、洞穴外的被解放者就是人的居留的三个阶段,与之相应的是“无蔽之物”的三个等级(阴影、比较无蔽者、最无蔽者)。不同等级的“无蔽之物”实即显现之物的“外观”(eidos)和“相”(idea)的等级。“相”是通过“看”(idein)来通达的。因此,“看”的正确性成为关键。洞穴比喻中三个阶段的居留之间的过渡也就是人的“看”变得越来越正确的过程。这就暗示着真理之本质的一种转变。海德格尔指出:“从相(idea)和看(idein)对于真理(aletheia)的优先地位中,就产生出真理之本质的一种变化。真理变成了正确性(orthotes),变成了觉知和陈述的正确性”。[15]
因此,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就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了。它形象地说明了处于日常幻影世界中的人向作为“相”的真实世界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解说了对“什么是存在者?”问题的形而上学追问进程,从而也就说明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形态。甚至“形而上学”一词也已经在这个故事的描述中有了苗头。在说明目光对于“相”的适应时,柏拉图说:思想“超越”(meta ekeina)那种仅仅阴影般地被经验的东西而“走向”(epi tauta)“相”。[16]这里已经有了形而上学的“超越”之义。“相”是超感性的,是感官不能把握的存在者之存在。而最高的“相”是“善”的“相”,它是一切“相”的“相”,是一切存在者持存和显现的原因。这个最高的原因也被称为“神”(theion)。有鉴于此,海德格尔认为,自从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相”(idea),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就是形而上学的了,而形而上学同时也就是神学的了。[17]这就是说,柏拉图的相论已经包含着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路向,即存在学的先验追问和神学的超验追问。
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柏拉图相论形而上学的追问还是有自己的侧重点的:对“什么存在”(Was-sein)、“本质”(essentia)的先验追问始终是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着眼点和出发点,或者换句话说,柏拉图是从“本质之问”(先验之问)达到“实存之问”(超验之问),是通过“本质之问”来实现和完成“实存之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称为“柏拉图主义”或者“本质主义”。
四
我们经常说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这个说法在形而上学的“存在学-神学”或者“先验-超验”双重结构上看能不能成立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相论”并不能说明事物的存在。柏拉图所谓“分有”、“摹仿”之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是打比方而已,它们尤其不能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实体”(Ousia)说。[18]根据我们熟悉的哲学史描写,Ousia的基本含义是“本体”、“基质”、“基础”。这个 “实体”概念有三项基本规定:“实体”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不依赖于任何东西;“实体”在逻辑上是主词,不能表述其他东西,其他概念、范畴是表述“实体”的;“实体”在定义上、时间上、认识秩序上都是第一性的。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人”、“人是动物”,但决不能倒过来说“人是苏格拉底”、“动物是人”。在这里,作为个体的“苏格拉底”是“第一实体”,“属”、“种”是“第二实体”,它们作为宾词能够说明“第一实体”“是什么”,而其他宾词只能说明主词的数量、性质、状态等等。[19]
亚里士多德实体说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把存在学与逻辑学结合起来,预设了存在形式与思维形式的同一性。这种学说把判断中的主词-宾词(S——P)的关系看作客观世界中个别事物与一般概念(即属、种)的关系,实体-属性的存在学结构。亚里士多德由此形成了他的范畴理论。[20]他提出的“十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场所、时间、姿态、状态/领有、动作、遭受),既是纯粹的语言(逻辑)形式,又是存在的最基本形式的表达。其中只有“实体”能充当判断的主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十范畴”可表示个体的一切属性,例如:某某个体(实体)、黄的(性质)、中等高度(关系)、下午(时间)、在教室里(地点)、站着(姿态)、着装(状态)、被指定(遭受)、讲课(动作)。于是,我们就可以把某某的当下状态描述为:黄颜色的中等高度的着装的某某下午在教室里站着被指定讲课。关子尹先生举的例子是“黄狗”:“某甲的三岁大的黄狗昨日在市集上狂吠,给打了一棍子”。[21]范畴既是思维形式又是存在形式。范畴是纯形式的,是先验的,与实质无关。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可以说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存在学的先验范畴体系。它是在柏拉图相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若没有后者提供的形式化思维方式的基本准备,前者就还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又是对柏拉图相论形而上学的一个推进,只有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形式-本质”的领域才构造起来了,形而上学的存在学追问(先验追问)路向才真正地确立起来了。
与柏拉图哲学相比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路向还另有侧重。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相论根本不能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也就是说,相论不能说明事物到底是如何在场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个别事物即tode ti[个体、这个]的“在场”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的Ousia,我们不能把它译为“实体”,而应当把它译为“在场”和“在场者”。[22]当亚里士多德把tode ti[个体、这个]设为“第一实体”,把属、种设为“第二实体”时,他实际上是区分了两种“在场”方式:“第一位意义上的在场乃是在hoti estin[如此存在]中被表达出来的存在,即如此-存在(Da?-Sein)、existentia[实存]。第二位意义上的在场则是在ti estin[什么存在]中被追踪的存在,即什么-存在(Was-sein)、essentia[本质]”。[23]进一步,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此-存在”与“什么-存在”这两种“在场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energeia[实现]。
“个体”(tode ti)的在场是energeia。人们通常以后世所谓的Energie(能、潜能)来译解这个energeia。人们经常这样来解说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他用形式-质料,潜能-现实来说明事物的存在、变化。任何个体(实体)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例如一座房子,砖、瓦是房子的“质料”,但不是砖瓦任意堆起来就成为一座房子,决定房子成其为房子的是“形式”。“形式”、“相”、“属”在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即eidos。柏拉图说是事物分有了“相”。亚里士多德说不对,那是质料的形式化。质料是被动的基质,是一种潜能,形式给质料以规定性,使质料确定而成个体(现实)。这样一种解说看起来不错,但其实是让亚里士多德自相矛盾,也抹煞了他与柏拉图之间的基本差别。
亚里士多德关心的是个体事物(tode ti)的运动和变化,即个体如何“在场”,如何“产出”。在希腊人那里,这种在场、产出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以physis[自然]的方式发生,即让某物自发地涌现出来,二是以poiesis[制作]的方式发生,即把某物制造和表象出来。亚里士多德显然更倾向于从“制作”(poiesis)、“作品”(ergon)角度来理解事物的在场方式。[24]“作品”当然是一个完成了的东西。但海德格尔主张,亚里士多德对“作品”(ergon)作了一种动态的、动词性的理解。“作品”不是单纯的结果、成果,而是“在进入其外观的无蔽之物之中被展览出来、并且作为如此这般地站立或者呈放之物而逗留的东西意义上的作品”。也就是说,“作品”(ergon)更多地还是动作性的,指示着一种出场、在场的方式。[25]亚里士多德的energeia必须在这样一种“作品”(ergon)意义上来了解。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文energeia在字面上直接地意味着“在作品中”。这种“在作品中作为作品本质而出场”的energeia,海德格尔把它译解为“实现”。“这个energeia[实现]乃是tode ti[个体、这个]即当下这个和当下那个东西的ousia(即在场状态)”。[26]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还用他自造的entelecheia[隐德莱希]一词来说明这个energeia[实现]。Entelecheia的词根是telos,后者指的是“终点”、“终结”(而非一般译解的“目的”)。Entelecheia是“在终点中拥有自身”。制造运动到了“终点”,“作品”完成了,就完全具有了自身,达到了纯粹直接的在场,这就是entelecheia。诚然,亚里士多德的energeia[实现]说仍旧可以推向柏拉图式的目的论。即便我们没有把telos译成“目的”而是译成“终点”,仍旧会产生一个问题:最后的“终点”是什么?或者说,“实现”的动力是什么?由此势必推出 “第一动因”,即“神”。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追问路向,海德格尔作过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亚里士多德把第一位意义上的ousia(在场)看作energeia[实现],而这种在场在后世经常被解释为actualitas[现实性]、“实存”(existentia)和“此在”(Dasein)。因此,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揭示了后来所谓的existentia[实存]对于essentia[本质]的优先地位。柏拉图所思考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ousia[在场状态]),即idea[相]或者eidos[爱多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成为存在的第二等级了。[27]
我们已经看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各自的方式对ti estin[什么存在]与hoti estin[如此存在]、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作了追问和解答。两者的重点各有不同。柏拉图首先开启了是一个先验本质追问的形而上学传统,即一般所谓观念论、唯心主义传统;而亚里士多德借助于ousia[在场]和energeia[实现]之论,开启了形而上学实存论的超验追问传统。在中世纪神学形而上学对于希腊哲学的转换中,亚里士多德哲学受到的特别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当然,我们上面这种分别的说法容易令人误解,就仿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各执一端、南辕北辙似的。实际上,我们认为,两者的区别更多地是在入思途径和追问路向上:柏拉图试图通过“本质”之问完成“实存”之问,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惟有通过“实存”之问才能达到“本质”领域。以海德格尔的讲法,柏拉图为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作了准备,而亚里士多德为这个区分找到了概念表达。[28]
五
我们说“超越”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形而上学所从事的就是一种“超越的”的追问,即存在学的先验追问与神学的超验追问。我们这个说法首先会碰到如下一个问题:难道“先验”问题不是一个知识学(认识论)的问题吗?确实,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康德意义上把“先验问题”了解为“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把“先验哲学”(例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视为一种知识学哲学。
按照康德本人的说法,所谓“先验的”,“并不意味着超过一切经验的什么东西,而是指虽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在的、先天的),但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29]它并不是就我们的认识对于物的关系说的,而只是从我们的认识对认识能力的关系来说的。[30]至于“超验的”,则是超出一切可能经验界限之外,与之相对的是“内在的”(immanent)。康德据此把形而上学区分为“内在的”形而上学与“超验的”形而上学,前者研究出于纯粹知性的知识,后者研究出于纯粹理性的的知识。
作为近代知识学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首先试图在“内在的形而上学”意义上解决知识问题:知识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康德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先验唯心论”,表明他对知识问题提供了一个先验的解决方案。知识的起点仍在于经验,“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刺激”感官而生感觉。知识盖有两个成分:外来的感觉材料,内心有条理的先天形式(先天感性直观即时间、空间,先天知性范畴)。在“感性”层面上,康德力图阐明时间、空间直观形式如何运用于经验材料而得数学知识。进一步在“知性”层面上,康德阐明了 “知性”如何运用先天的范畴对经验直观加以进一步整理,使其具有规律性,从而证明自然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这里又出现了范畴问题。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是根据逻辑学中的判断表推出了他的范畴表的,推出由“量的范畴”(单一性、复多性、总体性)、“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定性)、“关系范畴”(实体性、因果性、共存性)、“样式范畴”(可能-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性、必然-偶然性)构成的十二个“知性范畴”。[31]但康德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赋予范畴以“先验形式”的意义。在康德那里,知性范畴不仅是知识的条件,也是知识对象的条件。因为在他看来,感觉材料加上时空直观形式,再加上知性范畴,不仅是知识的构成,也是现象界(知识的对象)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就是现象学(自然界)的“立法者”。这个“立法者”被称为“自我”(Ich)或者“先验统觉”(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上面还只是康德在先验追问方向上对知识问题和现象问题的解答。康德哲学还有更高远的目标,即致力于完成“超验形而上学”的任务。康德在此引出了理性问题。理性企图用“理念”(Idee)整理和统一知性知识,以达到无条件的绝对完整的知识。理性企图达到三个大全的“理念”:“灵魂”、“世界”、“上帝”。不过,理性在证明三个“理念”的存在时却缺乏更高明的手段,只能借助于知性范畴,而后者作为现象以及现象知识的条件只适用于有限局部现象界,并不适用于无限大全的本体界,故理性在证明“理念”时必然陷于“二律背反”。所以,康德得出结论:不可能有关于“灵魂”、“世界”、“上帝”的知识。它们是“超验的”。这是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理性神学——的否定,但并不是对形而上学的“超验”之维的否定,更不是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拒绝。
我们知道,康德哲学具有十分典型的二元论特征。这种二元论固然表现在康德对本体与现象、实践与理论、道德与知性的分裂上,但最根本的表征却在于他对“先验追问”与“超验追问”的明晰区分上。[32]在先验追问路向上,康德把“先验自我”视为知识和现象的“极点”;而在超验追问路向上,康德把“超验的”“理念”设为超越于知识和现象的、归于道德信仰领域的本体。就现象界来说,“先验自我”构成知识的条件,而“超验理念”构成知识的限界。
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理解为一种知识学,这是完全合法的,但又是不够的。我们同样知道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的最高原理是:“一般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33]康德这话难道仅仅是一个知识学的表述吗?显然不全是。康德在此实际上提出了知识学-存在学的双重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这个最高原理表达了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本要义:存在是“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34]因此我们就可以认为,康德在“先验”与“超验”之间的划分实质上就是“存在学”与“神学”之间的划界,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先验形式范畴是达不到超验之物的;不能把存在学的先验“本质之问”与神学的超验“实存之问”混为一谈。[35]
六
如果说旧形而上学往往通过存在学途径来为超验神学奠基的话,那么,经过康德哲学的划界,在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特别是在现代实存哲学)中,新形而上学所尝试的就可以说是一种相反方向的努力了:通过“实存”的追问来为存在学奠基,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为存在学寻获一个“实存”基础。
在这方面,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学”(“现象学存在学”)是一个典范。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明言:存在绝对是“超越”(transcendens),而只有从此在的“超越性”(Transzendenz)结构入手才能达到绝对的超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主张“对作为超越(transcendens)的存在的每一种展开都是先验的(transzendental)认识”。[36]毫无疑问,这里所谓“先验的认识”指的是“存在学的认识”,而决非“知识学的认识”。前期海德格尔的进路显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就是试图从人的“实存”(Existenz)和“此在”(Dasein)入手,重新提出“存在问题”,重构存在学,达到存在学的“先验的认识”;这就是说,海德格尔也试图通过“实存”、“此在”之问通达“本质”(essentia)之问。[37]在这个意义上——在追问和入思的途径上——,我们就可以认为海德格尔前期存在学具有超验神学的性质,至少在起点上具有神学的超验追问路向。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形而上学的名声不佳。基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等大哲都是激烈的形而上学批判者。基尔凯郭尔以个体实存为出发点反对基督教理性神学传统;而马克思把哲学批判的矛头指向柏拉图本质主义的观念论(或唯心论)传统,其出发点同样也是个体实存(生活实践)。
尼采把形而上学的历史称为“虚无主义”(Nihilismus)。他是从价值思想的角度解释形而上学的,从而把一切形而上学都规定为“柏拉图主义”,即“价值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本质是“柏拉图主义”。什么是柏拉图主义呢?简言之就是“两个世界”学说。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世界被“二重化”;尼采说是“另一个世界”。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构造出一个“感性—超感性”的二元对立。一切都是根据一个“超感性领域”而得到评价的。这个“超感性领域”(即最高价值)可以是上帝、道德法则,也可以是理性权威、进步、普遍幸福等等。而基督教就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尼采原话)。现在,尼采从其强力意志形而上学出发,认为由传统形而上学提供的“最高价值”都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构成力量,都已经沦丧了,也就是“迄今为止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的崩溃”。于是得出了一个虚无主义的结论。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贬黜”。[38]
尼采自称为“虚无主义者”。尼采是如何否定形而上学的呢?他说,“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39]存在世界(本质世界)不应当“存在”(sein),而应当世界(理想世界)并不“实存”(existieren)。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充分理解尼采这个断言了:这句话的前半句是一个存在学的否定,后半句则是一个神学的否定。尼采以虚无主义方式极其明快地拒斥了形而上学的“先验-超验”双重结构。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思想-词语的严格性要求即便对于尼采也同样有效。[40]尼采之为尼采,哪里是“癫狂”两字可以轻松了断?
2003年3月1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曙光楼703室
注释:
[1] 本文系作者于2003年3月1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作的报告,为作者对另一个报告“形而上学问题”(2002年9月20日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补充,后者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 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武汉2000年;以及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1982年。
[3]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2002年。
[4]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1999年,第456页。
[5]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2002年,译后记,第662页以下。
[6] 参看海因里希·施密特编:《哲学辞典》,斯图加特1978年,第452页。
[7] 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296,B352。韦卓民译本,第317页。我们通常更多地在“自我提高”或者“自我进步”意义上来理解“超越”。的确,“超越”(Tranzendenz)的动词形式transcendere的意思好像恰好与我们的日常理解相合。但拉丁文的“超越”是特指的,主要是指从“此岸”到“彼岸”的逾越。在具有存在学-神学结构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超越”,离上面这种通俗理解益发远了。
[8] 参看拙文“形而上学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9]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526-527页。
[10] 因此我们把本文副标题立为“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
[11] 人们通常以“理念”、“观念”来译解idea、eidos,从而对之作了一种偏向于主观、精神方面的理解。实际上,“理”(ratio)、“念”(idea)是在近代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意义。希腊文名词idea、eidos出于动词idein,“看”、“见”。所“看”所“见”为“形”、“相”,故把idea译为“相”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12]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1986年,第272页。
[13]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251页。
[14] 此处“造形”或“赋形”(Bildung)通译为“教化”。但海德格尔认为,该词的“教化”之义是迟至十九世纪才获得的。
[15]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266页。
[16]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516C3;中译本未能译出原义,见中译本,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1986年,第275页。另可参看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载《路标》,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234页以下。[17]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271页。
[18] 海德格尔则以“在场、在场者”(das Anwesen,das Anwesende)翻译亚里士多德的ousia。见我们下面的进一步讨论。
[19] 承认“属”、“种”是“第二实体”,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一着,它实际上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学先验追问留下了可能性空间。
[20] 参看关子尹:《从哲学的观点看》,台北1994年,第170页以下。
[21] 关子尹:《从哲学的观点看》,第176页。关子尹先生在此上下文中主要强调了亚里士多德十范畴的日常语言基础,所论固然深刻。但我的观察方向可能正好与关先生相左,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用意在于日常语言背后的东西,那个使我们之所以能如此描述事物的东西,就是先验形式层面的东西。
[22] 在海德格尔看来,“实体”(Substanz)与“理念”(Idea)一样都是近代哲学的概念。
[23]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八章,斯图加特1998年,第363页以下。
[24] 这一点也影响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器具分析和作品分析。主要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版;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以及“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94年;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
[25] 据海德格尔这里提供的解释,也许我们更应该把ergon译为“作业”,后者显得更有动感。
[26]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八章,斯图加特1998年,第367页。
[27]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八章,斯图加特1998年,第369页。
[28]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八章,斯图加特1998年,第366页。
[29]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1982年,第172页注。
[30]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1982年,第57页。
[3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70/B95以下;中译本,韦卓民译,武汉2000年,第105页以下。
[32] 正是因为形而上学具有先验-超验双重问题结构,所以一般而言,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二元论的。
[3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158,B197。
[34]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斯图加特1998年,第207页。
[35] 这同样也就意味着,惟有依据上面描述的形而上学追问路向和问题结构,我们才能理解和赞同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不仅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理解为一种知识学,而且更把它把握为一种存在学或形而上学。
[3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版,第38页;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第47页。中译本对这几个词语的处理并不妥当。我们认为,即便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先验-超验”(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t)的区分也是十分清晰的。当海德格尔说“现象学的真理乃是veritas transcendentalis[先验的真理]”时,他指的是存在学的先验追问。中译者把这里的veritas transcendentalis译为“超越的真理”,未能显明作者真义。
[37]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前期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关注远多于柏拉图。进一步,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几乎重演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老故事。
[38] 尼采:《强力意志》,第2条。
[39] 尼采:《强力意志》,第585条。
[40] 翻译的细心和精确要求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果我们没有在译文字面上把其中的动词“存在”(sein)和“实存”(existieren)准确地区分开来,这话就无法得到完全确当的理解。
来源: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