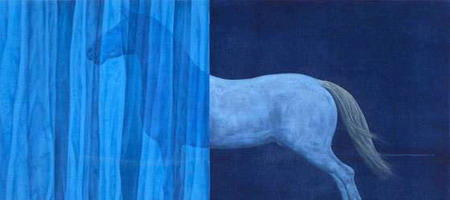文/查常平
就历史发生学而言,装置、行为这两种艺术形态的艺术意义,源于作品中的媒材与观念互动构成的个别场景。美术馆展出作品时需要装置布展,因为,作品同既定空间的场景关联的差异,必然带采观众的理解分殊;同样,艺术家为自己的行为表演设计的戏剧背景,要求观众在特定场景中领悟其行为的内涵。据此,在装置、行为艺术的创作中,艺术家如何挪用场景的问题,理应进人艺术爱者批评与实验的视域。本文以戴光郁近年实施的几件装置、行为作品为个案,侧重探讨艺术家在创作这类作品时挪用不同场景的艺术方式。
历史:场景的择取
场景差别于场所,它更多地类似于心理学上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场概念。美籍德国心理学家K·莱温(1890—1947),借用物理学的场概念,将心理场或“生命空间”当作人的经验与需要的场所,提出所谓的场理论。和心理场类似的场景,是生成性的,处于未完成时;与之差异的场所,是现成性的,处于完成时态。装置、行为艺术中的场景,指作品意义赖以呈现的境域。这种意义境域,由艺术家、接受者、文本及其置身的历史、社会、心理、自然诸因素共在互动形成。对于装置、行为的任何艺术文本的深度解读,都离不开场景问题。 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媒材,宣纸始终是汉族历史精神的物质见证。和旅居德国的中国艺术家朱金石对宣纸的无常性、虚幻性、相对性的直接自然呈现相反,[1]戴光郁利用宣纸、水墨制作的系列行为、装置作品,展开宣纸的浸润性能与人的文化生命存在的关系。1997年,在成都南郊一处民间坟场,他实施了《制造印痕的行为》。艺术家本人,静躺在自掘的坟坑里,人体的汗渍、大地的水气,在宣纸浸润下形成人体印痕。其实,任何民族的历史遗物,不过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文化生命体将自己的意识、精神印存于宣纸之类传播媒材留下的踪迹。它的物质样态,即广义的文本所内含的书籍、遗物、字画、印痕。《制造印痕的行为》,由于是在一处民间坟场实施的,其中的历史质素,表现在一位当代艺术家与过去死者的相 遇上,表现在一个生活于以当下为价值理想的艺术爱者对人的肉体生命结束后的去向关怀上。对不相信人将从死里复活的非基督徒而言,坟冢内的遗骨正是他们命运的终极印痕。艺术家在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他所择取的艺术观念——历史中的同在者全体(生者与死者)如何同在的观念,因着其行为特定的场所而生成为作品意义呈现的场景。艺术家在择取媒材与观念两方面,都达到了单纯性的指向。 除宣纸外,戴光郁在《边界》、《种瓜得瓜》里,还挪用了水墨这种历史媒材。“墨是苦难的颜色,在过去它作为一种艺术媒材为一个苦难的民族做见证,现在它和我们个体生命中的苦难感同在。”[2]水墨、宣纸,代表着世界的黑白两极,也是黑暗与光明两种价值观的媒介象征物。汉族历史的精神延传,通过它们在艺术史上固化为一种永恒的、富有期待性的物质见证,一种让艺术爱者驻足的历史场景。当代艺术中实验水墨的价值,并非在于对批评家所谓笔墨中心的持守,而在于拓展笔墨、宣纸作为艺术媒材潜在的观念图式的边界。戴光郁的墨纸装置,和实验水墨中王川的墨线图式、王天德的圆形组合、刘子建的分割构图、石果的框架结构、张羽的墨象空间有根本差别:前者已经突破了墨纸这种历史媒材的既定观念图式,后者依然停留在墨、纸和笔的相关性上。由混合着墨汁的泥土垒出的中国地图图形,在清水浇灌后,水墨互渗于宣纸上,图形随之隐失。中国历代水墨艺术家,借助师徒相续的笔墨程式所建立起来的水墨艺术的观念《边界》,在戴光郁看来本是可以证伪的。正如人们关于国家、民族、阶级之类的定义一样,水墨艺术只要被纳入历史的维度,其观念限定便不复存在。因为,无论在遥远的过去或将来,国家、民族、阶级乃至艺术的区别,都会从人的视野里消失;因为,那时只有人与人的共在,以及生者与死者在天地间的同在。 艺术的创造,同人的其他劳作一起遵循共同的法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3]在艺术家的意识生命里,他对水墨、宣纸的功用的主观理解,构成了他的作品图式的客观边界,同时是其赖以创作的种子或基因。《种瓜得瓜》这幅抽象水墨图景,在持守传统笔墨程式的艺术家心中,是难以想像的。其差异,仅仅作为个体生命的艺术家择取的媒材观念的不同。作品中的钱币,不再是人用以物物交换的货币而是传达艺术观念的媒介;墨汁、宣纸,也不是传统水墨画家用以除灭自己的个人性、进入历史中的他者之在的上手物。面对一样的艺术媒材,艺术家上手方式的殊异,源自其艺术观念的差别性。这种差别性的艺术观念,在装置、行为艺术的创作中,引导着作者对历史场景的择取,同时和他生存的社会场景相 关,并取决于他当下的心理场景。
社会:场景的隔置
如果说戴光郁择取宣纸、水墨之类历史媒材及生者与死者同在的历史观念来挪用历史场景,那么,他对于社会场景的挪用,则以观念及媒材的隔置为方式;如果说历史场景因场景本有的生成性特质而成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呈现境域,那么,社会场景,也因同样的特质构成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境域。这里,作为择取之物的历史场景以及作为隔置对象的社会场景,不能被误解为星星、月亮、太阳之类物质性在者。 艺术家从多种媒材及观念中,择取一种媒材和单一的观念装置一件作品,它的意义敞现,源于他的择取之对象本身。艺术家挪用社会场景时所选定的隔置这种方式,则是通过被隔置之媒材、观念企及它们所隔置之对象,由此呈现出作品的意义。不过,在场景挪用上,择取与隔置两种方式,都带有媒材与媒材、观念与观念的差别性的规定性。因为,择取意指被择取对象和所择取对象的差别,隔置也因被隔置对象和所隔置对象的差别才成立。 挪用社会场景对隔置所具有的上述性能,在戴光郁的《点石成金》系列里,偏重对象化为观念隔置,在《抱残守缺》的行为中具体化为媒材隔置。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点石成金》让人联想到中古乃至17世纪末炼金术士执着的点金石。据说,这种又名哲学家的石头,能将贱金属变为金银之类贵金属,制成长生不老药,提神强精、修炼灵魂。今天,炼金术士以肉体生命的生存为永恒的价值理想破灭了,但他们通过实验研究物质及其相互作用的努力,却为服务于人的肉身的有限生存价值的近世化学、药物学、冶金学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点石成金》在字词结构上,又同汉语神仙传说中的“点铁成金”相似,后者指仙人用手指一点使铁成金。当代人虽然不再相信点铁成金的传说及点金石的存在,但它们内含的价值诉求,不仅未从其心灵深处消失,而且表现得变本加厉。他渴望将贱金属变成金子,梦想把书籍、冰棍、米饭、苹果、树叶、城墙砖之类非金属的物质性在者点化为黄金。《点石成金》系列从当代人众多的观念中,隔置出统治人们心灵、支配人们劳碌的拜金主义观念。这观念,也是艺术家主题关怀的对象。 由社会场景的隔置所得的拜金主义观念,只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价值表象。其实质寄托着膜拜物质、肉身为特征的偶像情怀。金钱本是受造物,对于人的意义在于:它能满足我们的肉身快乐。因着人对肉身价值的无限信仰,导致人类爱钱财,由此生出种种社会罪恶。钱本无罪,但对钱的贪爱构成万恶之源。当代人越来越以此为人生得救之路,正如他们对科学的迷信一样。难怪在完成《点石成金》之三的行为时,艺术家自觉选定当代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波普尔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为媒材。此书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关于艺术、历史、哲学的讲演论文集。 《点石成金》的行为,从物质主义、肉身主义的社会价值体系中隔置出拜金主义艺术观念,这是通过把同类物质局部金色喷漆即媒材隔置达成的。例如:在该系列行为之三中,喷成金色后无书名、无作者、无出版者的作品与各种书籍的并存,再加上围观的购书者、书店本身的陈设,一同生成此件行为作品意义敞现的社会场景。金粉对作者、出版者、书名的埋葬掩盖,准确地传达出拜金主义的价值理想对当代人所创造的文化的否定。 媒材隔置,既可采用《点石成金》系列里对同类物质局部隔置的方式,也可借助如《抱残守缺》的行为里将一种媒材抽离、再还原到它可能遭遇的社会空间中的途径。任何社会,都离不开人的意识生命中的社会观念和人的精神生命中的公共空间。艺术家用一年的时间,以把玩的心态随身携带修复的破碎花瓶,出入于监控的商场、奔驰的的士、驻足的车站、娱乐的场所、交往的茶坊之类公共场所。花瓶残缺复原,但照旧为人爱不释手,如拜金主义使人心劳日拙,又令人心驰神往一样。残缺的花瓶,是艺术家共在的朋友;人心的所爱,才是他最信赖的同伴。花瓶因为破碎,从同类中被隔置,在艺术家的上手把玩中又回到当代人的生活空间,在一个相对有限时段内将《抱残守缺》的意义境域——社会场景——彰明较著。 从这件行为作品里,我们仿佛见到了一切在艺术图式、艺术观念的主张上抱残守缺之士的原型。
心理:场景的还原
无论装置还是行为,都要求艺术观念和艺术图式的完美统一。我们从《点石成金》、《抱残守缺》的行为图式就能直观出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即当代人的拜金主义价值取向和死守肉身拒绝向属灵世界开放的价值诉求。两者内化为当代人的心理场景。拜金主义作为肉身崇拜的物化形式,其最终的价值指向为:当代人对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精神生命的不朽永恒的认信。这种认信,并不为当代人所特有。早在公元一世纪,倡导人应追求属灵生活的使徒保罗,便流泪写信给腓立比人,告诫其中以基督十字架为仇敌之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3章19节)。保罗所说的“地上的事”,指对物质、肉身的崇拜。 择取、隔置,呈现出相关之物的差别性;心理场景的还原及后文要论述的自然场景的体现,开启差别之物的相关性。还原,意味着剔除多余的物质与观念,进而谋求它们在艺术观念图式上的纯粹性。由于艺术家在历史场景的择取、社会场景的隔置上,其前提离不开他的心理世界中的意识生命在逻辑上优先预设的观念图式。从戴光郁的艺术观念历程中,我们发现他在挪用场景时也有从历史、社会到心理的还原特质:从《制造印痕的行为》中生者与死者的肉身同在、《点石成金》系列里生者与物质的肉身共在、再到《还原-中药石》中个体生命的肉身存在的还原。 作品《还原-中药石》,经过艺术家的观念还原后得到的,是以肉身价值观为内容的心理场景。这种价值观,包括汉族一贯持守的以肉体生命的生存为精神生命的存在之道统。和宣纸、水墨一样,中药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载体和价值理想的传承。中医方剂学,最初同汉族认信的肉身不朽关怀相联系。在当代社会,“药物与肉体生命的关系,彰显于人对药物的依赖性,其形下观照征候昭示出:守持肉体生命不衰,即守持肉体欲念的希望所在。对药物的迷恋,显然道出了肉身对‘幸福’注解的内涵”。[4]药物所维系的人的肉体生命,如果仅仅以其本身为价值,这不但未提升人的生活,而且将人的全部非肉身的意识、精神、文化,已不再有意义。一种与动物肉身无差别的人的纯粹肉身,既是对人的精神性的泯灭,又是对人的肉身性的虚化。这将生出无灵无肉的在者,一个个仅仅在避孕套的利用中被动物欲望所支配的中药卵石。 艺术家挪用心理场景达成的观念还原,在戴光郁的行为作品里,借助于对避孕套这种现代文明之物的媒材还原。他在中药卵石内放入避孕套,将其投回大自然中。由此彰显的现代文明的自然人化主题,不过是人的肉体欲望的物化。人的自然化,仅仅是人的肉身化、动物化的学术表达。汉族历史一再经历的神迹的消隐、文化的无力、精神的贫瘠、心灵的沉沦,全由于人对肉身价值观的非理性认信。此种现象,尤其显明在我们这个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历史传统的汉人身上。我们从上承受的儒道之道,实质为关于肉体生命如何生存延续之言。 ‘ 《还原-中药石》还原出当代国人心理中的肉身生存场景,《还原-水迹墨痕》还原出他们的肉身延续场景。后者越过当代人表面的拜金主义观念,在墨汁、避孕套冷冻成的冰砖溶化于宣纸形成的水墨图景里,直指汉语思想中的儒家之道——一种以肉体生命的血缘延续为价值认信的人生理想。 不过,当代艺术的使命,并不限于呈现当代人的心理场景。汉语思想,虽然的确由于神性超越之维的消隐,留下的只是肯定肉身之在的价值体系,虽然这种价值在当代国人的生存现象中继续被强化,但艺术家展开媒材还原与观念还原的目的,是要警醒人如此生存延续的末世论结局。
自然:场景的凸现
经过艺术家还原当代人的心理场景得出的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内容的价值观,一旦僭越为一种社会主流信仰,一方面导致人的丰富性的单向度化(以肉身为唯一的向度),另一方面迫使人以对象化、实用化、工具化的立场审视外在的肉身(自然)。美丽的自然景观,除了具有单一的经济价值外,便毫无价值。无限神化的肉欲,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之根拔除得一干二净。此时,艺术的责任,或许就是重新引领人类回到自然与自身的丰富性中去,再次确立人的肉身与自然之终极相关。 1997年于拉萨河畔完成的《倾听》行为中,戴光郁所要凸现的自然场景由汩汩的河水、逐渐遭污染的河岸与充满关怀的人体构成。一段同河水相接的白布,和朝圣般的倾听行为演示,带出倾听者、倾听的场所、言说者。是谁在育说?言说者言于何处?艺术家举目问天,明晰而神秘的苍穹,迫使他把全身收回,浸沐于水中,两手向冰骨的河流伸去。水声与作者俯向水面时血脉的跳动声相融,人水的相交言说出一切:谁将作者、河水构筑为《倾听》的场景?又是谁在驱动着人追寻《倾听》的意义? 不能忘却的倾听: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到该倾听的时候了。人类自信征服自然,反而遭自然逼迫,因为人类忘却了倾听自然的诉说;人类苦苦寻求和平,反而备受战争摧残,因为强者忘记了倾听弱者的呼声;人类热情开启自我,反而对良知更加模糊,因为我们总是沉缅于絮絮叨叨的肉身言谈。 因此,在有血与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在有生命的地方,我们便需要倾听。 从媒材和观念凸现自然场景,旨在发现人内在的肉身自然和外在的物质自然、人的肉体生命和生物界的终极相关性。在本源论的意义上,自然是与人类同在的在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是与人类共在的在者。人对自然的顺服,才能唤起自然中河流、山川、植物、动物对人的祝福。人的意识性,是他能够采取此种优先顺服态度的前提。不过,汉语思想似乎自古以来缺少对此的自觉。其天人合一的道统理念,不过是因为天人分隔的现实在观念中的臆想物,并不具有实践的可能性。戴光郁的另一件作品《搁置已久的水指标》,正是古代国人生存的天人分隔现实在当代的观念凸现。 总之,每件装置、行为作品,都关涉到媒材与观念两方面。两者同时又构成艺术作品的场景质素,需 要说明的是:场景的择取、隔置、还原、凸现,在艺术家挪用场景时和它的所指意义境域即历史、社会、心理、自然并非处于一种对应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意义境域里,场景挪用的方式也许多种共存。本文中概括出的标题,仅限于艺术家戴光郁的几件作品个案。它对当代艺术创作的普遍价值,或许在于进一步激发艺术爱者研究场景挪用的途径及相关意义。(本文以“场景:媒材与观念—关于戴光郁几件装置、行为的评论”为题,原载于《山花》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