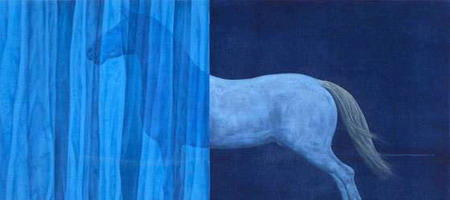一
20世纪的中国水墨画艺术是一段革故鼎新、大师迭出的创造历 程,与之同行的关于水墨画艺术的不间断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使 这一历程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艺术史和文化史现象。从20世纪初的康有为和后来的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 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人画的因循守旧发起猛烈抨击,倡导对中国传 统艺术进行彻底革命,主张“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康有为)[1] 开始,直到世纪末中国大陆的现代艺术运动“’85美术思潮”,引进 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大力促进传统水墨艺术的现代转型,这 一历程跌宕起伏,波诡云谲。围绕着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现代性” 和“民族性”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始终交织着关于传统与现代、民 族与世界、政治与艺术、现实与想象以及集体与个人、意义与趣味等 等关系问题的痛苦而深入的思考。这一历程的推进也始终伴随着其对自身的不断回眸,所有这些都体现了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 一种自觉精神。这一历程的每一个阶段性变化,全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这些阶段性变化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无疑是重要 的,应该说还是刻不容缓的美术史课题。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水墨史的研究与写作并未引起相应的、足够的重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是从“’85美术思潮”到21世 纪的开头几年)在不少人看来,“水墨”的问题太中国,不具“普适 性”;“水墨”无论是作为艺术方式还是作为艺术“媒材”都太古 老,与装置、影像、行为等新艺术方式相比太不具“当代性”。当然 最近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对水墨艺术的“当代性”问题有 了新的看法。但这主要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水墨艺术自身的发 展,与水墨方式向其他当代艺术方式的植入和渗透有关。但现代水墨 艺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仍然被排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领域之外。尽管批评家栗宪庭认为“水墨画是中国目前艺术界三足鼎立状态之一足”。(按栗的说法,其他两足一是写实主义油画,一是当代艺术。)[2]不过这似乎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现代水墨史研究与写作相对滞后的状态。栗的观点明显地将水墨画与当代艺术分开对待,这也代表 了不少批评家的看法。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将“水墨画”与当代艺术 “分而治之”的作法,导致了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史研究与写作 的相对滞后。如果我们不是完全套用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 叙事与修辞模式,而是着眼于20世纪中国文化总体上的现代转型,就 会很自然地发现中国当代艺术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文 化语境中生长出来的。就像西方当代艺术根源于其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文化逻辑和文化境遇一样,中国当代艺术也有其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文 化逻辑和文化境遇。这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提醒我们,从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由“中国画”而“水墨画”的概念演变,到新世纪继续发展为 由“水墨画”向“水墨艺术”推进的艺术史现象;以及与此同时出现 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与批评领域的“水墨性”、“水墨精神”、“水墨方式”等理论话语,乃是这一文化逻辑与文化境遇的独特表现。这 不仅说明现代水墨史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提示我们 对这一文化逻辑与文化境遇的揭示应该是现代水墨史写作的出发点, 这也同时决定了现代水墨史写作的方法论基础。
“出发点”的说法也许并不确切,此处套用GPS导航仪主菜单上的 图标“出发去”应该更为准确,因为艺术史的真正出发点只能是艺术 品、艺术家和艺术现象。但我们的艺术史研究经常是把出发点当成了目的地,局限于所谓“艺术本体”的历史学研究,常常忘记艺术史作 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它不仅仅只是帮助我们在历史的框架中去认识 和理解艺术,它的更远大的目标还应该是引导人们通过艺术史现象去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历史。因此对于现代水墨史的研究与写作,我更愿 意强调它的初衷应该是揭示20世纪中国文化总体上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文化逻辑。也正是这一写作目标,决定了现代水墨史研究必须有一个较为宽泛的 方法论基础,因为仅凭某种单一的风格学、美学或社会学方法,要想达至上述写作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不仅如此,基于此种目标,对于现代水墨的历史考察必然会涉及政治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心理的方 方面面,一部充实厚重的现代水墨史理应包容或折射出20世纪的社会 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心灵史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现代水墨史的写作还必须建立在多种学科资源的综合利用之上。
二
与传统的水墨画史建立在风格学与鉴赏学基础上的连续性的写作 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水墨史的写作必须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的 “非连续性”问题。如果说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杨之光、方增先、周昌谷、刘文西等为代表的新中国人物画,相对于明、清以降的中国画 传统,是非连续性的;则80年代随“’85美术新潮”出现的谷文达、王公懿、王川、沈勤等人的新水墨明显是一个断裂,而90年代石果、刘 子建、张羽、王天德、魏青吉等人的“实验水墨”几乎可以算得上是 “基因突变”了。是哪些、是什么样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导致了这些“非连续性”、“断裂”和“突变”现象的发生,现代水 墨史有责任作出回答。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我们不熟悉的现象是否可以 通过与传统的水墨画史中我们熟悉的现象的类比来转化为我们新的艺术史知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按照福柯的说法:对古典形式的历史学来说,非连续性既是给定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历史的原材料以决策、偶然事件、首创精神、发现等分散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分 析,这种材料不得不被安排、简化、消除以便揭示事件的连续性。非连续性是时间错位的烙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把它从历史中去掉。[3]而“在福柯认同的新型历史学中,非连续性,非但不是障碍,而是历史学家的实践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新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可能是这种非连续性的移位:它从障碍到工作本身的转移;它与历史学家的话语合为一体,在那里它不再起必须被减少的外部 条件的作用,而是起工作概念的作用;因此有符号的倒置,它借此不再是历史阅读的消极因素(它的阴暗面、它的错误、它的力量的限制),而是决定其对象并使分析有效的积极的因素。[4]
既然如此,就必须认真对待上述所有“非连续性”现象,将之作为自己工作的本身,作为与自己的写作话语合为一体的工作概念。必 须以极为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待构成这些非连续性现象的、以“决策、偶 然事件、首创精神、发现等分散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原材料”。现代水墨史研究与写作的第一步应该是将收集、甄别这些“历史 原材料”作为自己工作的头等大事。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道听途说,信手拈来。历史写作的局限性永远是无法逃避的,但还原历史真实、还原历史情境的不懈追求同样是历史书写者永远的天职。而历史书写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前提,也永远只能是建立在史料之准确与丰富的基础之上。以空洞的历史书写抢占学术高地,只能暴露我们自己的无知与 浅薄。无根游谈、兴到乱语从来止于智者。(近读王元化先生《九十年 代日记》有此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寅生谓寅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无可观,而独推荐其中某教授一篇论文。但我读后,觉得论文集中某 些文章提供材料颇多,反较某教授文章佳胜。”又说:“大陆学者强调观点乃四十年来宣扬‘以论带史’的后遗症。事实上,观点并不能代表学术的全部意义。有新颖观点的学术论文,也可能是内容空洞思想贫乏 的。”[5])对于现代水墨史,福柯所说的这些以“决策、偶然事件、首创精神、发现等分散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原材料”除了艺术 作品、展览活动及其相关评论,显然还应包括像策划方案、会议记录、艺术家手记、活动照片、海报、新闻报道等等历史文献。也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当我们在做“中国·水墨实验20年”、“实验水墨回顾”等带 有水墨史性质的展览,以及编撰《黑白史》、《九十年代中国实验水墨》等文献资料集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文献的精神给予了这些“历史原材料”以高度的重视。
三
艺术史写作首先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揭示、去蔽、匡 正、丰富是艺术史经常性的工作;如前所述,真实的“历史原材料” 是这一切工作的基础。但分散存在的“历史原材料”即使是真实的,也通常是沉默的。艺术史写作者只有在历史的框架之内认真研究艺术 作品和艺术现象,解决历史环境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问题,像能工 巧匠一样将这些分散存在的“历史原材料”合理地、妥贴地安排在一个特定的叙事结构中,材料才有可能自然地发出声音,从而最终形成 艺术史的价值判断。叙事结构因而成为现代水墨史研究的关键性学术 课题。我在为广东美术馆做“中国·水墨实验20年”展时,即有意将 其作为一个叙事结构来呈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水墨的发展脉络。该 展第一部分“水墨实验20年”由“新潮涌动”(80年代至’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张力表现”(1990年至1996年)、“实验走 势”(1996年以后)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编年史”式的展 示构成。有部分文献资料与作品同时展出,意在为艺术品提供有价值 的艺术史背景,为对作品的欣赏和解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线索。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一个历时性的结构,则由“想”(追忆、寻觅与梦想)、 “观”(心象与都市人文景观)和“思”(数码时代的神话与寓言) 三个单元组成的“水墨之光”部分便是一个开放的、前瞻的共时性结 构。作为上个世纪末中国画坛的现代性话语之一,实验性水墨贴切地 表达了当下的文化感受,成为蕴涵着中国当代社会心理结构和集休无意识层面丰富内容的“文本”,也成为20世纪末中国心灵史的一段索 引。它以前所未有的丰富性折射着当下中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 的巨大变迁,以及这些变迁所导致的个体心性层面上的深刻变化。事 实证明这样一个“叙事性”的展览结构,不仅清晰地呈现了新水墨相对自律的艺术史脉络,也为观众和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相应的理论阐释,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水墨,其价值诉求自然得以充分体现。 现代水墨史的方法论立场决定其历史叙事的框架结构,前述较为宽泛的方法论基础决定了现代水墨史叙事方式的多元性。但笔者以为,基于水墨艺术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当代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与地位,以文化转型为中心的叙事框架有理由成为现代水墨史核心的叙事方 式。这一叙事方式亦可借鉴福柯将结构主义的观点与非连续性概念合为 一体的做法,注重在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相对短暂的非连续性的断裂、突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国文化总体上的现代 转型正是在这种不间断的挑战、冲突、妥协、放弃、转化的相互作用中 一步步完成的。对于现代水墨史的研究与写作而言,由图像谱系和文献谱系构成的“历史原材料”中隐藏着所有这些相互作用的丰富细节。而 如何使这些细节显示、呈现是艺术史写作的有趣课题。自觉的问题意识 因此而成为水墨史写作有无价值意义的前提,因为如前所述,围绕着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现代性”和“民族性”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始终 交织着关于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政治与艺术、现实与想象以及集 体与个人、意义与趣味等等关系问题的痛苦而深入的思考。具体的每一时段、每一个艺术家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乃 是构成一部现代水墨史的基本元素。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将使现 代水墨史成为一部思考的艺术史。
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之光的水墨人物画创作为例,杨之光是新 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画家,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水墨人物画艺术实 践中,创作了如《一辈子第一回》、《雪夜送饭》、《浴日图》、《难忘的岁月》、《矿山新兵》、《激扬文字》等铭刻着时代生活鲜 明印记的水墨人物画作品。这些作品洋溢着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所 特有的忠诚情感和报效热诚,不仅在当时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情感,鼓舞了人们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在今天看来,它们所蕴涵的积极向上的 文化理想和超越物质主义的浪漫气质,也依然十分感人。重要的是,杨之光的这些作品,和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优秀的、有创造力的水墨人物画家创作的,以表现工农兵新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周昌谷的《两个羊羔》,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等一起,代表了20世纪中国水墨画艺术史上,一个有独特的 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并且是有十分独特艺术面貌的创作阶段。 这一阶段是徐悲鸿、蒋兆和借鉴西方写实绘画的造型手法,将光影、明暗、体积等等“语汇”引入水墨人物画的中西融合之路的延续和拓 展。也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美术界“改造中国画”[6]、提倡“写生”、“走上现实主义的大道”、描绘“中国人民在现实生活斗争中那些高 尚的和优美的心灵活动”的直接结果。[7]在这一段历史中政治与艺术 的关系便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而在另一方面,与“徐、蒋变革”的不 同之处在于,杨之光的新画法摆脱了素描加水墨的生硬作风,将西画 的写实主义造型观念与手法和传统水墨画的笔墨技巧很好地结合到了 一起。他在“打通”与“衔接”上下了大工夫,他的新写实风格的水墨人物画,对中国绘画“重意尚写”的精神传统心领神会、情有独 钟。应该说杨之光的这一融会贯通,是对徐、蒋开创的中西融合的水墨人物画法的一次有艺术史意义的推进。这一推进的艺术史意义正 在于对水墨性话语的不可言说性,也即水墨画的文化根性的寻觅与回 归。20世纪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水墨之争,从以金绍城、陈衡恪等为 代表的“传统派”对传统艺术满怀信心,对文人画的价值给予充分肯 定,反对标新立异和融会西法;到世纪之交的吴冠中与张仃的“笔墨 之辩”,几乎所有论争的核心实质,也都正在于担心这一水墨画的文 化根性的丢失。而在这里艺术史应该对艺术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 难抉择,以及在这一抉择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智慧与才能作具体而微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水墨画史既是一部中国传统绘画现代转型的历史, 也可以说是中国水墨画家向西方绘画学习和从西方绘画“拿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出一长串向西方绘画学习或自觉不自觉从西方“拿来”的著名的中国水墨画家的名字,徐悲鸿、蒋兆和自不待言,从张大千、刘海粟、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关山月到吴冠中、刘国松、谷文达、田黎明、刘庆和、武艺以及90年代的一批实验 水墨画家,哪一个没有受过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一学习和引进过程的 对象,几乎囊括了西方19世纪以来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 义的所有流派。在所有这些艺术史现象背后又隐藏着大量艺术家关于 民族与世界、现实与想象、集体与个人以及意义与趣味等等关系问题的思考,对这些内容的历史书写,将使现代水墨史有可能成为既往宏 大叙事历史的对立面,颠覆宏大叙事的话语权力。当然现代水墨史也 必须拒绝使自己变成新的独裁性的意识形态,因为尽管我们可以对历史作出无尽的推测,但必须提醒自己还原历史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必 须对所有的话语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
注释: [1]见康有为《万木草堂•画论》。
[2]见《净界》,广东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3]转引自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4]同上引,第153页、第154页。
[5]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2页、第226页。
[6]参见《中国•水墨实验20年》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年。
[7]见《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和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