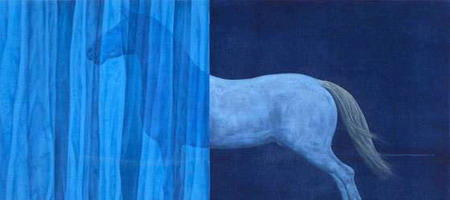郑宏彬:你怎么定义当代水墨?如今的当代水墨是否有其自身的边界?
何桂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批评界曾使用过多个与水墨相关的概念:现代水墨、实验水墨、表现水墨、都市水墨、观念水墨、抽象水墨等。由于立足点不同,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有较大的差异。譬如,“现代水墨”便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在面对传统水墨时,它主要体现为一种风格学上的意涵,特指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或水墨样式;在面对西方现代艺术时,它又具有了某种文化身份的指涉,即一种承载了东方精神和具有“中国样式”的水墨;在面对当代艺术时,它又可能成为一种时间上的概念,特指“八五新潮”这段时期,以形式先决和文化反叛为目的的水墨实验。因此,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因语境的不同,其内涵也在发生流变。我个人认为,当代水墨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便如此,它仍然有自身的边界,即指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不同于传统水墨的创作范式与品评标准,且具有现代风格和文化现代性诉求的水墨创作。
郑:当一名艺术家被纳入当代水墨领域进行讨论,有什么标准吗?
何:当然有标准,但这个标准也是相对的。比如这次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谷文达 ——“水墨炼金术”的展览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次到深圳来,我也是想进一步了解谷文达早期的水墨实验。以谷文达的作品为例,我们会发现,一个艺术家能否被纳入当代水墨领域实质还是有标准的。我个人认为,“标准”至少应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你是否创作过水墨类的作品。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第二个是,你的作品是否有内在的创作逻辑,而且,这个逻辑必须与水墨艺术有关,即需要与传统或当代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名艺术家,你是否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且你的代表作又能否在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如果前两个标准更多的是从艺术家个体创作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后一个标准主要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衡量的。从谷文达的创作历程上看,他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传统国画,但80年代中期却走向了反传统的道路。在他1985年创作的《乾坤浮沉》中,整件作品基本上是由泼、洗、冲的方法完成,同时,时空错置的空间意象,以及艺术家对图像的引入,让作品弥散出一种浓郁的超现实主义气息。对于谷文达而言,放弃用笔,等于就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入画标准和依存于笔墨之上的审美趣味,对于作品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在整个80年代中期的水墨实验中,谷文达对传统水墨的反叛都是最激进的,也是把这种反叛的文化态度保持得最为彻底的艺术家之一。如果从第一、第二个标准看,谷文达90年代中期以来的创作,尽管在形态方式上主要以装置为主,但其内在的创作脉络仍然是有联系的。之所以我们可以将谷文达看作是一个当代水墨的艺术家(当然,他的一些创作如《联合国》也并不局限在当代水墨领域),主要是他过去的一些创作已经在美术史上占有了自己的位置,比如,我们要讨论80年代的中国当代水墨实验,我们就无法绕开《乾坤浮沉》、《正反的字》等这一系列作品。这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就是我所认为的“标准”所在。
郑:在国际视野中,尤其是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的优劣应怎样评定?
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是西方人。不过,对于大多数的西方人来说,水墨艺术都会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但是,我想,他们是很难真正理解、认识我们的水墨艺术的,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都是如此,毕竟水墨艺术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仅仅从当代水墨的角度考虑,如果是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看来,一个当代水墨艺术家的作品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一是他的水墨作品是否有个人化的现代风格;二是要反映出艺术家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水墨的态度;第三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艺术家如何立足于传统的转化与创造,以及怎样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的。
郑:你认为当代水墨的发展状况基本上是先颠覆,后观念?
何:对当代水墨发展状况的讨论一定不能与其具体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脱离开。我大致将当代水墨的发展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三个十年,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水墨创作。当然,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绝对分裂的,它们之间仍有内在的联系。针对这三十年的发展状况,简要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水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一个艺术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学、文化学,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尤其是在80年代初反思文革、现代化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代水墨的起步与发展便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拨与疏离,对传统水墨的拒绝与解构,对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语言的接纳与吸收,而且,这些不同的文化诉求往往交织在一起,推动着当代水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进入90年代后,由于中国社会、文化情景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水墨由80年代的颠覆与反叛进入一种自觉的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状态。与此同时,一些具有西方观念艺术特质的水墨创作开始大量涌现。2000年以来,当代水墨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其中以李华生、谷文达、张羽、梁诠、魏青吉、阎秉会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不仅拓展了当代水墨的形态边界,而且将作品的创作与本土的文化传统、自身的艺术演进轨迹联系起来,突出创作方法论的意义。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当代水墨的发展强调对传统与既定创作规则的颠覆与反叛的话,那么,新世纪十年的当代水墨创作更应重视“重建”所体现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但包含了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积极回应,对现代性建设的不同发展路径的重新认识,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的挖掘,而且也在理论上体现为一种建立中国当代水墨价值尺度与批评话语的自觉。
郑:当代水墨自“建构”之后,如今的发展状态又是怎样的?有没有自身面临的问题或者危机?
何:2000年以来,当代水墨的发展基本延续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水墨的发展态势,格局也相对稳定,有表现性水墨(阎秉会、王川、李津、魏青吉等)、抽象水墨(张羽、胡又笨、张浩、刘子建等)、都市水墨(田黎明、李孝萱、刘庆和等),还有一些偏向观念表达的水墨(王天德、邱志杰、宋冬、朱金石等),这四大方向在90年代末期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格局。不过,在当下,当代水墨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抑或说是危机。一是来自于传统水墨的挑战。我们发现,虽然近些年批评界对当代水墨的讨论逐渐增多,但是,在整个中国水墨艺术的系统中,尤其是从市场份额的比例上看,当代水墨仍然是很边缘的。另一个是,当代水墨在展示形态和创作方式上仍然比较单一,会遭遇到其它当代艺术形态的冲击,如装置和新媒体艺术等。换句话说,当代水墨还需要更多元化,而艺术家也可以加大“跨界”尝试的力度。从近几年的创作上看,邱黯雄那种将水墨创作与影像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张羽那种融汇了装置、行为、观念的水墨实验都是比较成功的。第三,当代水墨界现在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今天活跃在当代水墨领域的主要还是90年代中期成名的那代艺术家,年轻艺术家的“缺席”肯定会影响到当代水墨在未来的推进。
(本文是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谷文达:水墨炼金术”展览的现场采访,成稿后,何桂彦对文本进行了调整。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