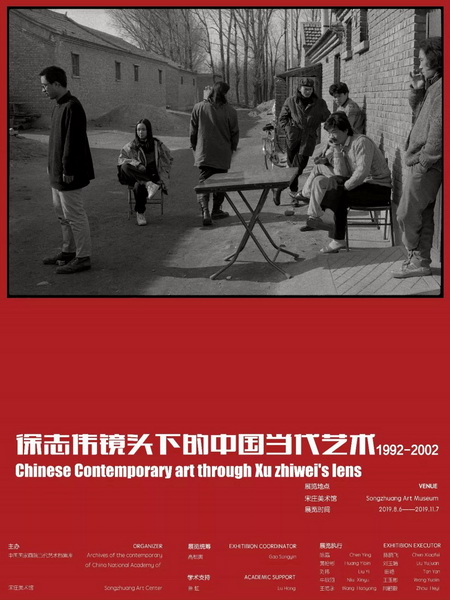1988年9月,在民间文化学术团体21世纪研究院(其前身被人为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主持与资助下,以艺术家温普林为编导、丁彬为制片人的一部名为《大地震》 的电视片开始投入拍摄。
温普林在他的 《世纪末的“巴洛克”—编导的废话》中说:“这是一部以画画人的眼睛看世界的电视片。从编导、制片、美术、摄影到大部分参与创作的人都是画画的出身。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件美术作品。”按照温普林的说法:“片中无褒无片貶只是表现,表现喘气和折腾、行动和不安。至于这一切究竟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与我毫不相干的。”在一篇原拟发表在《画家》杂志上的小文《关于〈大地震〉》里,温普林又说这部电视片“企图将现代艺术界的诸般境况,尤其是标榜为具有‘世纪末’精神的混蛋们一网打尽。”
由于经济及其他现实原因,这部电视片并未投入后期制作。摄制组的主要成员也于1989年6月的政治事件之后解散。然而,也许真正值得记录的历史并不是电视片本身,而是摄制组围绕拍片组织的一些活动。其中摄制组于1988年10月15日至16日在长城拍摄的告别20世纪艺术活动尤具象征意义。《中国美术报》1988年第52期记载了这次活动:一天一夜的长城狂欢,从青年人追随卡车上的摇滚乐队上长城开始,尔后用成千迟白布捆绑长城,接着是一系列行动艺术:从京剧演化出来的跳神舞;现代舞剧片断、独舞;捆扎、纹身的身体艺术;关于21世纪艺术的讲演;充满世纪末情调的戏剧场面;一部无人能解的“天书”;烽火台上滚滚的狼烟,最后是长城上的摇滚之夜,人们在演唱和狂舞中达到高潮,第二天清晨又回到古老而寂静的都市。
这场综合了戏曲、音乐、美术、讲演的戏剧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发泄性质,它与这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出现的种种行为活动形成了一种必然的呼应。其中具有受虐性的捆扎与纹身的表演再次重复了’85思潮以来的行为艺术。只是,当编导把这样行为艺术艺更大规模放在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 – 长城 – 时,行为艺术本身的社会性、批判性的特征就表现得更为充分。当然组织拍摄这次活动是具有自悦性的。然而这种自悦性使我们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氛围。这在其中的一首摇滚乐歌词中以文字的形式传达了出来:
鼻青脸肿两千年
踉踉跄跄万里路
从前现在后来
神话传说和典故
烽火箭垛123
青砖绿草345
将你全身都裹住
残破的四肢也会露出
裹住你的胳膊露出你的腿
裹住你的屁股露出你的嘴
裹不严、包不紧、绑不牢、绷不住
叮叮当当擂战鼓
踉踉跄跄走你的路
这种表现文化与精神溃烂的行为充分表示了这个时候的人们对急剧变化社会的不适应。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感觉世界的紊乱与动荡,还有精神秩序的解体。这样,艺术与文化就成了展示一部分颓废艺术家生活方式的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形式。把这些艺术家与19世纪末的欧洲艺术家进行联系是很可能说明问题的,可是,一种严重的区别是,中国的世纪末艺术家并不是逻辑地接近一个新的时代。且有秩序地推进一种文化进程,无论是物质与精神的资源,在这些艺术家来说都显得唐突和不自然。正如温普林在他的《编导的废话》中说的那样:“他们急不可待地要走向下一世纪,从内心到行为都充满了惶惑不安,而外表却是努力做出很是潇洒的模样。”《大地震》的拍摄是一次潇洒的活动,由于这种潇洒是“盲目”的,因而,那些保留下来的电视片素材带就成了记录虚无主义文化现象的文献。
温普林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毕业生。曾从事过油画拼贴的创作。只要我们对他的《自由像》和《三个小老虎》这类作品有一种感受力,就很能理解他以后跟进一步以“玩”的形心态从事的其他艺术活动了。无论是电视片、摄影还是其他活动,盲目的玩的心理状态是十分清楚的,至于艺术的“纯度与力度”或所谓的建构性,实际上是谈不上的。他的朋友丁彬说温普林的作品“极富幽默性”。其实,这种幽默是对难以承受的社会现实在心中造成的复杂心态的消解。
丁彬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他被认为是北京最早自费举办个人展的画家之一。他最初为北方交通大学教师,以后“落草为冠”。作为盲流艺术家,丁彬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同于温普林的。这位艺术家希望“养活”艺术,而不是“用它来养活我”,他指望着有人用感情去换取他的艺术,而不是金钱。可事实上,盲流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与活动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丁彬的命运。

早在1986年的冬天,盛奇、赵建海、奚建军等人就以在北大校园进行“观念21行为活动”活动而在北大乃至文化艺术领域里招致了批评。到1988年5月,盛奇、赵建海又和郑王珂、康木在古长城遗址完成名为“观念21 – 行动展观”的行为艺术。一般而言,他们的活动那个结果是臭名昭著的。由于这样的行为艺术所体现出的精神状态与温普林的感觉颇为合拍,所以在1988年10月,温普林约请盛奇等人在长城拍照。自然盛奇的国画作品远不如他与其它艺术家进行的“观念21—1行动展观”的活动更为充分体现它的精神状态。他在长城所进行的“太极”捆扎表演,将无可奈何和物力的挣扎心理展示得相当充分。他在一篇给《画家》的小文里谈到了“对未来世纪的畏惧”,并且“这种感觉渗透在每一个毛孔之中”。因而他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消解方式:
太极之奥妙,在于人与自然息息相关,象冰融化成水的过程,其实质原本是无差别的。为平衡而吸而呼、呼吸、呼吸、由短至长。由体会到感知,再由感知到无知,无知道无觉乃至之境界。
吸气 – 呼气 – 吸气,自自然然… …
其实,盛奇的“太极”表演并没有使自己回到自然状态。意志在此时起到了强迫性的自虐作用。
参与“观念21-1行为展观”的康木、郑玉珂这两位艺术家进行了捆绑与纹身的表演。由于“纹身”的艺术如此具有自虐性,因此表演更接近于受难。郑玉珂为《画家》杂志写的几句话,反映出了与大多数盲流艺术家相同的“盲目”的心理状态:
从现实的内疚,到内心的真实;从现实的真实,到内心的内疚。从客体,到主体,从人,到物;从天,到地;从山到水;从人间到地狱。从人到仙;从仙到人。
这样的心理状态是没法坦的上文化问题的。但是历史地看,这种精神的溃烂正是文化转变种的必然现象。
如果说盛奇和郑玉珂的行为艺术多少算是一度盛行于中国各地捆扎行为的重复的话,盲流艺术家王德仁的时间设计还能算是有些特点的边线。他在1989年2月的中国艺术展上抛撒避孕套的臭名昭著的行为,导致了非同寻常的新闻效应。艺术家自称早在1984年,他就开始构思一个叫作《最后的东方》时空艺术。这个攀登桑旦卡桑峰的行为活动使王德仁获得了从未有过体验。攀登的时间是1986年7月,与他同路 的有天津美院自费生巴特尔。王德仁与他的朋友是否攀上了6570米的高峰。他们是否遭遇到了如他所说的那样的险情,被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所怀疑。但无论如何,一次艰难的体验活动肯定会给他们以不同寻常的感受。1988年3月,王德仁在北京大学广场展示了他的《第3系列之一 – 大美术革命演习》。批评家陈卫和在她发表于《中国美术报》1988年第44期的《北京“盲流”艺术家印象》中饰这样表述王德仁的思路的:
以铺天横幅,书写标语和围观人群的无意识参与所引起的骚乱,达到再现他童年时所经历的文革场面的目的,他自述童年与少年时代因出身地主而背了15年“小地主”的绰号,他认为无意识参与者的表演行为又把他退回到童年时代,而他的目的在于证实“文革毒素还不自觉地残留在80年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这种对童年心债的偿还,竟是以导演“模拟戏”来实现的。
以后,王德仁又进行了种种行为活动。但均未给他带来“美女如云跪拜”、“记者之流蜂拥而上、闪光灯劈劈啪啪”(温普林)的结果,只是到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他抛撒避孕套时才达到了他渴望出名的目的。王德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抛撒避孕套的行为,在受到杜桑思想浸染的中国艺术界自然被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艺术行为”。这个似恶作剧的事件较之其他行为艺术,更不顾及一般伦理和道德,因为这位肇事者把无数赤裸裸的性象征物撒向观众,以强迫他们接受一种荒诞的事实。
其他盲流艺术家还有关伟、阿仙、林青岩、张大力等。这些艺术家在十年的现代艺术中虽然没有构成什么影响,但他们的行为与艺术自然属于这段历史的。即便我们在张大力这样的盲流艺术家那里感受到了令人同情的悲观主义(“人生本是虚无海面上的一虚舟,是茫然,是永恒的哑谜”(张大力)),也能在象阿仙、关伟这样的艺术家手下见到一些有特色的作品。阿仙最早画了一批油画,这批画反映出艺术家对墙与女人体的特殊偏爱。1988年以后,他在纸、布上进行了墨、丙烯与拼贴的试验。墙与女人体的重叠在材料与手段的辅助下,产生了一种都市的冷漠与伤害的效果。这种都市的感受在他的《环境工程.1990》这一装置艺术设置中,被加强了。有趣的是,伤害与相应得压抑感通过诙谐的设计得到了消解。
纯粹的和不纯粹的(那些有固定工作单位但因各种原因并未在固定单位工作的,如关伟,及因生活问题断断续续地放弃盲流生活的)盲流艺术家,远不止北京的范围。盲流艺术家这一概念已经超出了狭窄的地区而扩展到了对一种普遍现象的概括。当我们分析他们艺术的时候,正如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与环境的互不相同一样,他们通过艺术反映出来的精神形象也是因人而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