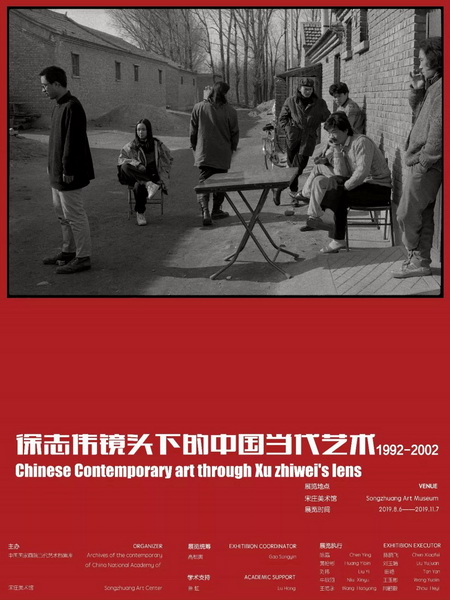(第五场)
时间:2010年1月23日
地点:东湖宾馆企辉厅
专题讨论
主持人:鲁虹
发言人:殷双喜(《美术研究》杂志主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冯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高岭(《批评家》杂志主编)
陈默(《大艺术》杂志主编)
鲁虹:下面请殷双喜先生、冯原先生、高岭先生、陈默先生上台来。上半场讨论时间超过了20分钟,我们就顺延20分钟。先请殷双喜先生发言,从80年代到90年代,殷双喜一直活跃在当代艺术界,他在各方面的著述颇多,现在是《美术研究》的主编、中央美院教授,也策划了很多重要的展览,请殷双喜先生发言。
殷双喜: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我觉得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是可能的,不仅因为已经出现了不少名为“当代艺术史”的著作,而且因为我们今天对艺术史的概念和写作的模式已经非常开阔了。如果按照经典艺术史的观点要求,我们可能会有很多限制,认为当代艺术史写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应该鼓励当代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我对这个持开放的态度。
第二,我本人觉得作为当代艺术的参与者、策划者,我们写当代艺术史要特别谨慎。昨天跟吕澎聊了这个问题,吕澎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进入50岁以后的人,逐渐参与当代艺术的策划和活动越来越少,很明显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会越来越多,用吕澎的话说,收拾收拾,差不多该回家了。吕澎本人就是这样,从一个翻译者到一个策划者,到一个读博的学者,现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记得,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开幕的当天我就坐火车回家了,高名潞说你为什么要走啊?马上开研讨会,正好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下。我说我们是在创造历史,历史的评价让后面的人来说。现在看来历史的写作权好像不能完全交出去,我们也有一份责任,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作为参与者、亲历者,了解许多历史的具体事实和现象,而这些艺术史现象隔了一代、两代人就越来越模糊了,会有人出于各种目的,有意无意地曲解历史。我们至少在历史资料学的层面上,有责任提供艺术史写作的第一手现场的东西。这是我为什么说“现场”,我们是现场的参与者和在场者,如果我们离场了或者不在了,别人就要花很多的劲去考证和猜测这批人的思想和他们的一些想法。我想这大概就是矛盾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参与要谨慎,但又不能随意地退出,这是我说的第二点。
今天上午对吕澎先生的著作讨论比较多,这个很自然。我觉得吕澎先生在当代艺术写作过程中是一个先行者,他有一种敏锐、勤奋,文笔和才思都很好。但我认为吕澎先生的写作并不是我们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完美和高峰,他提供了一个基础,使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变得具体化,可以有一个框架和对象进行讨论和批评了,我认为这是吕澎对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贡献。就像我们评论,没有作品是无法评论的,所以我觉得由吕澎的写作,希望我们能展开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和反省,包括分析吕澎在第三本书里面讨论他的艺术史观,就他的这篇论文,其实最早的那一本是高名潞等人写的《1985-1986中国当代美术史》,就是现代艺术展之后,马上就写了那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那本书的前言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我们现在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策展人、批评家,真正的艺术史学者关于历史大训练和艺术史的学科训练,我们是不够的,后来的学者、学生辈开始有这方面的训练,但他们对当代的参与和艺术审美的视觉方面的经验是不足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史学科还会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
我认为,艺术史写作是一个专业,是一个学科,它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门槛要求,要有一定的学术训练,尤其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关注和讨论。我们看贡布里希那个时代,那些学者之间的相互通信,非常亲切和尊敬对方,但是如果对方有了一个著作出来以后,那种批评是非常尖锐甚至是严厉的。巫鸿在美国写中国美术史,书出来以后美国的美术史学界就会对他的著作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讨论。这样通过批评推动学术发展,艺术史写作和研究本身也需要反省与批评,去推动艺术史的进步。
第三,我们现在一般注意大部头的通史,我建议我们要特别注意艺术史的论文。上午刘淳提到,许多20世纪现代美术的历史现象还处于朦胧,或者是逐渐隐入历史的浓雾之中,我们怎么样让它还原和清晰化,这有赖于扎实的论文研究。我在《美术研究》工作,我更看重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在西方学术体系里面,学术论文的价值高于一般教科书的价值。我们在这方面要培养出更多的对艺术史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进行研究的学者,推动具体的个案研究,在具体研究当中推动方法论和艺术史观的发展,当代艺术史的通史写作要建立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就说这么几点,谢谢大家。
鲁虹:对于殷双喜先生的发言有没有提问的?
好,暂时没有提问,那我们等下一轮发言结束再提问。现在请冯原先生发言,冯原先生是中山大学教授,他以前是艺术家,现在从事理论研究,对建筑、艺术、大文化都有研究,也有很多优秀的论文发表,下面请冯原先生发言。
冯原:讨论艺术史的书写问题,我不能算是个内行,但是在这次研讨会上面,我已经听了不少与会专家的发言,这些发言促成我自己的一些即兴的看法,所以,我打算撇开原来提交的论文思路,来谈谈历史书写的问题,当然,想法虽然有些即兴,但仍然没有脱离来原来的思考框架的。
我想寻找一条简单的路径来切入问题,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虽然是“书写历史”,但这个大问题应该分成两个问题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如何书写历史;第二个层面是如何成为历史。这两个层面分别涉及不同的主体人群。就艺术史写作的领域来说,它涉及到所有那些书书写历史的人,就像眼下正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是书写历史这个领域的人。不过,书写历史,必然会涉及到另外一部分人,那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层面——那些不书写历史,而是创造历史现象的艺术家们,他们是成为或即将要成为那个被书写的历史的主体。所以,只有把这两个层面合在一起来看,历史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说,书写历史的主体和成为历史的主体是两种不同却分工合作的创造历史的力量。
以刚才这个框架为基础,我认为可以从中衍生出三种不同的艺术史的书写方式。下面我简单来谈谈这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艺术史的传统书写方式,这正如刚才朱青生老师已经提到的现象,正常的历史书写是隔一代以后再写历史,或如同彭德老师所说的,本朝写上一朝的历史,这种隔代写作原则应该是艺术史的传统书写方式,对此我给出一个比喻,我把这种方式称为“历史矿场”类型,由此也衍生出“书写者—矿老板”这种角色。
为什么这样比喻呢?因为隔代书写原则的前提是时间,而时间正是历史的一个本质特征。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隔代书写方式所面对的历史对象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对象,或者说,只有当对象变成了史料,这就像地面上的植物必须埋入地下变成矿藏,这样一来,历史书写者就像是个挖矿者,历史书写等同于把埋入地下的史料挖出来重见天日,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出土的矿石——历史不能是新鲜的,它必须化为矿石以后才能作为写作对象。所以说,所谓的传统写作方式,意味着历史写作者要像一个挖矿的探矿者一样,把历史从地表下面挖出来,这个东西可能是矿石,可能是宝石,可能是煤矿,所以我说一个职业书写者无异于一个历史“矿老板”。
从生产关系上来说,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分为过去和现在两种,历史书写的旧有生产关系是“国家专卖”,因为历史矿石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因此,它也如同烟草这种大宗税源一样被官方所垄断,意识形态专控的历史领域一直在按照官方的标准生产出历史产品。然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虽然非常强大,但就艺术史的书写而言,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松动,并向民间出让了相当的空间。在这种时期,非专控的历史书写便发展出了一种属于自身的“书写自律”。艺术史领域的相对独立导致了历史书写者的分化,当历史书写者不再受迫于官方的书写方式时,写作者很可能基于各种自律或它律的目标来创造产品,因此,历史书写者会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角色,某些人可能出于赢利的目标过度挖掘或收购历史矿石,这样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历史书写的“矿老板”;某些人则有可能坚持某种自律性的标准,严肃的历史书写者无异于一个“艺术地质学家”,他们对艺术史的地质学做出贡献。
传统的历史书写传统方式,如果要用用食物的关键词来做比喻的话,其目标是要保存现象,手法是将对象进行“腌制”或者“风干”,这种手法所对应的产品应该是适宜贮藏的“腊肉型”,如果用茶来比喻,它所对应的应该是越老越好的普洱茶。总之,简单来说,老的就是好的这么一种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的一整套判断标准和逻辑体系。
除了刚才说的传统历史书写,今天已经衍生出了第二种书写方式,这种方式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当代艺术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才从中衍生出第二种历史书写方式。
与刚才我说的第一种以地质时间作为主要的时间对象的方式不同,我把当代艺术范畴中的历史书写方式比喻为“农耕节气”类型。其中衍生出两种人,第一种人即是“种植者—艺术家”,第二种人即是负责生产历史产品的历史书写者,在这种方式中,历史书写者转成了“计量者”。与传统历史书写所对应的地质时间形成对照,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所对应的时间类型是“农耕节气”,因此,它所对应的写作对象就不再是埋藏在地下的矿石,而是生长于地表面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由此构成了它的生产循环:艺术家如同种植者,种下了春天播种秋天就能收获的一年生植物,然后期待着每年的收成。所以,今天的艺术家不断地去创造那些所谓的历史事件,或者说,去播下那些历史的种子,然后就把收获交给了第二种人,即刚才说的“历史书写—计量者”。当历史书写者把每一年度发生的事件记录到历史中去,这就像青苗长成了稻穗,说到底,艺术不再具有事件的独立价值,艺术只是种子,只有当艺术事件被计量者记录到历史之中,这样的艺术事件才能转换为成果,才具备价值。
“农耕节气”的历史书写类型,由于其每年的播种、种植、收获、计量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租金”是它的生产关系的核心,我认为,去生产出历史的租金,是这种历史书写方式中的核心要害。租金产生于两种人,即艺术家和历史书写者的交易过程中,这两种人既像是农民和农科所技术员的分工合作;又像是生产者和收租者。历史书写者通过书写的选择可以从中挤压出历史的租金,而这个租金的多少就构成了反过来质疑历史正当性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今天,针对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的各种问题,其核心就是对租金的审核和侦查,或者说,是对种植者和计量者之间所产生的“历史租金”的质疑。事实上,租金并非全是不当的,它也是不可避免,因为,只要在“农耕节气”的生产类型中,只要按照种植和计量的生产书写逻辑去做,就必定会产生出“即时兑现”的租金的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去说,既然历史租金的生产和收取已经取代了生产艺术事件的重要程度,成为决定当代艺术史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方式比喻为一个“历史的收租院”。
与“历史矿场”完全不同,“历史收租院”处理现象的技术特征不是“贮藏”而是“保鲜”,它所对应的食物是难以保存的并以新鲜为标准 “海鲜”,它所对应的茶是新才是好的乌龙茶。总之,新的就是好的价值取向构成了第二种书写方式的判断标准和逻辑体系。
如果仅有以上的两种历史书写方式,那么历史书写仍然是好把握的事情。但是,历史书写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即使今天的会议也让我们察觉到,一定出现了、并存在第三种书写方式,我把这种书写方式称之为艺术史的“化学生产”类型。这种类型彻度摆脱了刚才所说的两种类型,无论是传统的“历史矿场”还是农耕类型的“种植与计量”的概念。
什么叫艺术史的化学生产呢?这就是说,当历史书写者已经获得了更大权力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趋向于去改变现象或事物的品质,以食物为比喻,这种历史书写者不是把新鲜的腌制成易贮藏的,而是反过来把应该腌制或已经风干的改造成新鲜的,它联系到一种化学生产方式,因此,就像今天用化学物品合成任何东西,或者,就像使用各种添加剂或兴奋剂一样,由此而生产出的产品可以称为“合成的历史”。“化学生产”类型所衍生出的生产关系,用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来说,就像是“吸毒者”和“制毒者”。以化学生产对感觉系统的支配而言,艺术家就如同渴望用化学历史产品来自我满足的“吸毒成瘾者”,而掌握了历史书写权的写作者则跃升为生产化学产品的“制毒者”。这种生产方式不再依据对象自身的条件,而可能根据书写者掌控的合成能力,把对像改造成需要的,或把需要赋予给对像。因此,根据需要和条件,化学合成的书写方式可以把新变成旧的,也可以反过来把把旧变成新。它的核心价值观是刺激就是好的。它完全超越了新和旧的问题,因此,刺激强度的问题构成了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的判断标准和逻辑体系。
由于有了第三种历史书写方式,它也就改写了前述的两种方式。比如,无论是传统的从时间矿场中挖取历史矿石的类型,还是从一年生植物收获中抽取历史租金的类型,都依赖于客观世界的定律,但是第三种历史书写方式,可以创造出不依赖于时间作用的矿藏,我把这种方式称为“人工造矿”或者“人工制矿”。当下对化学物品的滥用,化学品渗透进农业和食物生产中的严重程度已经是我们大家很熟悉也很警惕的内容,比如说,如何使用催肥的手段生产猪肉、如何用漂白的手段生产副食品,如何用避孕药来增加鱼类的产量,与这些比较普通的化学手段相比,更高一级的化学手段就只能是人工合成的毒品——冰毒或者摇头丸。可以说,合成毒品就是以人工制造的兴奋剂控制情绪系统的最高层次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说完了三种历史书写方式,我不得不去说说,这些方式是怎么演化,或者说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其实,历史书写,或书写历史的最终产品是创造名声。三种历史书写方式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传播条件和艺术生产关系中派生出的产物。历史之所以可以稳坐在象征产品金字塔的顶峰,那是因为最前面我说到的历史主体,那些不书写,但创造历史原材料的艺术家们,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历史就等于是获得一种终极的名声产品。当然,它也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名声的致幻剂。
关于名声与幻觉的问题,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记得2006年在北京开一个规模不大的批评家研讨会,就在会议现场,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跟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同志发生了语言冲突,以至艾艺术家要想显示肢体的力量。虽然现场的冲突很短暂,也安然收场,然而在现场目击的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温和的学术场变成了流氓的斗殴场?我认为,本质的推动力还是在于名声与历史,以及对这种名声的自我和他者判断。由此我推导出一个概念——“伟人幻觉”。今天来说,我觉得“伟人幻觉”也可以被历史化地分成三条路径来做出判断,联系到第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这种方式的终极产品是创造大师,所以,传统的“伟人幻觉”就是“大师幻觉”,许多的老一辈的艺术家,毕其一生的最大愿望,无非是想成为永垂不朽的大师。
而今天是一个大师正在消亡的时代,新一辈人已不再持有老一辈人的“大师幻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伟人幻觉消失不见了。今天这个会议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它证明了谁在今天掌握了操控伟人幻觉的能力,那很可能就是这些书写历史的人。毕竟,艺术家创造的原材料再多,谁能进入历史或谁才是历史的对象,还得靠书写者来选择和决定,当书写能带来越来越大的力量和利益之时,天平就会倾向于书写者这一极。于是我们就不难观察到,今天的历史书写者手中掌握了什么样的权力,由此来推断,伟人幻觉的当代形态应该是由过去的大师幻觉转换成了今天的书写幻觉,因此在情理之中,历史书写者群体中最自信和最有能力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伟人幻觉的代表人物。原因很好理解,因为谁能书写历史,谁就能掌握历史,那种掌握历史,改造历史,创造历史的幻象,导致了历史书写者自身的伟人幻觉。
从“大师幻觉”到“书写幻觉”,是否还是有一种伟人幻觉和第三条路呢?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把这种幻觉完全看成是贬意的。从艺术史的形成过程来看,伟人幻觉也许是推动艺术发展的终极力量之一。所以,最后我想说,伟人幻觉也许能转化成积极的东西出来。这是我从杨小彦的谈话中得到的启发。2006那个批评会冲突,小彦也在现场,我们都同样对致幻剂一样的名声效应感到失望和憎恨,我甚至说,当下的艺术生产,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名声摇头丸和先锋福利院。著名艺术家仿佛摇头丸的成瘾者,所以,也可以把这些人送进以先锋派命名的福利院里面去了。但是,几年过去了,名声摇头丸又放倒了多少艺术家不得而知,先锋福利院也许仍在扩大之中,但是,针对最近艾艺术家的行动和作为,小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我并不太清楚艾的所作所为,但从小彦高度地赞扬了艾未未今天的艺术行为和艺术计划来看,起码这种情况告诉我,伟人幻觉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它也有可能是积极的,而如果没有一种伟人幻觉的动力,历史领域和历史书写者的工作也很可能是乏味的。所以,我只是模糊地预感到,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艾未未的当下作为就代表了一种伟人幻觉的第三条道路,或者说,它可能预示了传统的“大师幻觉”和现在的历史“书写幻觉”之外的另一种积极因素?不管怎么说,起码我希望这是真的,如果这条道路真的能通向未来,无论对历史书写者的共同体,还是对创造历史的艺术家共同体来说,都应该值得期待。
鲁虹:接下来请高岭先生发言,高岭是80年代末出现的年轻批评家,一直活跃在一线,早期的行为主义的关注报告就是他写的,他策划了一些优秀的展览,也写了一些优秀的论文。现在我们请高岭先生发言。
高岭:谢谢主持人。我写的文章不想照本宣科,我想接着上午和刚才下午大家的讨论,发表一下自己的感受。我的发言从朱青生先生刚才的观点开始。他主张用历史的态度研究当代的艺术实践,因为他强调作为书写历史的人会有话语权力,今天写当代艺术史能形成权力,对于年轻的后学者来说,觉得写当代艺术的人可能会有权力膨胀。朱青生先生强调当代艺术本身的反历史性,从属性来说,从它的归属来说是反历史的信念。朱青生用了解放、自由这些关键词,我觉得非常好。我联想到了去年吕澎和王林的争论,这两位都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对这两个人的争论我一直没有用白纸黑字表达我的看法。这个争论的现实和历史背景以及学术环境其实是很繁杂的,因为我们都是当事人,又是批评家,又是推动者,同时还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看我们正在从事的事情。但是又造成两种东西,就是两种倾向性。一种像王林,他更倾向于是一种价值判断,我认为他和朱青生有共同的地方,王林强调的是解放、自由,这是王林一直在推崇的东西,就是反历史性。当代艺术本身的属性在当前的情况下不应该被当成历史来书写,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史料,或者质料、对象来书写。
吕澎则偏向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词,是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变化进行分析和研究时,讲到了这两个词。吕澎认为对当代艺术的看法仅仅在谈价值、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就是自由、解放、信仰这些东西,或者是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动力、信仰、解放、自由必须落地,必须落到制度化的层面。制度化的层面在物质化和商业化的90年代以来的社会里面,必须通过市场的机制、制度使它落地。而事实上更大的一个潜在台词就是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当代艺术院,比如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来说,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恰恰就是应和了落地,而且落地以后变成制度化、体制化、学术化、官方化的现实。
我觉得今天来看待最近30年的历史,我认为其实这两种倚重、侧重都是合理的,合理以后如何研究呢?应该是从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我赞成用历史的态度。实际上今天吕澎的研究,我们从当事人来说,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态度来做的一种对现代发生着的艺术实践的研究,只有到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N代人以后,对我们的文本,包括吕澎的文本,包括诸位艺术批评的文本,包括朱青生先生的文献档案,才可能逐渐形成一种比较客体化、比较对象化的历史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争论,他们的研究都有倚重,表明的是两种取向,这两种取向都是合理的,我就讲这么多。
鲁虹:谢谢高岭先生,下面我们请陈默先生进行最后的发言。陈默先生一直活跃在成都地区,成都大量的行为术都是他操办的,下面我们请陈默发言。
陈默:谢谢主持人鲁虹。他提到了我们这个讨论单元的相关主题: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批评以及当代艺术史的关系——这也几乎是艺术的当代进行时中诸多问题的集中所在。而在这些问题中,我想着重谈谈有关行为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问题。众所周知,行为艺术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留下了数量丰富的可用于写作的资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的很多当代学术活动以及艺术史写作中,一方面行为艺术可能是被涉及得最少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是我们诸多学术问题中敏感性、争议性、学术性很突出的领域。我在西南地区的艺术批评、策展及写作工作中,很多都与行为艺术相关。我亲历了许多活动现场,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那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09年底,各种群展、个展活动持续不断(我个人编写有《成都新视觉艺术大事记:1989-2009》,均有详细记录。)。去年年底,在成都龙泉驿洛带古镇的粮仓艺术区还召开了首届中国行为艺术年会,成为本土行为艺术发展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我今天的发言,肯定不会完全按照已出版的本次论坛文集中我的文章内容进行。当然,所涉及的问题与已发表的文章有很多连带关系,同时受今天现场会议的气氛的良性刺激,发言内容将会有所扩展。我的发言,是想谈谈被大多数史学家、批评家轻视或回避的本土行为艺术史的研究、写作问题。
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我做了一点发言准备工作,通过短信对相关作者进行了解、核实这几年有关行为艺术的著述情况。经初查,我这里列出四个版本的和行为艺术有关的写作情况。按照时间顺序。第一本是2000年温普林的《中国行动》,那是一本书加一张光盘的方式。这本书介绍、研究的是1989-1999年的中国行为艺术的基本状况。温普林的身份较为复杂,既是批评家、策展人,也是社会活动家,现在还可以加上慈善家和宗教研究学者头衔。这本书虽然有局限性,但仍然是当时较为权威的行为艺术史写作的范例。
第二本书是2002年高氏兄弟编著的《中国前卫艺术状况》。他们两位以艺术家的身份进行写作、编撰,根据艺术家之间互相提供的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劳苦功高。那本书我仔细阅读过,由于当时资料的有限性,以及作者身份的局限性,做出来的书不可能很全面,也难以涵盖当时中国行为艺术的准确学术面貌。
第三本书是2003年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这本书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它带有很强的官方体制色彩,有着十分明显的政治动机,却打着“学术”的幌子对行为艺术进行恶意攻击,甚至包括很多人身攻击,已经丧失了做学问的基本人格。在座的也有做出版或懂出版的老师们,凡是看过这本书的,相信都绝不会认同那种满篇都是的对作者名字用李××、王××,作品名称也敢断章取义,用《××××》表示的极为罕见的侵权做法。在他看来所谓“不雅”图片,公然敢用马赛克方式去遮蔽涂改,这些都严重违反了《著作权法》,是可以到法庭上清算问责的,可惜该书涉及到的大量作者维权意识不强。这本书虽然也在“写作”行为艺术,但因为其不良的人格和企图,已经彻底葬送了它的学术价值,成为艺术史写作的反面证物。
第四本书是2006年孙振华、鲁虹编著的《中国行为艺术》。该书是两位批评家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在所获得的有限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展开学科研究,将此前已见出版的对行为艺术的探索,推向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同时也表明了在专业学术领域,对该学科的认真务实的写作态度。
我说的这四本书,仅以我个人的初查情况而论,应该不是有关中国行为艺术研究的所有著述。因为对这几本书接触比较多,它们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相关问题,故在此提名。在这之外,像王林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包括高岭、吴鸿、冯博一、巫鸿、鲁虹、孙振华等都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我之所以提出这四本书的个案,是想以他们的写作为引子,探讨在该学科写作研究的多种可能性。通过比较,也的确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向鲁虹请教关于《中国行为艺术》这本书的疑问,所写是不是中国行为艺术的全部历史?他说不是。写作资料来源于艺术家、批评家、学者,受当时种种因素制约,难免没有遗漏。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做的研究,可能是片断式的或节点式的,受制于资料的因素较多。目前朱青生在北大做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系列,其资料库体系在逐步丰富完善之中。有了资料库做后盾,今后再做这个领域研究写作时,相信会大大增加学术的丰富性。当然,陈履生的问题已经不值一谈,应该说他把自己的学术资格删除了。而温普林的那本书是关于1989-1999年这10年的本土行为艺术研究专著,不足在于,一是受时间段局限,整体性受影响;二是对象选择性偏强,广泛性稍弱。当然,该书的重心在对行为艺术名家,如张桓、马六明、赵半狄、宋冬、苍鑫等的研究,其价值仍被看好。
下面我想谈谈行为艺术的批评和写作的缺席问题。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倍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热闹闹的行为艺术活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几年,被批评家、艺术家、学者们逐渐冷落?虽然在这个领域清贫寂寞,但仍有不少艺术家在努力坚持,令人敬佩。客观地说,学者们对他们的跟踪和研究的力度是不够的,甚至是缺席的。我提出“个中原因的追问”,是想做善意提醒,希望引起学界关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这个艺术门类曾经被叫做实验艺术,又有新视觉、新艺术、先锋、前卫、行为、现场等等名称,到目前比较集中于“行为”和“现场”这两种名称。由于其进入本土至今就是“非主流”的,所以一直被官方压制、舆论控制、活动限制就不奇怪了。因为这种艺术方式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和公共现场性,涉及到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以及一些意识形态政治敏感问题的触及,故而长期以来受到来自各方的有形和无形的压制,是有着上下文关系的。因此也不难看到,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媒体坚持一种长期误导,把行为艺术等同于人体彩绘、街头疯子、异类对待,使得大众对该艺术的认知仍存在严重偏差。到目前为止,行为艺术的传播仍然是在狭小范围进行,非常“小众”,甚至包括很多艺术家都不接受或排斥。仅只在小圈子范围自己研究,互相安慰,状态低迷。
2、这种艺术方式受材料、现场、记录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作品呈现的特殊性,使其市场属性大打折扣。由于不能形成良性的市场买卖关系,大部分艺术家为做一件作品捉襟见肘,甚至贫穷挨饿,到了必须有人赞助才能做下去的地步。在这种艰难处境中,艺术理想常常难以为继。相应地,我们的研究、写作工作也同步与此疏离,使得这一艺术领域的发展前景尴尬,方向不明。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比如基金会等模式,对行为(现场)艺术进行资金项目扶助,促进其健康有序的发展,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
3、长期受意识形态化的媒体传播误导,基本阻断了公众对行为艺术背景知识的了解通道,从而形成大众化的集体无意识排斥,所以“看不懂”、“伪艺术”的质疑不绝于耳,几成常态。就目前我们的大众审美情趣而言,基本上还倾向或类似于“文革”的宣传模式、批判模式、教育模式,所谓“懂”与“不懂”,还是以“似”与“不似”作为判断依据,新艺术的观念、表现、阅读等知识背景的补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段时间我在艺术国际网彭德老师的博客中看到一篇文章,谈艺术研究院的“院士”话题,说到多年前曾在国内比较活跃的“过气”理论家钱海源,最近在西安美院做讲座,以一种非常落后、反动的学术立场误导学生,非但没有人反对,还引起了学生的喝彩欢呼。可见我们学生的知识结构还是有问题的,艺术人格的塑造也有许多欠缺,不然何以做出如此荒唐的判断?彭德老师觉得非常悲哀,他说他在西安美院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当代艺术知识培育,最后钱海源来了一通“文革”式说教煽动,学生们的一声欢呼就把“武功”废了。
以上是我简单整理的本土行为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写作方面的种种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原因,希望能对同行们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最后想谈一点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应该排除一些前嫌,对这个领域的写作研究多一些关注和投入参与。因为,正在不断发生的当代艺术和围绕它进行的艺术史研究写作,一旦少了行为艺术,它应该是残缺的、不完整的,也是不严肃的。谢谢。
鲁虹:谢谢陈默先生,我们干脆把讨论放在下面一起进行好了。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行为艺术并不是我和孙振华关注与研究的对象,本来行为一书是由高岭写的,他拖着不交,而我们两个交稿很守时,所以湖南社改约我们写,我们是硬着头皮写的,由于前期的行为艺术基本上是属于地下艺术,刊物上资料很少,尽管我们想尽了办法搜了一些资料,但肯定是不全面的。因此,这个事还应该由高岭和陈默来做,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现在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