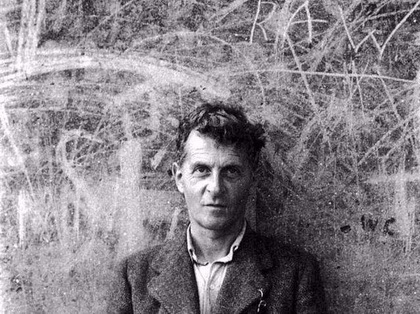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 约翰·塞蒙斯,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图片来自University of Kansas)
采访+撰文/龙星如(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员)
约翰·塞蒙斯(John Symons)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复杂性科学博士项目导师及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科技哲学史学会成员,他的研究和写作方向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逻辑学,尤其聚焦于计算机科学哲学领域。
2019年10月,塞蒙斯受邀在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发表系列讲演,主题包括“物理世界的运算”(Computation in the Physical World)、“用身体运算”(Computing with Bodies)、“运算理论在心灵哲学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Theory of Computation in Philosophy of Mind)、“自然信息运算”(Computing with Natural Information)和“极简认知的涌现:模态与心灵”(The Emergence of Minimal Cognition: Modality and Mind)——这些恰是当下计算机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恰好与笔者作为科技艺术策展人的研究方向有所交叉。近日,笔者通过视频连线采访了塞蒙斯,和他就“后人类”(Posthuman)概念、计算机科学哲学等话题展开讨论。
今天,“后人类”的说法已经很普遍了,但对“后人类”概念的诠释仍有不同版本。福柯、裘剑一(James Hughes)、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 等来自不同学术脉络的学者的观点,都曾在不同语境下被援引进关于“后人类”的论述里。在您看来,组成“后人类”概念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塞蒙斯:“后人类”,如其字面所示,意为“人类之后”。我们对“后人类”的思考,实际上是关于“我们之后的存在”的想象,但在讨论“后人类”之前,我们或许应该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对“人类”(the Human)的理解。20世纪中期,哲学领域对“人类”概念大致有两种宽泛解释,分别来自法国和英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系哲学的代表,包括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和福柯,集中对盛行于19世纪的人本主义者所持的“人,而非神,才是价值核心”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科耶夫、福柯和其他法国“后人类主义者”认为,人并不是上帝的替代。而在这群人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福柯。对福柯来说,“人”已经终结。法国的后人类思潮实际上来自对神学或神学所定义的“真实”,以及对围绕特定“中心价值”展开的理性秩序的批判——而在这些学者眼里,它们都是幻景。自启蒙运动以降,欧陆思想界一度认为秩序和价值来自“人类”,而福柯的批判也恰恰源自于此,他认为我们 应当批判“人类”概念本身。在整个法国哲学的线索里,对“人类”的思考很复杂,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法] 米歇尔·福柯/著
莫伟民 /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1-12
相比法系一派,英美语境下的“后人类”与科技发展的联系更为紧密,尤其是科技辅助人类身体演化 的可能性及计算机让人类成为非具身化存在、从有限的生命长度中解脱出来等潜能上。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想法曾一度蔓延于20世纪的美国,那时人们认为可以通过精巧的科技发明来解决所有问题。另一条支线则是,一些哲学家痴迷于“赛博格”[1]的概念,这个概念既蕴含政治色彩,也包含了自我创生和自体解放的意义。在“赛博格”状态下,人们可自肉身存在“升华”至一种新的生命状态。以哈拉维为代表的学者群体认为,“后人类”的核心就是“赛博格”带来的自我创造与解放。
你会发现,美国语境中的学者(包括哈拉维)是接触过法国思想体系的,但并没有对其全盘吸纳。他们认同法系学派对人本主义的批判,但并没采用福柯反进步主义的政治暗喻。与此相反,美国学派更倾向于持有革新式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对“解放”的乐观态度,这也包括对女性和少数族裔处境的改善。但对福柯来说,“人类解放”和正义的概念也是幻景。哈拉维对福柯观点的(部分)采纳,体现在她把对“人类”的批判延伸为对男性中心主义或族长中心主义的批判,所以她的视角像是“消化了一半”的法国后人类主义,同时糅合了某种技术乌托邦色彩和对政治的诗性想象,并不是那么自洽的,但很可能她本就不想自洽。
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有关“后人类”的思想,我们姑且称之为“硅谷后人类主义”。它更像是在流行文化里存在的对技术发展的乌托邦想象,有时也被称为“书呆子的狂喜”(rapture of the nerds)。这一类思考通常带有关于“人的彻底数字化”的想象,包括人是否可以被转换成信息、上传到电脑,以及所谓的“奇点临近”[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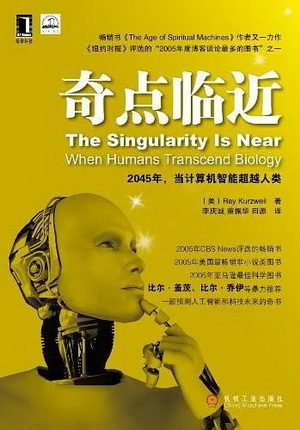
奇点临近: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
雷·库兹韦尔/著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0
您自己是如何理解“后人类”的?
塞蒙斯:我觉得“后人类”像一种“哲学寓言”。现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和卢梭,会讨论“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即一种想象中的时空所在。对于他们来说,对“自然状态”的想象恰恰是对所处时代的公民和主权状态的思考,是一种颇有建设性的哲学寓言。我想,不管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都不会真心相信“自然状态”真的存在(过),他们只是透过它来理解现实。我们对“后人类”的想象也与此类似。
但在我的理解里,不论是“自然状态”还是作为哲学寓言的“后人类”,都并非被完全外部化的思考对象,它还是会和当下具体状态产生种种牵连和交织,换言之,我们是半置身于其中的。
塞蒙斯:你说的对,这两者是相互交织的。这些哲学寓言会帮助我们组织起当下状况的方方面面,而我们也会论究我们所投射或想象的未来与当下之间存在何种纠缠和协商。对于这些哲学寓言的态度也不完全是一边倒的,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比方说,霍布斯可能认为“自然状态”是“粗鄙而短暂的”,卢梭则将它视作我们天性里一种理想且和谐的存在。而我们在哲学寓言蕴含的各个方面之间的迂回,也会帮助我们决定今日的投入,比如,我们需要关注什么?我们想要把什么带往未来?就像在“后人类”的语境里,有人可能更喜欢带有硅谷色彩的“后人类天堂”,也有人认为它是末日。所有哲学寓言的内在都交织着错综复杂的视角和疑惑。如果你对奇点深信不疑,那它或许就是你当下最重要的工作——将奇点带到人间,它或许就能成为我们文明的最终诉求。当然,我认为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寓言。我们只是在这些哲学寓言里选择了自己倾向的部分,并将之引入我们当下的政治和道德语境里,向前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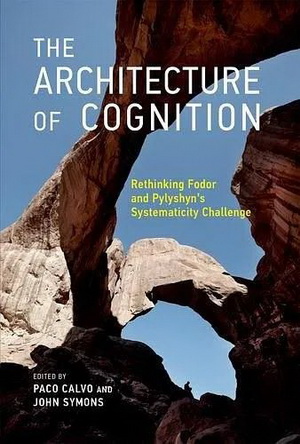
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
Rethinking Fodor and Pylyshyn's Systematicity Challenge
Eds. Paco Calvo & John Symons
The MIT Press,2014-04
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似乎还是以基准(benchmark)和解决方案(solution)驱动的,同时也存在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的追问。比如,计算机科学家凯特·克劳福德(Katett Crawford)近期的ImageNet Roulette项目就将目光投向ImageNet[3]中的“人”这个饱受争议的分类, 并尝试指出其中的缺漏。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思考人工智能领域里最紧迫的课题?
塞蒙斯: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时,它的意义其实很复杂。在今天的语境下,多数人将“人工智能”等同于“机器学习”(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机器学习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向而已。人工智能领域经历过好几次浪潮,它的发展和硬件的提升息息相关。而如今机器学习的发展势头也离不开GPU(显卡)的运算能力。但我相信这一轮潮流也终将过去。
此外,有必要回到对有关“人工智能”定义的共识,如果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指的是建造与人类有同等思考能力的独立智能体,那么我对它的可能性是非常怀疑的。但如果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指的是一系列“认知义肢”(cognitive prosthetics)工具的开发,我认为是有合理性的,这些义肢将会是我们能力的延伸。比方说,人类小孩有能力做简单的加法,但如果要学习更复杂的运算,则需要一些技巧,也需要工具。这些工具就是“义肢”,它增强了孩童的认知能力。在机器学习领域,我们开发出了关于模式识别和假设生成的种种系统,而计算机是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开发的种种“认知义肢”的延续,就像古代的算盘能帮助商人完成复杂的计算一样,算盘是商人数学能力的延伸。如上所述,我倾向于将人工智能视作“义肢”而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存在。当然,我们可以开开脑洞去想象奇点的到来,或者在我们之后存在于地球的人工智能,这本身很有趣,对这些场景的想象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状况。
您在写作中曾提到,真相的“收敛模型”[4]并不完全符合当今科学领域里密集运算的现实,但当代科学已经高度依赖运算和软件工具。汉娜·阿伦特曾写道,现代物理研究所设计的数据“不是现象、表象,因为我们在哪儿都不会遇见它们,无论是在我们的日常世界里,还是在实验室里: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仅仅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 测量仪器”[5]。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哲学层面的“真相”?

过去与未来之间
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张立立 /译
译林出版社,2011-10
塞蒙斯:很好的问题。我想,一方面我们应该思考计算机的工具本质和它们的局限。最显而易见的局限是:我们“创造”了它们,但我们有局限,我们会犯错误,比如你在前面提到的神经网络训练数据集的偏见问题。另一方面,“运算性”也逃不出系统的逻辑限制。计算机到底能做什么,其逻辑边界其实是分明的。
你问到对“真相”的理解,我想现在存在着很多无法抵达的真相。我们正处于一种“实际的不透明感”(practical opacity)中,我们使用的许多工具的运作过程如今已经不完全裸露在人类的肉眼观察之中,我们也无法如期待的那样完全理解机器学习系统,我们只知道这些系统能给我们提供不错的解释。但实际上,要完全搞明白这些运算过程是超出人类能力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哲学家就曾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时,计算机开始被人类用来证明数学定理,比如四色猜想。计算机证明了这条定理后,哲学家却遇到了问题——因为这个证明是“不可观测的”(not surveyable),换句话说,对于用大量机器生成的证明,我们无法一目了然。这是早在机器学习流行起来之前发生的故事,当时的计算机执行的只是所谓“传统的软件解决思路”。我们或许认为,我们确实得到了某种证明,但它是不透明的,因为这个“证明”并非一目了然。但事实上,有很多学科领域早就面临同样的现状,比如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我想没有人能了解它所进行的实验的每一个方面。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大科学”来说,“不透明感”就是它的现状。
许多科学家所谓的“真相模型”更像是一种“真相的渐近”,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逐渐逼近某一特定的真相。这也被称为真相的“收敛模型”,即我们会以渐近线的方式趋近真相。但我也认为,有理由相信这种对“真相”的描述依然有待商榷,我们的知识或许并不是逐步、渐近地向某一参考线推进的,因为我们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完全离散的。事实上,我们正走向不同的方向,而科学探究会渗透在所有的方向里。换言之,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很多“真相”,它们可能是不同的真相,而在所有复杂的人类工作里,都存在一种内置的“不透明感”。

▲《阿丽塔:战斗天使》剧照
至少从今天来看,关于“后人类”的讨论交织着计算机科技和生物因素,也暗含着对“人”的模仿、推测甚至改变,科技在铺设“后人类”的可能性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哲学研究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塞蒙斯:这些最终都会是哲学问题。我们不会从工程学或纯粹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意味着什么”,因为你无法把一个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分解为工程学或自然科学问题。你不能用科学本身来回答有关“科学的价值”的问题,也不能用科学论据来回答关于“科学论据的本质”的问题。对哲学家来说,我们基本是被困在哲学里的。哲学家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角色问题,但时刻需要担心自己所思考的问题的紧迫性。
我想,“人的价值”这个问题始终无法由科技来解决。如果你是福柯,你可能会认为“人”本身也是幻景,是一种错觉(delusion),“人类”的概念并不存在。但如果从常识来看,你可能会说“人”是一个物种,但哲学家会对此进一步追问,因为“物种”的概念也并非那么完备和清晰。我想,对哲学家来说,我们的工作恰恰在于如何建立关于对“人”的讨论,对“生物身份”和“人性/人格”的讨论,以及这些讨论之间的认知界限。
同时,人依然是具身化的存在,我们不是某种抽象对象,因此所有生物属性都依然和“人性”息息相关。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有能力对基因进行编辑,即我们有能力“工程化”自己的生理属性,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一选择恰恰和我们对“人的价值”及“人性”的思考息息相关。
虽然您说“‘后人类’只是一种哲学寓言”(我也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您也以“我们能教给我们的后人类后代什么?”为题发表过演讲,可否综述一下这个演讲的主旨?
塞蒙斯:假设存在一种计算机智能,或者说一种“后人类”的存在,虽然它具备各种能力,但这种存在依然会是一种有限存在。它的有限性植根于计算机的底层和逻辑局限。因此,“后人类”后代也依然会面临我们所面临的数学和逻辑限制,比如停机问题。如果这些未来的存在足够“智能”,它们可能会考虑这样一个策略:既然我是一个有限存在,我该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因此,它们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逻辑限制,还会包括有关“标准”的问题。甚至可以设想,它们是否会思考美学问题,即如何能更“美好”地生存。它们也需要思考人格的价值,即使它们的“人格”与我们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物种。
也就是说,个体性问题会延续到您所描述的“后人类”的状况里。
塞蒙斯:是的,它们也会需要考虑个体性问题,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所有的计算机(在不考虑任何技术限制的情况下)有可能相互连接在一起,那么它们也有可能成为“某一智能”。机器需要决定:“我是要融合进那个‘一’,还是我要自己待着?”“作为一个个体和作为一个与所有个体连接的存在,两者的价值有什么区别?”如果今天的我们可以接入其他人的思想和内部世界,我们或许也会面临同样的决定,即是否要成为“一体”。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但想象这样的情境有助于我们反思自我的存在。如果我们能成为“一体”,你会对其他的思想施加暴力吗?还是无条件地加入,抑或独自走开?这样看来,“隐秘性”似乎是人格的重要部分(如果“隐秘性”不存在,则有可能发生上述的情景,人们能进入彼此的大脑),它需要被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讨论隐私很重要,我们的个体性恰恰来自隐秘性。如果我们彻底裸露,则可能不再有今天意义下的“我们”了。
注 释
[1] 赛博格(Cyborg),通常指人类与电子机械共生的系统。
[2] “奇点临近”是由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提出的一种关于人工智能与人脑融合技术的乐观理论。
[3] 当前图像处理界最有名的数据集之一,多用来训练计算机进行图形识别。
[4] 收敛模型(convergence model),指我们理解真相的一种方法或趋势,即逐渐向某一确定值靠近。
[5] 《过去与未来之间》,汉娜·阿伦特 著,王寅丽、张立立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