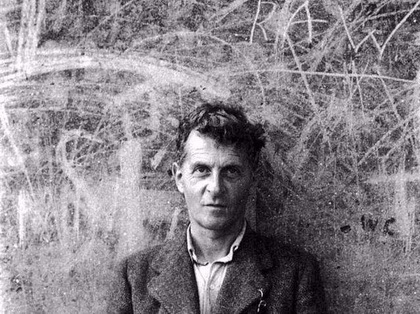一、艺术史的断裂与艺术史学的断层
如果把贾斯帕·约翰斯1955年的《旗》(图一)交给瓦萨里或者温克尔曼,他们会如何对它展开叙述?他们是在那张画中找到一个伟大的视觉规范,还是把那张画叙述为艺术大师们实现某个视觉目标的一个具体阶段?或者我们可以把《旗》摆到沃尔夫林、李格尔这类艺术史家的面前,他们能否从这张画的构图或者约翰斯的随意涂抹的笔触中找到某种风格类型?
对上述的这些艺术史家及他们的艺术史观念与方法来说,约翰斯的《旗》显然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旗》并不是在再现——不管是纹章学意义上的还是视错觉意义上的—— 一面美国国旗,而只是涂画出了(不是描绘了)一面国旗。在这幅画中,约翰斯的构图、造型和笔触都不担负着再现对象的意义,因此它们无法成为一种风格,也够不上一种趣味。因而,由于《旗》并不能被归入再现性绘画,那么,期望通过这张画来叙述某种视觉方式或者建立一个趣味规范也是徒劳的。
我们也可以请弗莱或者格林伯格这些现代主义批评家来评判这幅画。对弗莱来说,《旗》大概会让他不知所措,因为这幅画的形式实际上和生命情感没什么关系,它和任何一面星条旗的视觉形式是一样的,约翰斯显然没有去经营那些色彩和线条;再者,约翰斯在画这面《旗》的时候,因为旗(作为图像的旗,而不是在空中起伏飘扬的某一面旗)本身就是平面的,所以也根本不涉及弗莱经常津津乐道的赋形的问题。对于格林伯格来说,这张画肯定让他痛恨,因为从他的现代主义绘画观去看,这幅画的非错觉再现性与纯粹平面性完全符合他对现代主义绘画的“定义”,但这幅画的媒介与手段的纯粹性并不是为了给审美经验提供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斯对格林伯格开了一个玩笑。
对于现代主义中的审美主义来说,约翰斯的《旗》显然不是一个有审美价值的审美对象,因而任何形式的形式分析在这幅画上都找寻不到门径,以至于格林伯格会把它归于“次货”一类,也就是说拒绝承认《旗》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这显然是在回避问题了。
最后,我们还可以让帕诺夫斯基来对这幅画展开图像学研究,但我相信帕诺夫斯基在这里只能到达图像志的阶段,也就是说,只能描述出这张画的内容是一面美国国旗,再往下一步尝试着上升到图像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美国国旗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根本用不着费力去阐释,而且对约翰斯的作品来说,这样的阐释是不得要领的。同样,符号学的分析对这张画也毫无意义,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一面作为能指的美国国旗背后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指(甚至可以联系上这幅画创作时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但这样的阐释对于这幅画是多余的,因为它和图像学分析一样都没有把这幅《旗》与其他的(比如当时的美国援助物品包装上的)美国国旗相区别,但是约翰斯对美国国旗的使用却有着不同于意识形态象征的动机。
上述诸多艺术史观念与方法失效的原因在于艺术史本身的断裂,即约翰斯的《旗》所代表的是另一种质态和形态的艺术,因而它无法用既定的艺术史学去分析、阐释,及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史学本身出现了断层。
二、贾斯帕·约翰斯的意义
对于为何画美国国旗,以及靶子、美国地图、一系列数字等常见的图像,约翰斯有他自己的用意。在爱德华·卢西·史密斯看来,“他之所以选择平凡的图像,就是因为这种图像不会再产生任何能量了”。[①] 也就是说,这些图像因为太常见而失去了辉光(Aura),这样它们就不再蕴涵任何具有膜拜价值的象征意义,也不会带来审美感触。约翰斯把这些图像只是当作图像来使用,而不是审美对象或意义符号。
因此,在其出发点上,约翰斯的作品就是对任何形式的语义阐释与形式分析免疫的,或者说,约翰斯的着力点并不在于图像含义与形式意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绘画是没有内容的,不管是情节性的、再现性的、审美性的内容。甚至它们也没有符号性的内容。以《旗》为例,《旗》是一幅绘画,但同时也是一面国旗,如果我们把这幅画作为能指的话,那么它的所指也就是这幅画,也即是说,《旗》不存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没有能指与所指之分就没有语言性,因此,《旗》就不构成一个符号。
把约翰斯的《旗》与马格利特的《图像的背叛》(图二)作一番比较更能说清楚这个问题。在《图像的背叛》中,那只著名的烟斗是对“烟斗”这个词语的背叛,但其语境却是烟斗的图像能够代表烟斗的概念,否则马格利特的玩笑就是无效的。因此,马格利特还是把烟斗的图像当作一个符号来运用的,只不过他强调的是对图像与语言之间约定关系的怀疑。马格利特把绘画作为思想的视觉表达,在他看来,他的绘画视觉化了不可视的思想。[②]《图像的背叛》中的烟斗图像是烟斗实物的符号,这幅画本身也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在约翰斯的《旗》这里一切都大不一样。《旗》中的美国国旗并不是作为一个符号被使用的,那幅画本身就是一面旗,画中并不存在国旗图像指涉着国旗实物的情况。约翰斯也并不想用这幅画去表达他的思想,他给这幅画起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名字“旗”,这与马格利特处心积虑地用“图像的背叛”去暗示思想是多么地不一样。
约翰斯的《旗》这幅画本身不是作为思想的注脚而创作的,这是它与马格利特的《图像的背叛》最根本的不同。在马格利特那里,什么是绘画这一问题是自明的,因而绘画在他那里能够被当作传达思想的工具,但对约翰斯来说,对“什么是绘画”这个问题回答永远都只能是一种柏拉图所说的意见,因此他无法用绘画去表达什么,而只能是在绘画这一行为中给出一系列关于绘画的意见(并不是关于绘画的整体思考)。约翰斯的用意与意义正在于此。
也正因为此,约翰斯的作品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如果说它们有内容的话,它们真正的内容是作者的作画方式,更确切地说是思维方式。那么对于艺术史研究与艺术批评判断来说,真正要把握的是约翰斯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思考问题、角度与途径——他的艺术哲学,更确切的说:他的作为一种艺术意见的艺术哲学。
在分析约翰斯的艺术哲学之前,有必要把他与杜尚及安迪·沃霍区别开。众所周知,杜尚是第一个引发了“什么是艺术”这一思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第一个观念艺术家。但是杜尚的观念(我更愿意用‘哲学’一词,因为观念艺术中的‘观念’不仅仅是一个点子的问题,还包括着思维的角度与方法,也就是说它们是思想与思考方法——哲学)是隐匿在作品背后的,它们依赖于阐释,以及阐释的语境。比如就《泉》(图三)来说,一个脱离上下文的小便器再怎么都无法和关于艺术的哲学提问发生关系,所以必须由小便器的安置背景(博物馆)来引发思考,同时这种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批评家与哲学家的阐释。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并不包含思考,而只是能够引发思考。安迪·沃霍的作品,比如他的《布里洛箱子》(图四),也是这种情形,只有经过阿瑟·丹托这样的哲学家的一翻阐释,那个肥皂盒才不至于成为杜尚模仿秀中的一幕肥皂剧。
杜尚总是希望取消艺术从而弥合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泉》更多地是对艺术这个概念的挑衅。杜尚一直保持着达达主义的本色——反叛但从来不去建构什么。而约翰斯一直做着对艺术问题的自觉思考,作为新达达的他把杜尚所引发的空泛问题精确化,把杜尚的禅宗式的狡黠转换成了一种学科性的思辨与智慧。
在上面例举的那幅《旗》中,约翰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面用抽象表现主义式的笔触涂抹出来的国旗画到底应该是国旗还是绘画,简单地说,这个问题是:绘画的边界是什么——就这一点而言,约翰斯与极少主义者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这种提问是可持续深入下去的,不像禅宗式的狡黠只能是一次性的,三年后的1958年,约翰斯又把三幅国旗画堆叠到了一起,人们该把这件作品归入绘画还是浮雕,或者装置(图五)?他的靶子系列也是这样。在《有四个面孔的靶子》(1955) (图六)这件作品中,他把四个面孔模型与靶子并置在一起,其用意不是把它们作为符号而制造可能的隐喻,而是用人脸模型的立体效果去衬托绘画的平面性,以此来强调那个靶子实际上只是一幅画。在那些没有放置立体道具的靶子画中,约翰斯用绘画性的笔触与非写实的色彩等手段来强调这一点,就像在《旗》中做的那样。约翰斯一直用报纸做画底,并用蜡熔颜料强化涂抹的痕迹,这些都是为了强调那些国旗、靶子、地图、数字等等图像是画出来的,也就是说强调绘画的在场感(图七、八)。而另一方面,他却削弱绘画的社会、文化,以及审美的“内容”,以迫使观者去注视绘画真正的内容——在一个平面上的涂绘行为。
约翰斯真正在意而着力的就是如何涂绘,他的智慧总是体现在对绘画手段的思考上,而他常用的那些图像与符号只不过是他展开思考的平台,其本身并没有意义。因此,约翰斯并不能被称为是波普艺术家,如果波普指的是一种挪用大众图像的图像艺术的话,而约翰斯并不在乎那些图像与符号的含义与意义,他的作品只是寄生在这些图像和符号上,并没有和它们的内含发生关系。
实际上,这些图像与符号几乎贯穿了约翰斯的创作生涯,他经常返回到这些母题上来,每一次的图像与符号都是一样的,但每一次它们的用法都不同。1971年,靶子又回到了他的绘画中,但这一次他给了观者三种颜色与一支笔,让人们自己去做填色游戏,这样他使靶子完全成为了绘画这一涂绘行为的借口(图九)。
约翰斯总是使绘画手段凸现出来成为绘画的内容,他的很多绘画实际上是行动绘画。“画布……不是人们在其上生产、设计、分析或‘表达’一个对象的空间,不管是事实的对象还是想象的对象。正在画布上发生的事已不是一幅图画,而是一个事件。”[③] 这段罗森伯格用来建构其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概念的文字对于约翰斯的很多作品也是极为合适的。确实,在很多绘画中,他把绘画工具(如一把尺、一只假手)与绘制方式(涂抹、压印)转换为绘画内容,这些内容并不在讲述什么,而只是把绘画的手段和过程呈现出来,试图使人们意识到绘画的手段和过程才是绘画的本质,或者意义所在(图十、十一)。
他也把绘画图像与它描摹的实物对象并置在一起,呈现真实的三维空间与绘画平面上的三维视错觉之间的差异,以揭示绘画的二维性。这实际上是格林伯格所热衷的事情,但约翰斯的手段要智慧得多,他并不是直接论述出一个答案,而是采取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方式,使他的对话者(观众们)自觉地意识到了绘画的平面本质。在他1982年的《在画室》(图十二)中,一只涂着花纹假手和它的图像并置在一起,假手图像中的花纹的处理手法显示了绘画与实物的巨大差异,在这幅画的底端,一个微微有着透视缩减的矩形让观者产生了空间错觉,但约翰斯又安置了一根稍稍翘起的木条,这根占据着三维空间木条立刻消解了那个矩形带来的空间错觉。
晚期的约翰斯更加强调了绘画的行为过程性,他把一些经典的绘画作品加以改写,特别是在《描摹塞尚》(图十三、十四)系列中,塞尚的《大浴女》被用单色反复描摹,其艺术史文化意义与审美意义被消解殆尽,最终被还原成单纯的描摹行为。
可以说约翰斯的创作就是他对绘画及艺术问题的思考,即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意见。他的创作动力不是再现或表现的欲望,也不是使艺术介入社会的激情,更不是一种生命、生活体验,他所有的创作动机都是出于对艺术的问题意识。从一些细节上,我们也能管窥约翰斯对思想的嗜好。鸭兔图、花瓶人脸图等歧义图像也经常出现在他的画面中,而鸭兔图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重点分析的一个图像(图十五)。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他对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到早在1959的《失败的开端》(图十六)中,他把颜色与其书写的颜色名称相错位,形成了感觉经验和语言概念的分裂,而这恰恰是晚期维特根斯坦所竭力揭示的生活形式的事实。
三、是艺术哲学,还是哲学艺术
如果没有对艺术问题的自觉而持续的思考,就不会有约翰斯的如此这般的创作,这一点,我想已无须再次强调。但是,一种出于思考艺术问题的艺术,是不是应该属于艺术哲学,对这一点,还须暂存疑问。
在丹托那里,艺术已经被哲学剥夺,而在他的启迪者黑格尔那里,哲学替代艺术是以艺术终结论的预言出现的。黑格尔首先感到了艺术的衰落:
“不管这种情形究竟是怎样,艺术却已实在不能达到过去时代和过去民族在艺术中寻找的而且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寻找到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至少是宗教和艺术联系得最密切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④]
在一个“偏重理智”的时代,黑格尔认为,承担着用感性去显现理念的最高任务的艺术已经逐渐丧失了它自身的能力——感性,因此,艺术已经不再是实现人类心灵的最高旨趣——认识理念——的必要方式,因而艺术终将被宗教、继而被哲学替代:
“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经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⑤]
在黑格尔那里,艺术只是一个整体的以理念为其核心和最高价值的世界中的某个有机部分,一旦艺术脱离了这个整体就不再是必需的必要的了,而哲学将代替它的功能。其背后是一种艺术何为的诉求——当艺术不再能担当某种职能,它理因结束。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是以理念的名义对艺术的废黜,艺术只是失去了意义,并没有死亡。
但在丹托那里,艺术的终结是艺术史的终止,其原因是艺术标准的丧失使任何一种艺术史判断都无法出现,这样艺术自身的由人把握的自觉推进的历史就永远不会再往前发展了。其背后是对一种目的论的艺术史叙事的怀疑,因为艺术本身已经失去了目的。
不管是黑格尔还是丹托,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使艺术丧失真理性及判断标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逐渐地丧失了与这个整体世界的联系,因此失去了生气,丧失了与理念的联系。这是黑格尔的判断,但他并没有抓住要害,因为他没有从社会、历史层面来观察这一问题。
艺术从一个整体世界中孤立出来的原因并不在于文化氛围或者一种艺术潮流,而是社会分化使然,是艺术体制从其他社会实践领域中分化出来的结果,是一种体制层面上的艺术自主的结果。在一个分化得有些分裂的社会中,艺术只为艺术的目的而存在,这恰恰是艺术丧失其真理性的真正原因。这也是艺术丧失自身标准的深层原因,当艺术需要给自身提供标准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是无标准的,因为各有各的标准,在多元状态下,一个自足的一元无法暨越另一个自足的一元。
在艺术实际上成了一种只有专家才能把握和理解的活动的时候,它必然“不能达到过去时代和过去民族在艺术中寻找的而且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寻找到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废黜艺术,因为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的异在,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从社会其他领域中寻找,特别是当所谓的社会整体越来越受控于一种虚假意识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使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保持着距离才有可能使真理在场,起码在阿多诺看来是这样的。
除了社会体制层面的分化,艺术的自主也引发了对艺术以及各门艺术的基础的寻求,在这个层面上,所以的艺术活动都必须去确证自身。而这种自我确证,在格林伯格看来,只能是在艺术的范围内,以艺术的手段来展开。但在艺术没有得到确证之前,关于艺术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包括艺术这个概念。这就把艺术置入了一种哲学反思中,而在我看来,约翰斯的艺术就是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反思。
黑格尔在预言艺术的终结的时候,曾经描述过一种正逐渐转向哲学的艺术:
“现在艺术品在我们心里所激发起来的,除了直接享受以外,还有我们的判断,我们把艺术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段以及二者的合适和不合适都加以思考了。” [⑥]
如果说“把艺术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段以及二者的合适和不合适都加以思考”在黑格那里是昭示着艺术的学科化(艺术哲学)的出现的话,那么在约翰斯这里,一种建立在学科化研究之上的艺术创作已经出现了。但约翰斯的艺术创作并不是对艺术活动的哲学研究,而恰恰是倒过来的,是对艺术哲学问题的感性手段的询问。他的艺术并不诉诸哲学概念,但出发点却是对艺术的哲学反思,所以对艺术哲学及艺术史一无所知的观众是无法领会其奥妙的。
简言之,约翰斯的艺术是一种生发于艺术哲学的艺术,而评价这种艺术的标准是其问题意识的敏锐程度、提问方式与角度的独特程度,以及对接受者思维的启发程度。也就是说,这种艺术是有标准的,丹托有意忽视了总体叙事与局部叙事的区别,关于艺术的总体叙事的失效并不能代表所有艺术史叙事的失效,而通过约翰斯,我们实际上已经发现,艺术在他的这条道路上依然在发展着。在这条道路上,哲学,或者说观念成为了艺术的媒材,这种艺术可能不再和理念有关,也不再与审美有关,但它会始终与人的感觉和智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期待着一种深刻的主体性。
注释:
[①] 爱德华·卢西·史密斯:《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陈麦译,劳诚烈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②]参 马格利特:《致福柯信》,载Michel Foucault, This is Not a Pipe, Transl, James Hark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③] H · Rosenberg, ’The American Action Painters,” in The Tradition ot the New, p.23ff. 转引自《20世纪艺术批评》,沈语冰,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④]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一卷,第14页。
[⑤] 同上书,第15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⑥] 同上书,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