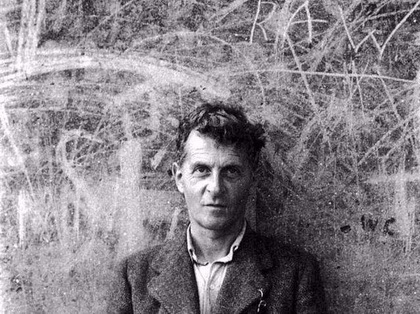一、 生态危机的警钟
科学与神学的关系经历过许多个阶段:攻伐、寄生、共存。近年来,二者的对谈似乎是从“领土需要”(territorial imperative)中产生的。伊安·巴伯(Ian Barbour)指出,新正统派(neo-orthodoxy)、存在主义和语言分析至少都同意把宗教和科学看作是完全独立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只有几乎很少的重合领域(尽管有些地方一致)。这种理论所关心的是方法论问题,而不涉及诸多科学的具体内容。这似乎成为急需要治疗手段。
如果科学和宗教完全是相互独立,则二者的冲突就可以避免。但这样一来,建设性对话和相互补充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人们不能把生活体验为截然分开的两个独立的车厢。把生活体验为整体和相互联系,才能发展出具体的学科,以便研究生活的不同方面。伊安·巴伯说,有充分的《圣经》根据使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全部生命和自然的主人,而不仅仅是独立的宗教领域的主人。系统阐明一种自然的科学,将会鼓励强烈的环境关切,在今天也是一项关键的任务。1)
有些人认为,神学内容与科学内容之间的某种整合是可能的。有三种整合方式:在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中,据称,上帝的存在可以从自然的设计的证据中推导出来,而自然的证据是科学使我们认识到的。在自然的神学(theology of nature)中,神学的主要来源存在于科学范围之外,但是科学的理论也可能影响到某些教义、特别是关于创世教义的重新表述。而在系统的综合体系中,不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推动了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如过程哲学)的发展。本文试图分别讨论自然神学和自然的神学以及二者的过渡与关系,由此阐发当代神学与自然的密切关联。
自然神学在欧洲神学传统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在英国,它同设计论论证联系在一起;自然世界的复杂多样性使人推导出其创造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神学是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的神学,而不求助于启示、《圣经》或类似的权威来源。另一方面,在德国,它是指以社会与历史的现实和结构(如种族与民族)为基础的神学。相反,自然的神学指的是以神学为根据对自然世界的反思。在神学圈子里,从事自然的神学而不是自然神学,在政治上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对神圣活动的信仰本身并不被看作是遵从科学知识,尽管对神圣的活动可以根据自然科学中的模式来描绘。当科学家与哲学家通过他们的科学知识寻求意义或奥秘时,自然神学的风格便公开呈现出来。鲍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也把自己说成是复兴自然神学。他认为复兴自然神学是在完成下述任务:寻找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最深刻的可能的解释,寻找一种对经验世界的最全面的流行的解释。尽管他有时(例如他考察宇宙的可理解性或人类学的巧合时)是从科学出发论证关于上帝的论断,但鲍金恩对神圣活动的讨论和对自然邪恶的讨论更符合自然的神学的传统。
自然神学依据宇宙的可理解性及秩序等宇宙的特征来捍卫信仰的真理其合理性。如果说秩序或可理解性是人们强加的,则这一论证就不会流行。自然神学要求达到的结论同样是实在论的:上帝是客观的、超自然的存在。我们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善的,但是意图却是神学中的实在论。
并非所有赞成科学的与神学的实在论的人都试图从科学来论证神学。其他的人试图把科学的见识同神学信念综合在一个更广泛的架构中,例如,自然的神学便把关于实在的知识(某种形式的科学实在论)同关于上帝的观念(采取神学实在论的形式,并不必然地采取科学实在论的路线)结合一起。这样的一种综合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提高了神学的声望。如果科学知识和神学主张可以结合在一个单一的体系中,则关于神学与科学二者不一致的观点就会放弃。一种斡旋的、综合的方式有助于向那些按照科学方法认识周围世界的人们传输宗教观点。即使科学知识内容和神学知识内容不能被结合在一起,神学家仍旧对科学实在论感兴趣。
然而,很多迹象表明,对生物学发现的内容重新关注,再度使基督教神学与伦理思想面临难题。新的问题来自微观生物学和宏观生物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在普通人看来,这些发现同对人类的基因控制的可能性,同通常被称为“污染”的环境危机有关。生态学成为一个热门政治性话题,并成为代沟的新标志。它也可能成为制定基督教神学与伦理学的富有成果的新模式。
一九七0年四月地球日(Earth Day)使基督教神学面临双重挑战:一、制定一种对自然环境负责的伦理学;二、详细阐明一种关于自然的神学。尽管从逻辑上说,前者最终取决于后者,但是,如果不能制定某种伦理学,则人类自身而临存亡续绝的问题,神学家们就没有闲暇从容不迫地进行神学反思。
然而,今天,对宗教与环境科学的重新对话的最有影响的号召力却来自神学界以外。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号召建立“土地伦理”(land ethics)和生态良心(ecological conscience)。他说,除非有哲学和神学的关切,否则,就不会有严肃的环境保护。
要求社会科学全身心地关注自然的价值的最有力的挑战来自米恩斯(Richard Means)的《伦理命令》。他说:“我们对自然的运用和误用,必须脱离单一的经济考虑的背景,并坚定地根据社会与伦理价值领域来考虑。”2)
我们时代建立自然——伦理(nature-ethic)的最著名的宗教尝试是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尊重生命的哲学”。由于认为以前所有伦理的巨大错误在于它们仅仅局限于人类生命,所以,施韦泽要求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至今,这仍然是把一切生命都包含在伦理学中的最令人钦佩的尝试。然而,它仍有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施韦泽自己对野生生命的理解几乎完全是中产阶级欧洲人的理解,在生态学上也是幼稚的;二、他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体现在二元论的生命哲学中,它强调精神与自然、意志与理性的对立,因而导致浪漫主义的和朴素的个人主义。克拉克(Henry Clark)在同情性与批判性研究著作《施韦泽的伦理神秘主义》(波士顿,1962)中建议通过蒂利希(Paul Tillich)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影响来消除这些缺陷。蒂利希是近代真正赏识自然的少有哲学家之一。然而,对蒂利希的研究者很少有人注意他的思想的这一方面。
二 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指的是不依赖于信仰或特殊启示,而仅仅凭借理性与经验来构建关于上帝的教义。这一名称大概始自罗马古文物研究家瓦罗(M.Terentius Varro)。他区分了诗歌神学、公民神学和自然神学。其中,自然神学指的是对于神性的哲学思考。它是哲学家关于自然与实在的解释的一部分。这样看来,自然神学并非与启示神学相对立。但在基督思想史上,二者却尖锐对立。自然神学从一开始就有三个特点:其一,辩证上帝的存在;其二,反对唯物主义,其三,对混沌无序及罪恶进行反思(即神正论)。从自然神学观点看,人们可以宣称,从原则上说,有可能获得拯救所必需的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既然坠落的人类的理性如此败坏,因此,启示仍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宗教改革家们的观点。人们也可以宣称,尽管理性可以验证神圣存在的存在与仁慈,但仍有某些超自然的真理,从原则上说是理性能力所不能确立的。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在自然神学中,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历史启示(启示神学)或宗教经验(自然的神学)的基础之上。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puinas)的五种证明方法就包含了宇宙论证明的几种形式。有一种证明断言,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一因(First Cause)才能避免无穷追溯。另一种证明说,都可能不存在,它依赖于那必然存在的存在。这些问题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界限问题(boundary questions),因为它们仅仅指世界的存在及其一般特点。目的论证明可能同样是从作为自然的一般特征的秩序性和可能性出发。但是,自然中存在着设计的具体证据也会被引用。这一论证形式常常是从科学发现中得出的。
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常常表现出对自然的和谐的关联的敬意,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杰作。牛顿说,离开了光学技能,眼睛就不可能被设计出来。波义尔(Robert Boyle)赞扬全部自然秩序中仁慈设计的证据。如果说牛顿的世界是一个完善的钟表,那么自然神论的神就是它的设计者。十九世纪早期,佩雷(W.Paley)说,如果你在荒原中发现一块手表,你就可以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它是一个有理智的存在者设计出来的。在人类心目中,许多复杂的零件都和一个有远见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这里,同样,你可以得出结构,存在首一个聪明的设计者。佩雷引用许多复杂部件的合作以完成某种单一功能(如眼睛中的视觉)的例证以证明一个聪明的设计者。
休谟(David Hume)早已对目的论证明提出严历的批评。他看到造成自然中的模式的组织性原则可能就在有机体内部而不是在有机体外部。他认为这一论证至多只是表明一个有限的上帝或许多种的存在,而不能证明唯一神论的全能的创造者。如果世界上存在着邪恶和机能障碍现象,难道也可以把它归因于一个具有不太仁慈的意图的存在者吗?然而,正是达尔文对这一论证给予最严历的打击,因为他证明适应性可以用偶然的变异和自然选择来解释。一个自动的和非人格的过程可以解释自然中的明显设计,尽管他在后期仍旧承认进化规律本身是聪明的设计的产物。
许多新教徒对这一争执视而不见。他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以启示为基础,而不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另外一些人赞成对这一论证加以改进。他们说,设计是很明显的,但是它不在单个有机体的特殊结构中,而是在物质的属性和自然规律中。进化过程藉物质属性和自然规律产生这些有机体。上帝的智慧正是在对整个过程的设计中才能被看到。三十年代,腾南特(F.K.Tennant)主张,自然是相互支持的结构的统一体系,它导致生物有机体,并为人类道德的、美学的和理智的生命准备了条件。3)对目的论论证的重新表述。在罗马天主教思想中是司空见惯的。传统天主教思想认为自然神学是启示神学真理的准备而加以尊重。4)
在现代西方,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布伦纳尔(Emil Brunner)有过激烈争论。巴特拒绝自然神学的概念,而布伦纳尔则捍卫自然神学的观念。这一争论具有政治意味,因为巴特相信,教会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基本争执是:教会难道不应当绝对和唯独信赖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巴特的观点构成福音派教会著名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的基础。巴特的“以基督为中心”并没有被改革宗神学家诸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以及蒂利希所接受。蒂利希认为,自然神学系统地阐明关于上帝的基本人类问题,而不是提供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或证明。神学的任务因而就是证明,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人类意识到有限性和存在本身;其次是揭示,基督教的象征对这些基本人类问题做出了回答。
对这一问题的上述任何回答都没有被普遍接受。许多年轻的神学家由于受到分析哲学、过程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因而试图以新的方式理解这一问题。
英国哲学家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全面捍卫自然神学。他从讨论科学哲学中的证实理伦(confirmation theory)开始。在科学发展中,新的证据并不能使理论变得确实。相反,一种理论起初具有合理性,它之为真的概率会随着证据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贝斯定理)。斯温伯恩认为,上帝的存在起初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具有简单性,根据行为者的动机对世界做出人格的解释。他进一步主张世界中秩序的证据增加了有神论假设的可能性。他也主张科学并不能解释世界上的有意识的存在。为了解释意识的起源,就需要“物理规律之纲以外的某个东西”。最后,宗教经验提供了另外的重要证据。斯温伯恩得出结论:“从我们的全部证据看,有神论更为可能。”5)
最新的设计论论证文本是宇宙论中人类学原则(Anthropic principle)。天体物理学家发现,如果早期宇宙中某些物理常量和其他条件同它们曾经有过的数值稍有不同的话,则宇宙中的生命便不可能出现。宇宙似乎被安排得正好适合于生命的可能性。例如,霍金(Stephen Hawking)说:“如果在大爆炸之后一秒钟内膨胀的速度小到1/20,则在其达到现在的规模以前,宇宙便可能再次坍塌。”6)戴森(Freeman Dyson)由此得出结论:“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这些偶然事件的存在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宇宙是一个意外的适合于有生命的生物安家的宜人之地。作为一个受过二十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思想和语言习惯熏陶的科学家,我不认为宇宙建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我只是宣布宇宙建筑同下述假说是一致的:心智在其运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7)
巴娄(John Barrow)和梯普勒(Frank Tipler)提出许多例证,根据这些例证,早期宇宙中的多种力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8)哲学家莱斯列(John Lesile)把人类学原则当作设计论论证来捍卫。但是他指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应当是许多个世界的假定——或者是在一个振动的宇宙的相继循环中,或者走在同时并存的独立领域中。这些世界彼此可能不同,而我们正好生活在一个包含着有利于生命出现的可变因素的世界之内。9)此外,这此显然任意的条件中的某些条件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存在着物理学家正在制定的更基本的统一理论。
伯明翰主教蒙特弗洛尔(Hugh Montefiore)宣称,宇宙中存在着许多设计的例证。包括人类学原则和进化的方向性。其他例子如拉夫洛克(J.Lovelock)的“盖亚假设”和谢尔德雷克(R.Sheldrake)的“形态发生场”(morphogenetic fields),在科学共同体中尚有很大争议。蒙特弗洛尔并不声称这些论证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他仅仅声明,后者比其他解释更为可能。10)
关于这些论证的有效性的争论仍在继续。在一个宗教多元化世界里,自然神学仍具有极大吸引力,因为它从科学资料开始。我们可以以科学资料为根据期待文化与宗教的一致性而不是差异性。这些论证可以克服阻碍信仰的障碍,因它证明设计者的观念像其他的解释假说一样合理。但是,即使接受这些论证,它们也不会导致一个《圣经》的人格化的上帝。正像休谟提出的那样,它们只能导致一个远离世界的智慧的设计者。此外,很少有人实际上是从这些论证中达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自然神学可以表明,上帝的存在是合理的假设,但这一推理过程与宗教共同体的实际生活相差太远太远。更重要的是,自然神学同现代科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甚远。
三 科学与通向上帝之途
把神学和自然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胎源往古。早在基督教时代最初六个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与科学家就把通向上帝之途与通向科学之途、把对被造物的科学认识与对上帝的神学认识结合在一起思考。公元前一世纪,有些科学家就满足于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先验的(a priori)抽象理论形式来认识世界。他们公开探讨实证问题域制定“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以便揭示他们研究的实在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家受到新学园派(New Academy)的攻击,被他们称为教条神学(dogmatics)。他们认为科学是严格符合自然的行为,其目的是揭示所讨论的任何实在的实际性质。这被叫做“教条式科学”(dogmatic science)。
在教条的科学中,科学思想忠实地服从于某种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约束。它要求人类精神同那个实在一致,因为实在逐渐向我们显示出来,决定着我们如何真正地思考它,如何表达我们对它的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与实在是同义词。只要在对象的特定性质及其产生的知识的制约下制定出合适的推理样式,这种严格的科学的探究方法就可以运用于任何科学知识领域。在亚历山大城,有关对上帝的性质和活动的科学的神学探讨就这样被古代教会伟大神学家发展起来。神学家们和科学家们相互影响;通过上帝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上帝,影响到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神学科学对创世的认识也影响到自然科学对上帝的认识。
正是在亚力山大城,神学与科学传统开始合流。神学与科学从概念上、认识论上和语言学上相互作用。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道成肉身和创造的教义上,集中到被造的时间与空间秩序中的道成肉身的教义上,所以,在知识的基础和宇宙论世界观方面便发生了急剧变化:神学与科学开始被放在同一个单一空间与时间的世界中进行研究。因此人们应当注意整个被造秩序,因为它来自上帝,并被上帝之道所维持。六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与科学家菲洛诺(John Philoponos)认为关于上帝的知识和关于宇宙的知识相辅相成。全部近代经验理论科学都把这一点作为终极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托伦斯(Thomas F.Torrance)认为,可以有保留地说,通往上帝的途径与通往科学的途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认识上帝与认识科学是一致的;科学是通向上帝的途径。
菲洛普诺提出了革命性的自然科学概念,反过来又助长了关于道成肉身的神学。菲洛普诺对有关神圣真理神学的理解使他对世界的偶然性质及其合理秩序有了更现实的认识;同时,他的物理科学的动态特征也影响到他的神学的动态特征,深化了他对认识论基础和视角的了解。他从未想到从世界推演出创造主,因为那将假定二者之间有一个种逻辑上的联系。不!他认为世界是上帝出于自由而创造的,并赋有不同于上帝超验理性的偶然的理性形式,因而超越自身指向创造主。这就是说,他的基督教神学使他接近科学,他的科学又使他接近上帝。对他来说,上帝的非受造之光与世界的受造之光的神学划分十分重要。
偶然性(contingence)的概念(偶然的实在、偶然的秩序)是极其重要的概念。我们的全部近代科学,特别是从麦克斯(Clerk Maxwell)和爱因斯坦以来的近代科学都以此为基础。正是被基督教神学推向极端的《圣经》“从无中创造” (Creatio ex nihilo)的概念使经验科学在理性上成为可能并导致它的早期诞生。偶然性是指,由质料和形式组成的整个宇宙是上帝的自由创造并被赋予它自身特有的理性;这理性根本不同于上帝的超验理性,但却依赖于或附属于后者。
偶然性指的是理性秩序的肯定方面,它并非自我解释(self-explicable),而是超出自身指向秩序的超验基础,以其作为一切既存事物的终极理由。偶然性不是自然科学可以解决和解释的。然而,我们全部的自然科学及其试图制定的自然规律,本质上都同宇宙的偶然性质及其理性的偶然形式有关。这意味着,自然科学不能解释自身,因而没有办法从科学探讨的世界的偶然性质或理性来推论上帝,因为这将设定世界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说,自然科学及其所探索和试图认识的自然世界实际上可以提供通向上帝的途径。然而,托伦斯认为,因为世界的理性秩序是偶然的,就其本性而言,它公开超越自己,默默无言地迫切需要一个创造主。自然科学还不是接近上帝的途径;它只是打开了通往超越自身去认识上帝的途径的门户。由于具有偶然的理性秩序,所以,自然科学在制定自然秩序时,超出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超出自身,默默无言地指向某种形式的“规律外的规律”(law beyond law),指向一种终极的“为什么”(why)的问题或规律的超验的理由(transcendent reason)。由于具有偶然的性质,所以,离开同上帝的关系,世界最终便不可理解。
科学本身不可能认识自然的秘密的终极核心——除非以超验性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找到自然规律的终极理由。找句话说,秩序的概念不能被科学所证明。对秩序的信念是科学的,从而也是一切理性思想的必要前提。那么,如何理解所谓“自然神学”呢?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到两点:一、应当认真考虑早期基督时代科学家和神学家提出的教条式科学的性质;二、应当考察我们时代广义相对论对认识论的意义。
在严格的科学中,我们对任何领域的探究都允许领域的性质和对象的性质决定我们如何认识它,如何思考它,如何制定关于它的知识。如何验证这一知识。这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神学。在每一种科学中,人们都制定了符合对象的特殊性质的推理样式。符合无生命的实在的推理样式不同于认识动物的推理样式,也不同于认识人的推理样式。这是从非人格的推理样式到人格的推理样式的转变。我们不能把人当作客体来控制。但是,当我们转而探究对上帝并试图按照他的本性(Nature)来认识他时,人们就能以同样方式把他客体化。对作为我们认识对象的上帝,我们的认识关系面便发生了认识论的颠倒:在按照上帝的终极神圣性质来认识上帝时,托伦斯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自我启示和恩典来认识他,因而只能在崇拜、祈祷、崇敬中对上帝神圣的主动性亲自、谦卑而顺从地做出应答,使他自己作为创造主和救主被我们认识。上帝如何被认识,是由他实际上如何被认识来决定的,即通过他的自我启示。这里,人类推理的样式发生了很大调整,以便适应上帝的超验性质的强制性要求。这就是科学神学或教条式科学所涉及的:严格按照上帝的本性及其真理或实在来认识上帝。在严格意义上,这就是自然神学,是符合上帝的本性的神学。
今天,广义相对论拒斥二元论,并发现在自然和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的各个层次上,经验与理智互相联系,因而上述认识方法被大大加强。这对传统自然神学影响很大。爱因斯坦以相对论为根据拒绝牛顿的绝对数学化空间与时间和运动的物体的二元论,拒绝几何与经验的二元论,即拒绝科学认识中理论与经验要素的二元划分。他说,不应当把几何学同经验分开,把它理想化,使之成为独立的概念系统,作为获得和组织物理知识的外部框架。他认为,几何学应当被放到物理学之内,在这里,它成为同物理学不可分离的自然科学的一种形式。这并不是说它被物理学吞并或消失了,而是说,几何学成了物理学的核心中的认识论结构。没有物理学,几何学便不彻底。
托伦斯相信,对作为信仰的先导(praeambula fidei)或作为先于关于上帝的实际知识的独立的概念体系的自然神学应当加以拒斥,因为它作为认识框架来解释和阐明关于上帝的真正的或实际的经验知识,使之服从于扭曲的思想形式。排除独立的自然神学,是严格的科学方法所要求的,因为严格的科学方法要求我们的全部前提和每个预定的框架都要接受探究过程中所真正揭示的事物的审查。然而,托伦斯并不全然拒绝自然神学,他认为应当把自然神学转变成神学的实质内容,以变化了的形式服务于人们关于上帝的知识的认识论结构。这样,自然神学便不再是外部的参数(parameter),也不是脱离人们关于上帝知识的实际主题的独立的逻辑结构,这同圣安瑟伦(St.Anselm)的信仰寻求理解(先信仰,后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对信仰的解释一致,也同对自然科学的正确认识一致,因为它是在基督教关於宇宙的偶然的合理秩序的教义影响下产生的。11)
托伦斯相信,对时空宇宙的严格的科学和数学的解释,强化了关于一个由偶然的合理秩序组成的开放性的宇宙观念,它超出自身,标明在创造主那里有一个理性秩序的超验的基础。这并非说科学本身或凭藉其自身基础就是通向上帝的途径,而是说,它服务于通向上帝的途径。这途径是上帝藉他在耶稣身上道成肉身的道 (Word)和光(Light)给予人们的。这就是自然的神学。这样,独立的自然神学便不复存在,但它并未完全消失,它包含在自然的神学中。
四 自然的神学
自然的神学并不像某些自然神学那样从科学开始,相反,它从基于宗教经验和历史启示的宗教传统开始,但它认为必须根据当前的科学对某些传统教义重新加以制定。这样,科学和宗教便被认为是相对独立的观念的源泉,而同时它们的关切却有部分重合领域。具体说来,创世、天意、人的本性的教义都受到科学发现的影响。宗教信仰如果要同科学知识协调一致,则要进行某些调整和修改。神学家们将会希望吸收公认的科学的许多特点,而不是适应行将被抛弃的有限的、思辨的理论。神学教义必须同科学证据一致,尽管科学证据并非必不可少。
我们对自然的一般特点的认识将会影响我们关于上帝同自然的关系的模式的认识。今天,自然已被看作是充满着由突然出现的奇异组成的漫长历史的动态进化过程,其特点是或然性和规律性。自然秩序是合乎生态的、相互依赖的和多层次的。这些特征将修改我们对上帝和人类同非人的自然的关系的描绘,反过来也影响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并对生态伦理具有实际意义。邪恶问题也将被放在进化的世界中而不是放在僵化静止的世界中重新加以考虑。
生物化学家和神学家皮考克(Arthur Peacocke)认为,神学反思的出发点是一个连续的宗教共同体的过去和当下的宗教经验以及连续的解释传统。宗教信仰是由共同体的同意和连贯性、全面性和有效性的标准来衡量的。但皮考克乐意根据当前的科学来重新阐述传统的信仰。他详细讨论了在宇宙论、量子力学、非均衡热力学和生物进化中或然性和规律所起的作用。他描绘了有机生命和心智的多层次等级结构中较高复杂层次上的独特活动形式的出现。在对所有层次上的潜能的探究与表述中,或然性具有积极作用。上帝通过充满规律性与或然性的整个过程进行创造,而不是通过对这一过程的中断进行干预来创造。“自然因果的创造性事件联系本身就是上帝的创造性活动。”12)上帝通过科学所揭示的自然世界的过程进行创造。
皮考克用大量的比喻来谈论在一个充满或然性和规律性的世界中的上帝的活动。他说,或然性是上帝的雷达,它扫描可能性领域,引起自然体系的多种多样的潜能。他还用艺术家的活动来比喻目的性和开放性相互依存的同时存在。皮考克把他的观点说成是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而不是泛神论(pantheism)。上帝在世界中,但世界也在上帝中,因为上帝不仅仅是世界。在另外一个地方,皮考克把世界比作上帝的身体,上帝是世界的头脑或灵魂。皮考克用许多生动的比喻来讨论上帝同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秩序的关系。
耶稣会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是自然的神学的另一榜样。某些解释者认为,《人的现象》一书是自然神学的一种形式,是从进化论论证上帝的存在。但伊安·巴伯认为这部著作更应当被看作是对科学观念和从基督传统与经验中产生的宗教观念的综合。德日进的其他著作清楚地表明他深爱他的宗教传统和他自己的宗教性灵的影响。但是他的上帝概念也受到进化观念的影响,尽管并不是从对进化的分析中产生的。德日进谈论连续的创造和上帝内在于一个未完成的世界中。他关于向欧米伽点(Omega Point)的最后趋同既是进化的方向性的思辨性延伸,也是对基督教末世论的独特解释。13)
任何自然的神学都认为应当澄清下列几个问题:是否应当重新阐明关于上帝全能的古典概念?几个世纪以来,神学家们为上帝的全能、全知同人类自由和邪恶与苦难的存在如何协调争论不休。但是,在各门科学领域中,或然性的作用提出了新问题。我们还可以维护关于神圣全能的传统观念,坚持认为在科学家所说的或然性中所有事件都是受上帝天意控制的吗?或者,不论是人类自由,还是自然中的或然性,都反映了上帝对预见和权力的自我限制,而这又是这样一个世界的创造所必需的吗?
我们应当如何描绘上帝在这个世界中的行动?传统对第一因和次要的因的区分保留了科学所研究的次要因果键的统一。上帝并不干预次要因,相反,却通过次要因行动。次要因自身又对所有事件给予彻底解释。这倾向于自然神论(Deism),因为上帝从一开始就为万物拟定了计划,以致万物可以通过自己的结构(决定论或者或然率)展示出来。以便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圣经》所描述的神圣活动的独特性是否会被上帝与自然原因同时起作用的一致性所代替呢?我们还可以仅仅谈论上帝的一次性行动,谈论宇宙历史的整体性吗?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神学应当回答的。
今天,自然的神学必须为我们这颗涉危的行星上的环境保护提供动力。环保主义者正确地批评基督教以牺牲内在性为代价,片面强调神圣的超在性,并严禁格划分人类自然。《创世纪》中对自然进行统治的观念有时被用来为无节制的统治自然辩护,其他被造物被当成为人类服务的手段。但近来许多作家要求恢复《圣经》中强烈支持环保主义运动的主题。
当前,重新呼唤关于自然的神学,首先是从基督教神学开始的。一九六四年秋季号《对话》(Dialog)发表了关于“创世与救赎”的专栏论文,包括斯特勒尔(Joseph Sittler)大声疾呼重新关注自然的文章。他还在《基督教世纪》上发表了〈一种关注地球的神学〉(1964年9月,37/3)。狄特曼森(Harold Ditmanson)在《呼唤一种创造论神学》中评说了路德对自然神学的恐怕,提出了一种“创造的神学”(a theology of creation)。它从启示开始,而不是从自然开始,不是从自然证明上帝(自然神学),而是把上帝的启示活动与自然联系在一起。
一种关注自然的神学的发展,不仅要解决新教对自然神学的反感,而且要解决流行的科学与宗教间的君子协议:把宗教和科学看作相互独立的语言游戏。巴伯对二者的分析极为平和:他提出,最招人注意的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读者应该注意鲁斯特(Eric Rust)的《科学与信仰》(纽约:牛津,1956)和《进批论哲学与当代神学》(费城:西敏寺,1969)以及澳大利亚生物学家伯奇(L.Charles Birch)的《自然与上帝》(费城:西敏寺,1965)。博尼法齐(Conrad Bonifazi)在《事物的神学》(费城:1967)中广泛利用了基督教传统和西方文献,证明物质在基督教观念中的意义。
推动自然的神学的还有埃尔德(Frederick Elder)的《伊甸园危机——对人与环境的宗教研究》(1970)。他相信,生态危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人类的行为表明好像自己在生物领域中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包容性(inclusive)观念与排斥性(exclusive)观念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埃斯勒(Loren Eiseley)被认为是一系列生态学家和进化论者的代言人(“进化论首先是历史的生态学”)他把人看作是自然之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这种观点称为“生物中心论”(biocentric)。与此相反的是顽强的基督教排斥性的与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传统。它把人同自然世界分开,并抬高人的地位。被埃尔德引为排斥主义的近代例证是德日进、考克斯(Harvey Cox)和理查森(Herbert Richardson)。
这一类型学有助于揭示人类究竟应当把自己同自然生态联结在一起,还是可以创造自己独立的生态系统这一问题。但这一区分带来更大困难:尽管包容主义观点被当作基督教的首选而被垂青,但埃尔德并未证明它应当超越那杂染了神秘经验(numinous experience)的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而且,他把德日进算到考克斯和理查森的排斥主义营,也有问题。毫无疑问,德日进在《人的现象》中“以人为焦点”以及关于“自然的人化” (hominization of nature)可以看作同考克斯的《世俗之城》或理查森的系统神学是相似的,但他之所以吸引许多追随者,是因为他有机地把人类放到进化过程之中。他对未来的洞见,是诗性的、非精确化的。他是企图通过技术建立完全属人的“环境”,还是探求一种包容自然在内的更大范围的视野,这有待于考查。德日进很可能应当被看作和赫胥黎(Julian Huxley)等人一样的“垂直层次论者”(verticalist)。他们把人看作是在进化中突现的,但又承认人所特有的新的可能性。
埃尔德的神学与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的神学非常相似。尼布尔关于与环境一致的伦理概念(《负责的个人》,纽约,1963)在本质上是生态论的。它打开大门,以便以比纯粹属人的方式更宽阔的方式来理解“善”与“恶”。尼布尔的极端一神论(monotheism)及其以价值为中心的关系主义(relationism)的价值体系超越了人类中心论和生物中心论,使得有可能把上帝、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看作真正以神为中心(《极端一神论与西方文化》,纽约,1960)。
沿着上述路线,基督徒有可能为解决人类同其环境的关系发表正确的神学与化理意见。
五 通向生态论自然的神学
在神学创世论的历史上,有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圣经》传统和古代世界的宇宙图像融合为一种宗教宇宙论。在这种融合中,不但赞美宇宙的泛神论因素,而且贬低宇宙的诺斯底派因素,都被排除在外。创造主在同他的创造物的关系上的超越性的神学观念,引起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限的、偶然的和内在的世界的宇宙观念。在第二阶段,科学摆脱了这种宇宙论的束缚,神学也使它的创造论从宇宙论中彻底分离出来,把创造论归结为个人对创造信仰。科学与神学热衷于划定彼此的界限。今天,科学与神学已进入第三阶段。现在,如果人类和自然毕竟要在这个地球上存续下去的话,那么,在生态的压力和寻求神学与科学二者却必须为之奋斗的新方向压力下,神学与科学成了患难中的伙伴。科学家们发现,他们不断努力在神学与科学之间划清界限,是不必要的,因为原先对自身毋庸置疑的信仰已不复存在。科学家们也发现,基督教神学并不维护陈腐世界观,相反,它不仅在宇宙论领域,而且在社会实践领域,都是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伙伴。在全球出现“要么一个世界,要么没有世界”的状况下,科学和神学没有能力对一个单一的实在加以剖分。相反,神学和科学将共同实现对世界的生态认识。此即自然的神学阶段。
今天,如果人们把实在划分为人与自然,无论从科学上述是从神学上说,都是虚假的。今天如此迫切需要的生态论自然的神学,其目的不是要满足意识形态对一种封闭的世界观的需要,它的目的应当是为生态世界危机提供参照点。可以说,在神学与科学之间龃龊迭起的关系中,沉默不语和行将死亡的自然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第三个伙伴。结果,神学与科学的分离只是微不足道的争端。基本的要求是在生态方面使神学与科学都同自然环境相适应。
科学知识正在迅速增加。通过一成不变的世界观来束缚无所不包的理论,是不明智的。从意识形态上来支持这些世界观,或者通过政治权威来推行它们,也没有益处。知识的宝库迅速增加,以致单个的理论及其总的方向也将比以前更加短暂,更容易被代替。它们越来越具有临时草图的特点。它们必须是可以变化的,本身必须是创造性的。因此,一种有关自然的神学理论将既是可变的,也是临时的。
进入生态阶段,我们开始根据生命系统自身特殊的环境来认识生命系统。事物不再仅仅是人的主体的对象。它们同时也处在自己的环境结构和自己的环境交往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也开始在他的环境中,按照他的环境来理解自身及他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意味着客体化的思维方式被吸收到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中。单一化的看待事物的方法被变成综合的方法。同认知的主体相联系的认识,被参与性的认识所代替。在第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把客观孤立起来。在第三阶段,更重要的是把客体融化到它们活生生的世界中。
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的神学的任务是什么呢?科学业已向我们表明如何把创造理解为自然。现在,神学必须表明,应当把自然理解为上帝的创造。把自然看作是上帝的创造,意味着既不把它看作神圣的,也不把它看作是邪恶的,而是把它看作“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它就不是必须的存在;它只是偶然的。如果它是偶然的,那它就不能从上帝的观念中演绎出来。它只能通过观察被认识。因而,我们藉以理解并认识世界上各种现象的理性秩序,本身就是偶然的、暂时的和易变的。自然规律也是如此。
在这个背景中,凡是能够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的一切,都应当被看作是“自述”。但是,创造的概念还不止如此,因为在它看来,不仅被变成对象的实在是被造的,而且面对这一实在的人的主观性,以及人的有限的精神,也是被造的。在现代科学对主体与客体的每一种划分中,创造信仰看到的是被造的共同体——可以是被分裂的共同体。但毕竟是没有被清除的创造共同体。即便是由理性和意志组成的同自然相对的人类主体性,也是被造的、偶然的,永远不会变成绝对的。
但是,创造的概念甚至大大克服了人与周围可以认识的自然之间的充满张力的历史。根据基督教的信条,上帝是天和地的创造者,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的创造者。因此,可见的、人类可以理解的、可以用科学方法认识的实在,只是创造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使之成为他们认识和统治对象的那个“自然”,对神学来说只是被造物的可见的一部分。因而,把自然理解为上帝的创造,就意味着把已经认识的那一部分实在和尚未被认识的那一部分实在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从而把已知的部分看作是相对的——不是指向自身存在,而是指向自身以外。
为了把自然理解为上帝的创造,基督教神学不可能认为当前的世界状况是纯粹的神圣的“创造”,并分享上帝原初的判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保罗承认被造物的“焦急等待”及“渴望”,更适用于被造世界的当前状况。被造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叫它如此的(罗8:19-21)。受无常的奴役所造成的强制和对上帝荣耀天国的未来的渴望的开放性,决定着世界的当前状况。不仅人的世界是这样,它也适用于整个被造物。任何在当前世界状况中看到“创造”的人,都和被造物一道受苦,也为被造物盼望。在这种状况下,被叫做“自然”的,既不是纯粹原始状态,也不是万物的终结。它是被造物所服从的命运:连续毁灭过程,无所不包的共患难,对另一种未来的紧张而焦急的开放性。因而把“自然”看作创造,就意味着把“自然”看作是渴望解放的被奴役的被造物。过去,神学很少看到自然被安排在由灾难和拯救构成的这种历史中,神学也很少使别人接受这种概念;但也正由于这一原因,“把自然看作上帝的创造”的方案才具有现实意义。
六 简短的结语
自然神学和自然的神学都是试图综合科学与神学的努力。自然的神学更是对付生态危机的产物。对基督教而言,自然神学通过自然认识上帝,并不是通向上帝救恩的大道。真正的自然神学只是启示了对上帝的重新认识,它并不导致行动。因此,自然神学不是使人得救,只是叫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变得聪明,因为他们学会在自然中留心上帝的声音。当前,基督教需要一种新的自然的神学,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上帝,而且是为了认识自然及尊重自然的尊严,保护自然。自然神学探讨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如何推动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情形也可能相反:自然的神学探讨的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如何推动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双向互动应当被综合在一起。
今天,基督教神学也可以借助于对这样一种自然的神学的信念来重新发现创造的广度和创造的前景。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中的上帝并且尊重上帝中的自然,人们就会依照自然生活。认识自然中的上帝,仅仅是自然神学的任务;而认识自然中的上帝并尊重上帝中的自然,则已经是自然的神学了。前者不是被抛弃,而是成为后者的一部分。
自然神学的设计论一类的论证,只能作为自然的神学的一部分起到辅助作用。设计论不过是对一个可以理解的和有目的的上帝的预期而已。或然性、邪恶和人类自由的存在,使人们对全能的观念加以修正。现在只剩下一个遥不可及的和不太活跃的上帝,是来自《圣经》中同世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动上帝的远方呼喊。自然神学中的人类学原理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设计论论证——这主要是由于或然性和必然性有利于无神论。但这一原理却同自然的神学一致。
自然的神学同科学证据所要求的更一致。自然的神学的上帝并不粗暴地干预自然规律或填补本应由自然因果的互相作用来填补的自然秩序中断裂(所谓“填空的上帝”)。上帝的作用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内部相互影响的作用。在自然的神学中,具体的科学发现对神学观念的重新表述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天体物理学以外,自然的神学也利用了许多科学领域的发现。
自然神学是一种理性主义护教论。但自然的神学不是护教论,不是辩证上帝的存在,不是为神学对生态的失误辩护。它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它的重点不是上帝的存在,不是作为世界整体的极限问题,而是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问题。
自然的神学把自然提高到被神创造的高度。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因而使人专注世界。它承认世界是合理的,也是偶然的。神学当然是从历史启示和个人经验出发,但它也应包含一种自然的神学。这种神学并不蔑视或忽略自然秩序。在新正统派那里,自然是人类救赎戏剧中尚未蒙救赎的一个阶段。在语言分析那里,谈论自然秩序中的现象同谈论上帝,毫无共同之处。这两种立场把自然与恩典、非私人领域与私人领域、关于自然的语言与关于上帝的语言之间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但根据对《圣经》的某些理解,《圣经》本身对自然世界采取肯定的态度。基督徒认为,上帝是所有生命的主,而不仅仅是独立的宗教领域的主。《圣经》的上帝既是救赎者,也是创造者。这一切使人对自然的神学容易产生同情和理解。
注:
*因循习惯,本文仍将natural theology译为“自然神学”,将theology of nature译为“自然的神学”。较为正当的译法应把natural theology译为“自然的科学”(符合自然的神学或符合上帝自然本性的神学),而应将theology of nature译为“自然神学”(关于自然的神学),如同将scientific philosophy译为“科学的哲学”,将philosophy of science译为“科学哲学”,以及将philosophy of nature译为“自然哲学”一样。但为避免引起混乱,本文仍沿袭惯例。
1.Ian G.Barbour, Religion and Science《宗教与科学》,New York,1997,页89。
2.Richard Means, The Ethical Imperative《伦理命令》,New York,1969,页135。
3.F.R.Tennant,Philosophical Theology《哲学神学》,Canbridge,1930。
4.参W.N.Clarke, Is Natural Theology Still Possible Today?〈今天仍可能有自然神学吗?〉,载Physics,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Notre Dame,1988。
5.Richard Swinburne, The Existence of God《上帝的存在》,Oxford,1979,页291。
6.Stephen W.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时间简史》,New York,1988,页291。
7.Freeman Dyson, Disturbing the Universe《打扰宇宙》,New York,1979。
8.John Barrow and Frank Tipler,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人类学的宇宙论原理》,Oxford,1986。
9.John Leslie, Universes《宇宙》,London,1989。
10.Hugh Montefiore, The Probability of God《上帝的概率》,London,1985。
11.Thomas F.Torrance, Science and Access to God〈科学与通向上帝之途径〉,载《建道学刊》,1998.7(11) 。
12.Arthur Pcacocke, Theology for a Scientific Age《科学时代的神学》,Minneapolis,1993。
13.Picrre Teihard de Chardin, The Phenomenon of Man《人的现象》,New York, Harper and Row
(安希孟 学者 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