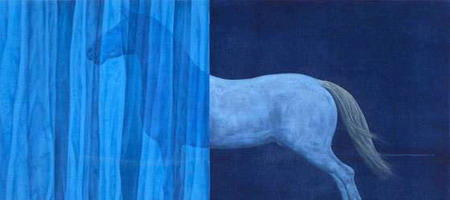概述
中国画在西方通常是指传统的中国水墨画,说到中国画就会自然而然地与遥远而又古老的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从十九世纪西方以各种手段获取的大量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被收藏在一些的博物馆里,与此同时由少数西方学者用西方艺术史学的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由此所产生的中国当代艺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艺术的一些看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水墨画在西方学术范围内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中国画没有一天停止过它的变革和发展,它所面临的传统和当代的问题,东方和西方问题,全球化和地域性的问题
等等都是当下文化乃至政治问题,但是中国画的问题被一些似乎更重要的当代艺术问题所掩盖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将在中国画的媒介,文化身份等问题上展开讨论,并举两个中国画画家个案为例,以祈对一些中国画问题的理清。
媒介问题
东西方绘画作为艺术媒介在现代艺术发展进程中似乎有相似的被边缘化问题;1985年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李小山提出了当年骇俗惊世的看法认为:“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只能作为“保留画种存在”1关于中国画式微的类似观点和理论在中国不在少数,它们大多建立在作为传统文人画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这一事实上。2
实际上中国画被边缘化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康有为和陈独秀提出的中国画写实主义的革命为写实主义油画在中国取得艺术媒介上的主导地位扫平了理论道路,3接着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半个世纪的中国艺术学院油画,国画,版画设立顺序上反映了中国画地位的失落。80年代后期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各种新艺术媒介眼花缭乱地出现和运用,加上油画在中国当代艺术里取得的成绩使得中国画进一步被边缘化。
在西方绘画作为媒介更是危机重重,早在1839年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克(Paul Delaroche)看到银版法(daguerreotype)拍摄的照片就感慨地宣称, “从今天起绘画死亡了!”上一个世纪初抽象绘画在西方的发展,到70年代的极简主义出现,绘画作为媒介存在的合理性被不断地质疑,而后绘画以外的艺术媒介如表演和装置艺术等新媒介的崛起,绘画作为媒介被不断地边缘化。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绘画媒介的危机,当李小山宣称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时候,在西方连艺术本身和艺术史统统都被宣布“死亡”。4
我们必须认识到从艺术史角度来看东西绘画有其各自发展的轨迹,西方绘画乃至西方艺术的困境首先是哲学理念上的困境,是西方哲学内在矛盾在现代社会发展下的必然产物。而中国画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展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中西绘画虽然处在同一全球化浪潮之中,它们的所面临的问题却完全不同。
“文化身份”问题
首先,与西方绘画不同中国画在全球化的艺术语境(实际上是西方艺术语境)下有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中国画这一概念是基于中西绘画的传统的不同,中国画不仅材料工具特别,它的漫长历史,整个绘画系统包括技法技巧,画科分类,画史画论,以及各历史时代留存下来的大量作品,都是独立于西方绘画之外而存在。这些相对于西方绘画的特殊性构成了中国画的特质,这些特质在当下文化环境中体现了中国艺术“文化身份”。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各种新媒介的文化认同上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媒介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如影像装置等等,这些媒介在文化认同方面自然地就与西方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感觉上像是西方的当代艺术作品从而容易被西方认同的原因之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牵涉到如何对中国当代艺术定义的问题,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其中必然会牵涉到“文化身份”这个问题。彭峰把“中国”和“当代”分作两个概念来分析,对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提出质问,并提出一个当代艺术在中国古典哲学语境下中间发展的道路。5而我的想法是对艺术作品创作过程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其文化身份。我愿意称我的方法为“麦当劳”方法或者“烹调方法”,因为我的灵感来自上海的一家麦当劳餐馆。
首先让我声明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定义不是由“谁”创作而决定的,也不是在“某一地点”(如在中国)更不是用“某种材料”制作所决定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一家麦当劳餐馆用餐,我发现所有的员工(当然包括厨师)都是中国人,后来又了解到他们用的土豆,鸡肉和牛肉都是中国本地生产,人员,地点,材料都是中国的,但是你能称“巨无霸”为中国菜肴吗?我由此联想到艺术作品的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文化性质更应该是由制作这件艺术品时用的“烹调方法”来决定。为什么众多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看上去像西方的当代艺术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媒介原因,更重要的是“烹调方法”。因为制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用的是西方的“烹调方法”,所以这些作品从本质上说是西方的当代艺术,或者从文化身份角度说是由中国艺术家在中国创作的西方当代艺术。
视觉艺术和烹调艺术(麦当劳的快餐食品恐怕不能算烹调艺术)虽然都带有自身的文化身份,但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在一些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的视觉材料如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符号等,以及中国人的形象有时是中国艺术家自己的形象等等,这些中国的符号形象本身携带了中国的文化身份,因此被认为筑就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定义。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应该怎么确定西方艺术家运用中国视觉材料制作作品的文化身份?如安迪-沃霍尔丝网作品毛泽东肖像是否能算作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它们与一些中国艺术家所作的毛泽东像在艺术媒介和个人风格以外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艺术家麦克-汤姆生的拼贴作品运用了他在中国收集的毛泽东和其他政治领袖肖像,[见图1]如果我不告诉你名字你也许会说那是中国当代艺术!我这里有一个相反的例子:美国版画艺术家戴安娜-斯蒂生用石板(litho)和金属板(etching)混合制作她的以鸟为题材的版画作品,她的构图形式是传统中国花鸟画的构图形式,仔细看完全是西方的版画手法,印章竟是美国的红色邮票,但是她的作品很“中国”。[见图2]
用“烹调方法” 法来分析中国画可以得出同样结论:即使是用中国画媒介创作也不一定因此而解决艺术的文化身份问题,因为中国画本身在全球化艺术语境下也存在“文化身份”异化的问题,90年代由老画家吴冠中提出的“笔墨等于零”而引起的长时间的争论证实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画出现了新的形式称之为“实验水墨”“观念水墨”等等,“水墨画”这个观念名称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画文化身份的淡化,“中国画”一词的传统定义已经无法涵盖“实验”和“观念”所包含的内容,我们从“实验水墨”的一些作品看已经无法用中国画自身的价值系统来判断,因为这个系统已被强行切断,大部分“实验水墨”是以西方的“烹调方法”来创作的,“实验艺术”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从艺术的文化身份角度看 “实验水墨”水墨还是没有脱离水墨媒介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中国画“文化身份”的又一失落。这不是一个想象,而是正在发生的问题,正如詹姆斯-埃金斯(James Elkins)的观点:中国山水画史是西方艺术史,因为艺术史学本身是西方的学科。6在西方还有一个不太被中国国内艺术家所注意的中国画与日本墨绘(sumi-e)的文化身份混淆的问题。水墨媒介在西方是代表东方文化的身份但通常是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日本先于中国在西方推广自己的文化,而西方很少人知道中国画与日本墨绘的关系。
尽管中国画的发展面临严峻的的形势,我认为它还是应该从自身出发,具体的说就是要与中国画的传统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有上下文的联系。如果仅是以西方方法处理结果的话就会出现如姜苦乐(John Clark)在“亚洲的隐身现代主义”一文中生动描绘的那样“布谷鸟(西方当代艺术)将蛋放在中国的“异质”鸟巢中,后代由中国的父母一手带大”7(在自然界布谷鸟的蛋孵化快幼鸟生长也快,并会将原配蛋或小鸟推出巢外)姜苦乐还提到“在欧美以外的地方如亚洲由于历史进程也可能孕育与欧美同类型的现代主义”8对于中国画来说这也许是后话,根据我对中国画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画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除保持传统以外中国画还在继续发展,因为它所体现的文化思想是具有自省精神的中国文化思想,西方艺术的现代发展史可以作为中国画发展的一个参照,由此可以回避重复,中国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走西方当代艺术走过的同样道路。
两个中国画画家个案
通过上面一些分析再回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定义问题,我想提问: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或当代艺术作品?我认为答案是有。“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提法似乎近于狭窄,但我认为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以便弄清观念上的界限。这次研讨会的一些学者如杨小彦,黄专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到了一些艺术家9,10并讨论这些艺术家作品,这些可以视为对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答;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共同之处是都以中国自身问题为艺术创作的出发点,以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些手法为借鉴。但他们是油画家,摄影家,雕塑家和其他艺术媒介的实践者,而我这里要推出的是两位中国画画家,我之所以要这样做首先是媒介的文化身份问题。如上文分析,对传统中国画媒介的运用必须是以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上下文为前提才能确定无误其文化身份,这在他们的案例里体现为除了使用中国画传统媒介即毛笔,水墨,宣纸,以及运用传统中国画技法和风格如白描或写意画来创作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传统出发而又突破了传统,同时又继承了传统并将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作品的当代性角度看他们的作品确实受到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但还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当代艺术,因为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幻想。他们的作品对当下现实的介入是中国式的,因此对于欧美式当代艺术的介入方式来说是一种对比,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是梁常胜和李津。
我想在进一步分析他们的作品之前先看两个西方现代艺术家的例子:家喻户晓的
西方现代艺术大师凡高和比加索都受到非西方艺术的影响,凡高临摹日本浮世绘版画,比加索模仿非洲面具,这些影响对凡高和比加索来说非常重要,是他们之所以在艺术史上成为凡高和比加索的关键之一。但问题是他们的创作既不是东方艺术也不是非洲艺术而是地地道道西方现代艺术。同样道理,我要寻找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当代艺术而不是“很像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朱其语)
由于我自己画中国画所以一直关心国内中国画的新动向,看到不少不为西方所知的有意思的中国画画家,这里篇幅有限仅选两位。我不认识李津,最早是在2000年李小山策划的中国现代水墨画大展的展览画册上看到李津的作品,每次我回国去书店都能看到李津的新画册,几年下来我有了好几本。我在2004年上海的一家画廊看到梁常胜的剪纸作品的画册,直到去年(2008)在北京一个偶然的碰到了梁常胜,并看到了他的水墨作品。梁常胜是用白描的方法创作,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谓司空见惯,但是对西方的观众有必要做一些关于白描方面的信息交待:如白描的对象常为人物或花卉鲜有山水,白描人物有十八描式,它与中国画写意画法的区别,与山水画里的皴的画法的区别,等等。李津继承传统文人写意的画风,这就牵涉到笔墨的问题,是一个很难与人说尤其是与西方人说清楚的问题。郎绍君说:“中国水墨画则始终不为西方人所理解,西方对于水墨画的部分接受,主要是极少数海外华人和汉学家,这种不理解主要不是在媒材,而在于它的笔墨形式,笔墨表现与文化意蕴。”11这确实是一个中西文化的难题。
不仅画法是传统的,梁常胜还用传统手卷形式进行创作,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的装裱,[见图3] 用西方的术语是“展现”(presentation)都是道地而且罕见的中国传统;他为此特地去了沈阳,找到裱画师(此裱画师的师傅是清末溥仪的宫廷裱画师)用当时的宫廷裱法,并特制一个红木小匣,加以存放,所以梁常胜的作品从外表上看特别古典而显得珍贵;一度被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在梁常胜手里起死为生。[见图4] 梁常胜用小号毛笔勾勒线条,水墨深淡略有变化,人物造型奇特但细部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因而画面看上去很细密。梁常胜的奇特人物形象仔细看有一点像他自己,他称他们为“和乐”并题画名为“极乐闲居”[见图5] 照他的解释是佛教中极乐世界的理念给了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灵感,而他为他的奇特人物取名为“和乐”是要着重一个“和”字,意思是“和谐”。这些“和乐”在梁常胜的画里处在一个光怪陆离,似梦非梦,中国式山水又有现代城市景象的环境之中,似乎与现实生活远离千里,但又似曾相识。[见图6]
我读了几篇西方批评家评论梁常胜作品的文章,几乎都谈到他一定是受了15世纪尼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的影响,12为此我特地问梁常胜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也很喜欢波希的作品,他知道波希的作品是因为有人说他的作品像波希。梁常胜问我有没有看到过山海经的插图?我觉得梁常胜的奇特人物想象方式是和山海经插图里的怪物形象有联系,[见图5-6]他的艺术灵感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尽管梁常胜的绘画风格相当成熟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而且他的探索是从绘画的内外两方面着手的;他正在画一张已经画了一年多的作品。从媒介角度来看这是一张雄心勃勃的画作,它的尺寸是一米九十宽,四米八十高(宣纸),同他以前作品一样用针尖般细的小号毛笔勾勒游丝一般细的线条。由于作品尺寸巨大,要看清作品必须坐升降机才能欣赏其全部。从远处看,由于密集的线条,作品呈灰色,加上作品本身的尺寸距离一远看上去就有点像一幅极限主义的抽象作品。梁常胜的这一尝试似乎改变了中国画的观赏方式,或者说是必需要用新的方式来观看,并且,由此而产生了不同读解这幅画作的可能性。从内容来看,这幅画里的“和乐”有了新的面貌,观者可以认出有些是中外历史人物,甚至是美术史人物,环境似乎也可以用我们对地球及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而加以辨认,但是从画面效果看还是那样地光怪陆离又似曾相识;这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中国画画家眼里的当今世界。梁常胜还告诉我他另一个创作的计划:一个宣纸裱成的巨大画镜框,用同样的方法画他的“和乐”,画在镜框上,画满,成千上万个“和乐”但镜框里没有画,对此梁常胜说道:“你能告诉我当代艺术的本末吗?”与李津的文人风格的写意画不同,梁常胜所继承的那部分中国画传统可以追溯到唐朝吴道子线描人物“八十七神仙”长卷画风甚至东晋顾恺之的线描人物风格。问题是梁常胜运用这一传统来表现他对当下社会的感受,他所描绘的“和乐”的形象和所处的环境是如此离奇但不咨为此时此刻的形象和环境。因为他的创作理念与佛教理念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的作品对当下社会的介入完全是中国式的,或者从更大范围说是东方的。
2000年李小山策划的《中国现代水墨画大展》那本厚厚的画册中包括有一百多位中国画画家,李津的两幅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原因我想是因为很多作品看上去都很新很现代,但正如本文上述过的“文化身份”问题而很难确定这些是否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中国画作品。李津的作品吸引我的地方首先是他的笔墨。从一本题为《浩大能量就在身旁》 的书里我了解到了李津的一些个人经历:他受过美术学院的教育,算是科班出身,他早期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颇得蒋兆和水墨人物画风格的神采,[见图7]有西藏生活的经历,并尝试过用藏画风格画画。大约从90年代早些时候李津开始用传统文人画的格式作画,这包括用笔用墨,作诗题画等等,他作品中的笔墨和人物造型让我想起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但是仔细看完全不同;李津受过美术学院的正规训练,虽然他的人物造型很随心所欲,但是都在解剖结构之理。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受过学院正规训练的画家往往被其所受到的正规训练所束缚,不易放开,像李津那样得文人画之趣而又不逾解剖结构之矩的实在难得。从笔墨角度说李津将美术学院素描基础训练溶化到中国画传统的笔墨中去,这一溶化在李津的作品中是如此地自然而不落痕迹,从而创造了他自己的笔墨语言,是既破又立又在其中的独特语言,他近作中笔墨更加奔放,更随心所欲,但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画笔墨。李津的这种画风可能与他的个性有关。李津对待艺术的态度可以从以下这段文字中看出:“艺术它本来就是艺术家自己的事,千万别企图对别人造成什么深刻的影响,说穿了,艺术这件事并没有艺术家自己想象的那么严重”。13李津这段充满文人精神的自白与眼下当代艺术所提倡的干预和进取的态度绝然相反,不失为一个清醒智睿的中国头脑对西方现代主义盲点所在的提醒。
李津以他自己和他的三口之家为他水墨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都是他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如打盹,吃饭睡觉,三口之家在睡觉,上厕所,[见图8] 带他妻子去医院生小孩,[见图9] 接受针灸推拿治疗,[见图10] 做爱等等,都栩栩如生,一切就像是发生在眼前。李津的绘画风格不能算是写实主义,但是他作品里溢出极其真实的生活气息,这种对生活的真实表达让写实主义油画都望尘莫及,也许这就是中国画传统中所说的那种“传神”。齐白石画虾,小老鼠,蟑螂,牵牛花鸡冠花等等,等等,把中国画从梅兰竹菊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画贴近了生活,而李津又进了一步,更紧密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从李津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画在这方面的继续发展。李津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他的真实生活,而且通过这一反映折射出当下社会的问题,引起观者的思考:他画过多幅三口之家睡觉图,[见图11]他和妻子呼呼大睡而他们的儿子却两眼大睁地醒着,并流露出诧疑恐惧担忧的表情。画中李郎(李津儿子)年纪那么小,而且睡在父母中间,没有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因为全家都在睡觉也不会是两代人代沟的问题,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贫穷,暴力等等如此无节制地发展下去,我们能不担忧吗,但是我们经常是多么地麻木,就像画中的李津和他的妻子呼呼大睡。
从题画的书法风格来看,李津也是受了金冬心书法风格的影响,有其漆书的味道。但是李津在书写时将方块字笔划的长短比例进行随心所欲的调整,同时又不逾传统之矩,和他的画一起,显露出他强烈的个人笔墨风格。题画文字诗句应该算文学范畴,李津的诗句读着像传统民间诗歌但又却是他自己的创新,并具有现代生活的内容,更有意思的是李津的题画形式;在他的“菜肴系列”作品中他将菜谱抄写在一盆盆菜的之间,填满整个画面,还有一幅他和妻子的吃鸭图,他将“吃”字写满整个画面,形成画的背景,[见图12]他的这种题画方式让中国画耳目一新。李津在笔墨风格,题材内容,题画方式,书法诗词等等方面都对传统文人画作了突破,然而,他并没有否定中国画的传统,相反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这是李津艺术的可贵之处。
结束语
2001年我在一篇短文中写道:“现代的中国画应该是传统的,换句话说,它必须与传统有相继延续的关系,同时又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对传统有所突破,具有探索性。”14 李津和梁常胜的对中国画的探索给予我们画中国画的艺术家们以启发:他们的作品证明了中国画并没有寿终正寝,传统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承载体与时俱进。他们的创作还告诉我们作为绘画语言中国画具有更深层的潜力,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是难度极高的创作,比所谓的“当代艺术”创作要难得多因为它面对的是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当代”两大包袱。我们还可以从李津梁常胜以及其他许多中国画画家的实践反思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些问题;在西方,当某一艺术媒介如绘画与艺术史的某一运动或某一段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换转成那个运动或时期的化身,当那个运动或时期结束时艺术媒介跟着一起终结,这是现代西方认识论的一个缺陷,是“单一方向发展论”或“进步论”的难以克服的认识局限。中国画的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当媒介与个人风格联系在一起时它的可能性是无穷的,因为每个艺术家都会倾注自己对时代的感受。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我们的艺术创作要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上下文联系起来,我们要对西方现代主义单一性历史发展观念进行反思,包括对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反叛”“颠覆”等老调进行审视和从新评估,我们必须改变对传统的看法和态度,中国画的历史告诉我们:传统不是发展的毒药,而是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
注释:
1 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 1985 第5期
2 水天中《进入新世纪的水墨画》,朵云第51集,现代水墨画研究,134页,1999
3 郎绍君《守护与拓进》,20世纪中国画研究,138-139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1
4 1984年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的著作《艺术的终结》(The End of Art)出版,1987年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Art? )出版。
5 彭峰《意象之路: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试探性理论》(Paths to the Middle: A Tentative Theory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本届研讨会论文
6 詹姆斯-埃金斯(James-Elkins)《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s Western Art History)Hong Kong University 2009
7 姜苦乐(John Clark)《亚洲的隐身现代主义》(Asia’s Invisible [?] Modernism )本届研讨会论文2009
8 同上
9 杨小彦《记忆的权力----九十年代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中国纪实摄影》The Power of Memory ----Chinese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s a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90s,本届研讨会论文
10黄专《什么是我们“国家遗产”?》What’s Our “State Legacy”?本届研讨会论文。
11郎绍君《守护与拓进》,笔墨论稿,210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12 他们是:朱莉-赛格菲斯(Julie M. Segraves) Asian Art Coordinating Council, 魏莉莉(Lilly Wei) a New York-based independent curator, essayist and critic who writes regularly for Art in America and is a contributing editor at ARTnews and Art Asia Pacific, 乔纳森-古德曼(Jonathan Goodman) a teacher, editor, and writer 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Asian art, particularly Chinese art. He has written on Chinese art for such magazines as Art in America, Sculpture, Art Asian Pacific, and Yishu. He currently teaches at two New York City art schools, Pratt Institute and the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戴安-特度斯(Diane Thodos)an artist and art critic who lives in Evanston, Illinois near Chicago. She is a former recipient of a Pollock Krasner Foundation Grant and has written over 60 essays on individual artists and reviews in various art publications
13 李津,宋平《浩大能量就在身旁》第4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14 蒋奇谷《蒋奇谷国画选》,画展小记,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