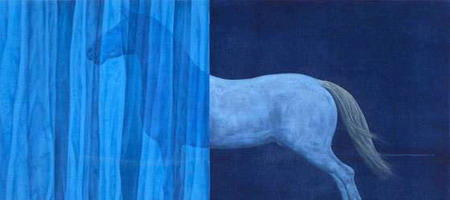一、“全球化”的背景
水墨,为什么要面对现代性的反思?“因为,所谓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1]
“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2]。“现代性”与“全球化”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与机遇。今天,脱离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水墨”的问题会使视野显得封闭和狭窄,并由于缺乏现实的意义从而不能真正的理解“水墨”的困境、其所面对的历史的变迁和未来发展的可能。
(一)当代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今天,文化处于危险中,文化受到金钱、商业帝国和重商精神(收视率、营销调查、广告期待、销售额、畅销书排名)的威胁。商业消费社会将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产品的庸俗命运,与玉米、香蕉和柑桔等量齐观,有意无意促进了文化和精神的沦落。”[3]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同样处于此种文化危机之中。
(二) “后历史艺术”[4]的谎言
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了阿瑟.C.丹托所言得“后历史时期”全球文化的一部分的。
“文化符号”对于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5]但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恰恰在于它对各种历史文化符号去价值化的“滥用”。在后现代消费文化中,传统文化符号被简单化的处理后赤裸裸地用于商业用途,其原有的文化意义被剥离了。“后历史艺术”对各种不同文化符号的大量“滥用”切断了文化符号与原有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了中国当下艺术与其自身历史文化的割裂;造成了文化符号的去价值化、去意义化和去内涵化。当代艺术从而变得更具消费价值、庸俗化和令人乏味,它体现出一种真正的价值匮乏,也使得普通大众对自身的历史和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变得更无感受性。
(三)“文明的冲突”
中国,作为非西方文明的一种,必然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非如此就不能在今天的世界中生存。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并没有产生一个完全统一的文化,非西方文明在接受了西方文明物质和技术层面的东西之后,在第二、三代人身上文化的自我意识却加强了。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6]
(四) “世界是平的”[7]
当下信息、资源、知识、财富、技术每一天都在跨越国界进行着快速的流通和转移,全球化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境遇,中国也正在这一历史情景当中寻求自身发展的机遇和可能。今天的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自身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反映和文化经验的表达。
二、“水墨”是什么?
水墨,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历史的延续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文明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8]然而,水墨,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毫无疑义的概念和理解。
(一)关于“水墨”
“水墨”并不仅仅指一种与特定媒材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实际上是指一种价值。它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士”(读书人阶层、文人阶层)——长期维系的一种价值体系。它代表了“士”的阶层长期延续的一种价值理想:忧国忧民、独立的文化人格、对学术的终生追求、对超出现实之外的虚拟精神家园的永恒向往。而“水墨”实质上是这种价值在绘画上的表现,它维系、建构着传统文化知识份子(整体上作为一个阶层)的精神归宿和价值取向。脱离了这种内在的价值,“水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文化意义。
(二)在今天,“水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今天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所呈现出的重重的文化危机,面对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商业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我们依然要问,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信仰、心灵慰藉、生活和工作的终极价值……这些还有意义么?
由于经济的快速的发展而造成的价值失落给这代人从精神层面上造成很大创伤,“水墨”所具有的价值是无法取代的。它是我们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和融合,表达我们自身历史文化经验重要方式。这取决于“水墨”——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能否更加积极地面对现代性的挑战。
三、水墨——面对现代性的反思
“水墨”:
如何能够从一种传统艺术语言形式转换为一种当代艺术的语言形式?
如何能够从代表传统社会文化生存经验转变为表达现代社会的文化生存经验?
如何能够真切地反映时代变化,与现代社会的生存环境真正的发生关系?
如何敢于面对中国两千余年来发生的最大的改变而调整自身的文化因素使其具有现代社会的新的文化特征?
如何能够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具有新的“合法性”?
面对现代性的反思,“水墨”该如何应答?
“水墨”:
能否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具有更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属性?
能否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把公共经验和个人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的表述?
能否体现正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从传统社会农业文明社会的价值向现代公民社会价值的转变?
能否继续延续和保留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独立性?
能否抗拒“资本拜物教”对一切社会领域的规训?
能否体现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价值承担”的勇气与新的批判精神?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形式(对西方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模仿),而在于价值(价值的重建)。“水墨”,对于在延续我们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建立我们新的现代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飒
2009年8月4日
[1],《现代性的后果》,(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4页。
[2],同上,第154页
[3],引自布尔迪厄《遏制野火——抵抗新自由主义侵略之言论》,选自《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河清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4],“后历史艺术”是阿瑟•C.丹托的主要观点之一,参考于他所著的《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一书,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4月第一版。
[5],《现代性的后果》,(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2页。
[6],《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第3版,第58页。
[7],“世界是平的” 观点参考自 《世界是平的》,(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
[8],《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第3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