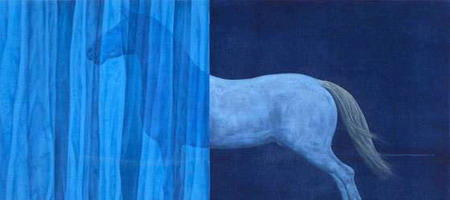内容提要:2010年9月21—22日,由巫鸿、朱青生和黄专先生主持的“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讨论议题尽管涉及“历史的反思”、“水墨与话语”、“艺术分析的新视野”及“水墨艺术的世界性”等多个角度和层面,但贯穿其中的无非还是“谁的‘水墨’”和“何为‘水墨’”两个基本问题。毋宁说是当代水墨所遭遇的双重身份危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超越狭隘的、简单的本土身份认同这样一个认识和实践误区,即如何去身份化。当然,去身份化并不是重建“水墨”的普世性,也不是迷失在艺术家的个人趣味中,而是回到艺术话语本身的实验和探索中。
且不论是否与“大国崛起”、“文明复兴”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话语有关,近年来,水墨不知不觉地成为“显学”而广受“热捧”。高名潞的“极多”和“意派”,栗宪庭的“念珠与笔触”,奥利瓦(A.B.Oliva)的“伟大的天上的抽象”,以及朱青生的“第三种抽象”,无不借助水墨寻求一条可能的中国当代艺术之自主之路。如果说在“水墨”不受关注的时代,反思与批判的阙如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一片“众声喧哗”中,冷静的思考与检省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2010年9月21—22日,由巫鸿、朱青生和黄专先生主持的“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来自美国和国内的2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了专题演讲。议题涉及“历史的反思”、“水墨与话语”、“艺术分析的新视野”及“水墨艺术的世界性”等多个角度和层面。各个角度和层面之间也并非绝对自足,很多时候是相互交叠、勾连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得出来,不论身份认同的自觉,还是重新定义的焦虑,贯穿其中的无非还是“谁的‘水墨’”和“何为‘水墨’”两个基本问题。
1.历史反思与身份的双重自觉
有意思的是,讨论一开始,三位来自美国的学者林似竹(Britta Lee Erickson)、沈揆一和安雅兰(Julia Andrews)都将自己对于水墨或中国画的观照和反思置于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框架中。
安雅兰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命题:“20世纪中国水墨画的历史是一部斗争史”[①]。从“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中国画的谴责与陈师曾为文人画的辩护,到抗战期间傅抱石、潘天寿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对抗”,直至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主义的重兴与老一辈画家重现画坛的分野,看得出来,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贯穿着这样一条同质性的话语线索,表面看似是一个古今问题,事实上已然不是古今,而更像是一个中西问题或“我者vs他者”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古今之间并无差异。也许,安雅兰是有意抽掉了古今之变而将其演化为一个中西问题,亦即身份问题。
尽管安雅兰没有明确身份问题,但在沈揆一看来20世纪中国画问题就是文化身份的问题。[②]从世纪初中国画作为民族文化概念,到八、九十年代,水墨的观念、主题、技法虽然都已远远超出了既有意义上的中国画概念,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身份及国家认同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笔下的山水、风景都已不是被看的对象,而是一种主体身份的体现。可以说,沈揆一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安雅兰论述的延续。
与安雅兰略有不同,在林似竹这里,尽管同样认为是一部变革史,但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变革方式。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前是一种被迫变革,即外界推动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为变化而变化”。表面上,“为变化而变化”似乎是一种主体性的变化,但本质上还是被外界推动的变化。看上去这与安雅兰的结论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林似竹对此则明确了自己的反省和批判态度。她说,尽管“变革始终是主旋律,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变革必然是有益的”。“在西欧和美国,恰恰是因为对于变革的强调,最终在20世纪晚期几乎将艺术推向了‘死亡’的边缘”。[③]问题是,她是看到了20世纪中国画“求变”的一面,但同时也忽视了其内在“处常”的一面。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求变”本身就是“处常”,但不能否认,作为中国画自身自有其应然的“处常”的一面。不过,林似竹似乎并不悲观,她已经发现今天至少仍有不少艺术家在“勤奋练习技法”,在默默“经营位置”。
其实一开始,安雅兰就已潜在地抛出了“谁的‘水墨’”和“何为‘水墨’”两个基本问题。在她的论述中,中国画尽管生长于中国本土,但外界的挑战本身已经意味着这样的本土化发展已不再纯粹,已不可避免或隐或显地受制于他者。因此,恰恰是越强调本土,越自觉于身份,反而越加陷于身份危机当中。但不论如何,中国画或水墨自身的演变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特别是深受现代进步论影响的20世纪,这样一种演变本质上也成了一种“历史必然”或“时代所趋”,于是,重新定义中国画或水墨也在情理之中。难怪安雅兰将张晓刚、方力钧的绘画也纳入其中。因此,如果说“谁的‘水墨’”诉诸其外在的文化身份的话,那么重新定义水墨,本质上同样是身份问题,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内在的身份问题。它不再是“谁的‘水墨’”的问题,而是还是不是水墨的问题。毋宁说今日之水墨面临的是双重的身份危机。
2.艺术语言与水墨的重新定义
安雅兰等澄清了“谁的‘水墨’”,但忽视了“何为‘水墨’”。这或许与她自身的身份以及经验有关。与之相应,在朱青生、严善錞及杨小彦这里,更加关心的恰恰是“何为‘水墨’”,而非“谁的‘水墨’”。当然,诉诸“何为‘水墨’”这一追问本身也不乏“谁的‘水墨’”之自觉。而且,不同于西方学者历史化、整体化地去审视问题的是,国内学者试图通过个案分析重新定义“水墨”。至于最终是否回到身份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朱青生先生讨论的是水墨空间问题。他认为,如果说西方的写实主义是一种三维空间,抽象绘画是一种二维空间的话,那么中国书画特别是书法是一种一维空间,即“气韵”。“气韵”的“艺术性在于它功能之外的无用性;在于实用功能(指政治意义和经济价值)之上的那种不可言说的空灵虚阔的状态”。它“既与现实无关,也与时间无关,变成一种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区别于物理空间的精神空间。因此,他认为中国书法和希腊艺术是相并行的。[④]换言之,西方理论是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传统水墨空间的。表面上看,他是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艺术语言的解释问题,但实质上背后隐含的还是如何重新定义水墨的问题,如他提出的“第三种抽象”便试图在西方固有的框架和体系之外找到一种可能。但问题是“抽象”本身还是一个西方话语,因此即便是重新定义,也还在既有的西方话语体系中。
相对朱青生先生的空间话语而言,严善錞先生所谓的线条问题则更为具体。同样,他也是通过中国水墨画的线条与西方绘画中的线条的比较和区分,强调了中国画线条自身的趣味和观念。在他看来,西方绘画中的笔触属于一种“结构性线条”,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用笔则属于一种“表现性线条”。以此审视20世纪中国画的变迁,正是在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展开的。基于对“结构性线条”的反思和对“表现性线条”的辩护,严善錞在此明确了自己的偏好和主张。诚如他所说的,徐悲鸿为了“准确”地表现形体和空间关系,线条只是起到了笔触的作用,也失去了应有的个人风格,而黄宾虹则将线条的自然趣味发挥到了极致。[⑤]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这样一种书法的“表现性线条”并没有停留在个人趣味层面上,如井上有一、王川等早已付诸与“结构性线条”的融合及观念话语的实验和探索。因此对他而言,重要的并非是能否实现观念的重构,而是线条之趣味性的自觉。
杨小彦先生以水墨人物画展开关于“公共水墨与私密笑语”的讨论。有着传播学知识背景的他更看重的是水墨人物的特征及其与社会、政治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认为,不论改革开放前的“公共水墨”,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私密笑语”,背后都有一套生产机制。如果说前者依赖于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之控制的话,那么后者则不得不“遵循现代展览制度而出场”。问题就在于,后者建基于对前者的反省和颠覆,但一旦进入“公共空间”,都具有被工具化的危险。不同在于,前者是政治工具,后者是资本工具。因此他鲜明地指出,如果“让艺术具有现代性,必须让其成为个体经验之表征”[⑥]。
看得出来,朱青生的“第三种抽象”也好,严善錞的“趣味性线条”也罢,包括杨小彦关于个体性的诉求,都意在重新定义“水墨”本身。不过三位的观点明显不同。如果说朱青生和严善錞的定义背后隐含着一种基于中西之争的身份自觉的话,那么在杨小彦这里,身份自觉则是源自对于一种“视觉政体”或“视觉伦理意识形态”及其工具性的抵抗和瓦解意义上的主体性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水墨不仅被赋予一种文化身份,还涵有一层政治权利的意义。因此他断言,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自觉,所谓“水墨性”、“中国性”都是不可讨论的伪命题。某种意义上,杨小彦的定义与朱青生和严善錞的定义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难怪杨小彦对于严善錞所谓的个人趣味可能转向公共(客观)趣味的危险性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批评。
3.认同焦虑与话语的自我重构
安雅兰、沈揆一及林似竹等基于与西方或他者的纠缠关系,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水墨画的基本演变脉路,而朱青生、严善錞及杨小彦则基于自我的立场及其与他者的区分突出了中国水墨画自身的特征及其变化。显然,他们都忽视了作为当代(即1980年以来的)水墨艺术本身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在发生着变化。
何桂彦在《颠覆与重建:当代水墨画的变迁与突破》一文中对近三十年当代水墨的发展作了相对清晰的梳理、辨析和概括。在他看来,80年代以来,当代水墨对于传统笔墨的颠覆本身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或意识形态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才逐渐进入一个自觉的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状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水墨不仅拓展了自身的形态边界,而且通过与本土文化传统的有效融合,体现了一种建立中国当代水墨价值尺度与批评话语的自觉。[⑦]如高名潞先生提出“极多主义”及“意派论”,不仅意在建立一套艺术创作方法论,也是为了形成一种批评理论话语。
周彦先生的发言“水墨·类抽象·东方宇宙观”基本沿袭了“意派”的理路,通过对陈箴、丁乙、李山等具体个案的分析,调动了内在于当代水墨中的线条、颜料、飞白、书法等元素分别加以解释,从而将其延伸至中国传统自然观和宇宙观,即老子思想中的核心或本质——“道”。[⑧]当然,这样一种解释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重新定义“水墨”,背后隐含的还是一种身份的自觉。
颇具争议的是鲁明军的发言,他试图避开以往普遍的后殖民话语和老庄禅宗话语,通过诉诸宋代“道统”即“内圣外王”话语重新解释当代水墨。[⑨]他以李华生和谷文达为例,着重分析其内在的“书写”方式。在他看来,李华生通过“反求诸己”的书写方式诉诸“内圣”,而谷文达则以公共介入的方式诉诸“外王”。如果说“内圣外王”一体的“道统”为一种“理想类型”的话,那么,李华生和谷文达尽管都偏离了这一“理想类型”,但都不乏“道统”的自觉。因此,他将其称为“当代儒家美术”或“当代士大夫美术”。不过对于鲁明军而言,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样一套话语本身所内涵的思想史叙事及其当下的反思性所指,某种意义上,重构当代水墨的士大夫精神才是他真正的诉求所在。
尽管何桂彦直到文末才提出批评理论话语自觉的问题,但本身还是与周彦和鲁明军一样,都隐含着一种“主体性或自我认同的焦虑”(黄专语)。在黄专看来,这种身份和主体的焦虑背后,可能是更大的陷阱。王南溟的质疑则更为直接,他提出这样一套“道”“禅”和“道统”话语的价值立足点何在?反思性和批判性何在?正因如此,他依然坚持意识形态话语对于当代水墨解释的有效性。
问题就在于,这是不是建基于一种身份和主体的自觉和焦虑呢?至少对于鲁明军所提出的宋代“道统”话语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强烈的诉求,首先考虑的是这样一套话语进入艺术语言内部的有效与否,其次才是话语本身的反思与批判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只是寻找另一条新的可能的解释路径,并没有取代而是丰富和拓展了既有的话语和进路。事实上,这背后隐含的问题依然是,如何定义水墨?除了后殖民话语和“道”“禅”话语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因为,不论后殖民,还是“道”和“禅”,某种意义上已经被政治化了,与其说这是以水墨定义水墨,不如说是以政治定义水墨。而“道统”话语的前提恰恰是从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解放出来,将水墨放回水墨的位置上。这并不意味着它抽离了政治,恰恰相反,它不仅是将认同开放出来,更是为了更深地介入政治。对于“道统”话语而言,重要的是水墨性及其内在的政治性本身,至于政治的具体所指如左翼还是右翼并不重要。因此,“道统”话语意在寻找一种“临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这恰恰是为了走出身份和认同的困境。
4.超越本土与主体的去身份化
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策划部Alexandra Munroe博士在发言中强调了关于“水墨”的争议。即对于我们而言,“水墨”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水墨”?她说,一直以来,当代水墨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而言是一种“次传统”,对于西方现代艺术而言是一种“次现代”,而所谓“传统艺术的当代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偏见。[⑩]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如何从其独特的“中国性”和“媒材性”这一局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启一个更为开放的话语视野。在论述过程中,她以韩国艺术家李禹焕的水墨作品为例,认为李既是西方后极少主义的代表,也充分体现了我们所谓的“道”的精神。因此,对于李禹焕而言,身份并不重要,甚至不成为问题。按巫鸿先生的说法,Munroe是站在一个世界美术史的视野提出了一个当代水墨的边界和疆域的问题。也就是她开始提出来的,在媒材上如何跨出既有的水、墨等边界,在文化地理及民族国家认同意义上如何超越“中国中心主义”。而李禹焕的艺术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Munroe是站在一个世界性的视角反思当代水墨背后隐含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话,那么,刘骁纯先生的“墨象论”的恰好相反,他是站在中国的视角,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不过他并没有回到狭隘的国家和民族认同,而是以中国包容西方、乃至世界。以至于连很多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等都在他“墨象论”的范畴之内。[11]虽然他以“以墨致道”这一哲学话语作了界定,但在实际的论述中他所谓的“墨象论”的边界反而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只要是属于“玄”或“黑”的形式范畴,都在其中。问题是,当一个概念变得无所不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什么都包不了。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站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或许还有一点意义,而一旦反过来以世界的眼光观看中国的话,那么这一纯粹的“黑”究竟还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这也是巫鸿先生对他论述的质疑所在。
显然,刘骁纯先生的“墨象论”是以中国眼光看世界。无独有偶。沈语冰先生通过比较黄宾虹与塞尚之别,意在重建中国画的现代性及普世性价值,本质上这依然是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沈研究发现,黄宾虹通过强调用笔和用墨的主导地位(物象已退居其次),进而与西方现代艺术史的主流相遇,或者说他汇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主义的主流。因此,他认为黄宾虹是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艺术自主的中国画家。[12]尚且不论这个结论是否成立,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则是因为沈语冰先生是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展开黄宾虹与塞尚的比较。[13]而形式自律本身就是西方现代主义之自主性的核心所在。问题在于,抽离了具体语境(context)而单从形式出发的比较可靠吗?正如巫鸿先生在评议中所说的,黄宾虹也好,塞尚也罢,他们在对谁说话?他们的“预想观者”是谁?或者说,他们要改造的对象是什么?如果去掉了这个前提,那么这样的比较意义何在呢?
毋庸讳言,对于沈语冰而言,与其说是重构黄宾虹笔墨的普世性意义,还不如说其真正的目的是重返现代主义及其形式自律。很简单,当我们以现代主义的眼光观看黄宾虹笔墨的时候,就像放在普罗克鲁斯蒂(Procrustes)的床上一样,不免或多或少的裁剪,以最终契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因此,黄宾虹在这里不过是证明其现代主义原则及其普适性价值的中国依据而已。当然,沈语冰的这一诉求背后,还不仅只是一种普世性价值的认同,也包括对于后现代艺术中简单粗浅的拼贴、挪用等语言方式的反省与批判。不过,单从其世界性自觉而言,无疑更接近Munroe的立场,只不过二者主张的具体对象有所不同。如果说沈语冰坚持现代艺术及其艺术自主的话,那么在Munroe这里却更具开放性,她所强调的对话性不仅只限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艺术自主和形式自律。而且,沈语冰与刘骁纯之间也不乏重叠性。不同在于,刘骁纯眼中的普世性建基于中国历史中的中国水墨,而沈语冰眼中的普世性则源自西方历史中的中国水墨。
在这里,实际上三位发言者都试图超越狭隘的本土化身份认同,但是所持的立场和选择的路径却截然不同。对于Munroe而言,其认同并没有具体所指,但明确反对“中国中心主义”;在刘骁纯先生这里,表面上超越了中国这个地理边界,但本质上认同的还是“水墨”,尽管这已经改变了“水墨”本然的界定;吊诡的是沈语冰先生的发言,看似回到了黄宾虹的书写方式,但事实上恰恰要超越中国传统绘画的本土性,而试图建构一种现代普世性。虽然三位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分歧,但都在诉诸对于水墨本身的重新定义。不管怎么样,且事实业已证明,他们的确丰富和拓展了长期以来我们关于“水墨”的认知和界定。
说到底,水墨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总是纠缠在古今中西之间。于是乎,媒材、形式、语言、趣味及观念这些艺术本身的话语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身份及定义。此次研讨会上,虽然三位主持人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不论从策划这次活动本身,还是从会议期间的演讲及零星的发言中都看得出来,对于朱青生先生而言,尽管他一直在回避身份问题,但是寻找“第三条道路”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自觉,何况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书法中的一维空间既不同于西方写实主义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西方抽象绘画的二维空间。而黄专先生似乎是纠结于身份与定义之间,或用他的话说可能是一种“焦虑”。
然而对于研讨会总策划和主持人巫鸿来说,表面上关心的看似更多是如何重新定义“水墨”的问题,但实际上其真正意在如何超越狭隘的、简单的本土身份认同这样一个认识和实践误区。也就是说,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如何去身份化。换言之,不论对他,还是对我们而言,身份问题也恰恰是当代水墨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症结或瓶颈所在。当然,去身份化并不是重建“水墨”的普世性——这实际上也不大可能,也不是迷失在艺术家的个人趣味中——这根本上也属于一种理想状态,毋宁说是回到艺术话语本身的实验和探索中。我想,这或许是巫鸿先生以“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为研讨会主题的深刻用意所在。在这里,所谓的“美术史”不仅指的是美术(形式、风格或语言)的演变过程,还指的是内在于美术中的大历史(文化、政治与社会变迁)。
参考文献:
[①] 安雅兰(Julia Andrews):〈国际化文化界下的国画复兴〉,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OCAT及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出品,2010年,第39页。
[②] 沈揆一:〈作为文化身份的水墨〉,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5页。
[③] 林似竹(Britta Lee Erickson):〈当代中国水墨画的创新之需〉,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2-17页。
[④] 朱青生:〈艺术史中的水墨空间〉,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96-101页。
[⑤] 严善錞:〈作为观念和作为趣味的线条——当代水墨画问题的一个思考〉,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02-106页。
[⑥] 杨小彦:〈公共水墨与私密笑语〉,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08-111页。
[⑦] 何桂彦:〈颠覆与重建:当代水墨的变迁与突破〉,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81-90页。
[⑧] 周彦:〈水墨 · 类抽象·东方宇宙观〉,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65-79页。
[⑨] 鲁明军:〈实验水墨中的“书写”:话语生成与思想史叙事〉,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45-64页。
[⑩] Alexandra Munroe:〈水墨争议〉,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18页。
[11] 刘骁纯:〈墨象论〉,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20-126页。
[12] 沈语冰:〈黄宾虹VS拼贴:论中国画“入世”的途径〉,载巫鸿主编:《“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27-139页。
[13] 有意思的是,沈语冰先生在论述中所援引的文献均为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如罗杰·弗莱[Roger Fry]、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等),而未见任何与黄宾虹绘画有关的材料。实际上,黄宾虹与傅雷的通信中便不乏与此相关的讨论。参见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02-227页;傅雷:《傅雷书信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7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