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打边炉ARTDBL

↑《劳动摄影》,摄影:梁荣 ©️李燎
受访:李燎
采访及编辑:陈颖
去年3月,李燎终于可以正视老婆已经辞职开始创业的这个事实。“既然这样,”他说,“我应该去做一个事情。”于是,他应聘了美团外卖的专送工作,工作目标,是为家里赚取一个月的房贷。
为了还上这一个月的杠杆债,李燎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体力劳动,并且努力把自己活成了送外卖的样子。六个月结束后,李燎像是做了一场关于打工的梦,他回到美术馆,要将梦境分泌出来,重塑似是而非的真实。
李燎的最新个展以“老婆去创业了”为题,作为“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最新一期展览,今天在坪山美术馆开幕。美术馆的一楼展厅,此刻正被一条由不同马路形态拼接而成的环形马路所包围,李燎将再一次骑着电驴在“路”上行走,沿途所见,无论是用路障组装的风车,还是大理石路墩组装的经轮,甚至是悬挂着晴天娃娃的铁丝网,都是这一场劳动的物证。而这一刻的李燎,看起来像极了堂吉诃德。
展览开幕前,打边炉与李燎进行了一次访谈。采访当天见到李燎,真人明显已经比拍摄于打工时期的照片瘦了,肤色也变白了许多,他还在戒碳水化合物,努力让自己“瘦回原样”。
以社会系统作为工作室,是李燎新的工作方法,难得之处,在于他真正地深入到了“敌人”的现场,以肉身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正因为取材过于现实,采访当中,时不时都需要从对话中抽离出来,想一想我们正在聊的是生活,还是艺术,李燎富有张力地混淆了这一切。而我们的难题在于,在真正的真实面前,语言太难以尽兴。
辞职
“老婆去创业了”这个项目,原初并不是为了展览,我在生活里确实碰到了事情。我老婆一直说要辞职去创业,而我劝了她将近两年,劝她不要离职。我的收入已经是有一天没一天了,而且在疫情的环境中,辞职确实不是很好的选择,创业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后来,劝不动了,既然两年的探讨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心,我就开始支持她辞职。我们非常喜欢相互探讨,人生也好,随便聊一些话题也好,都会聊得很透彻。更多的是我想明白了,人不能太自私,不能因为我要做艺术,我的家庭和我的另一半都得维持住稳定的收入,我们都有做自己事情的权利,然后一起承担风险。
但是,当离职的时刻真的到来,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慌,我们都开始闲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的生活事项都在不断地支出和投入。记得当时借着武汉“废船”空间的驻留邀请,我出去“躲”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我见识到了一种夸张的驻留方式,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学生,聚在一起放映、玩乐队,闲着、呆着,睡觉也没有床,我像回到了年轻时的乌托邦时代。那帮小孩,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生命一无所知,也没有恐惧,撒着欢玩。我何不更放开、更洒脱?后来,我老婆也去了武汉,吃饭的时候,我和她说了这个方案,名字都定好了,就叫“老婆去创业了”,而我应该去做一个事情。当时的情形,还挺感动的。
公器私用
“老婆”是一个原因,就像生活和生命里很多事情的启动,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我喜欢把事情混淆起来。就像她爸爸最初不同意我俩在一起,我就把她爸爸和我吵架的录音,通过美术馆混了几万块钱来交给他,以此来证明艺术还是能赚点钱。在作品里,他们都不能称为“元素”,而是主因,是我所处的真实背景。
我不喜欢空想,也不喜欢创造,我只是想换个角度看生活,艺术就是这个角度。实际上,既然艺术已经发生了,它必定也是这个世界中的现实。我在《我是正义的》里,去找仇人复仇,我打了他,而每一次展出这件作品,我都认为是成功复仇了一次,直至将他推到了大场面,这个时候,如何界定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说是生活,我说的是艺术,如果你说是艺术,它其实就是生活里的一次报复,是某种欲望的释放,释放的方式就是艺术。这件作品就是明显的一次“公器私用”,最后这件作品去到了蓬皮杜,虽然我并不认为去到蓬皮杜就怎么样,但这件作品特别需要。
拨弄
“岳父”这个因素,在《艺术是真空的》到了第三部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拿下了,他已经接受并喜欢我了。我假装找了法兰克福的MMK美术馆,伪造了一个纪录片拍摄,委托我当导演,其实是我和美术馆的勾结,写了一封信到我岳父的镇上,说德国的美术馆要拍摄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采访他,我们在洪湖上泛舟,还安排了无人机航拍。我请了一个美术史博士,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一起聊,我拿着大炮似的摄像机拍,每次拍摄都故意凑近他的脸。他特别骄傲,向村民介绍我说,这是我女婿、导演、艺术家。
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对话到底怎么达成和解,一定要勾起人们那种真实、可爱又可恶的本性,挺可爱的,我又喜欢去拨弄这些事情。就比方说,我就认为你其实认为钱和名重要,但是人们都不会承认,但是它真实存在,有趣地去拨弄,就是一个挺文化的事情。
创业
我的家庭最初的配比,是她去上班,我做艺术。我的老婆是一家服装公司的总监,而我相当于创业了,不成的概率大于成的概率。创业和赌博差不多,而这两者也和做艺术差不多,都是投入、投入、再投入,没有什么收益。创业还可能有收益,但实际上,我老婆创业这么久,和打工时的收益也差不多,还要自己去承担风险,之前,这些风险都是她的老板承担了。
爹味
虽然我老婆不愿意承认,但我在家庭里的分工,早已是家庭煮夫。因为我更闲,也不是家庭的经济来源,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带小孩和做饭,所以,我的饭越做越好,小孩的教育也管得不错。当她一定要辞职,我突然发现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但目前而言,就算她去创业,我也还是传统地认为,她在家庭里,依然还是站在了男性的角色位置上,而我站在了偏女性的位置上。我认为做艺术就应该要像厨房里的家庭主妇,不用考虑生计,也不靠艺术维生。我知道女权主义者肯定会反对,按照他们的说法,我肯定是很“爹味”的人,但其实我又是特别“真女权”的人。我认为不要过于提示优待,反倒是一种真正的平视,而不需要特别把哪一方供起来,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在心里真正地面对这个事情。我平时可以表现得很“爹味”,但同时我是一个很懂道理的人,我很知道分寸在哪里。比如我在家里和老婆、女儿的沟通方式,我妈就看不过去,我说为什么看不过去,这个家里面是她在赚钱,她就是我大爷。道理明白了,性格上还保持着我喜欢的男性特征,纯正如地里耕田的老农,这是比较舒服的状态。
私下说一句,要是我老婆以后不给我零花钱了,我就去送外卖,我现在有了生活技能,骨头都变硬了。

↑《瘦身计划》,行为、文字记录、彩色照片,2011年
收入
在强大的压力下,我应对的方法,就是去打一份体力劳动的工,用赚到的钱去还一个月的房贷。我家一个月的房贷是25,700元,而我的打工生涯收入如下:前两个月由于是菜鸟状态,平均才得到4000元左右的工资,第三个月6000元,第四个月7000元,第五个月8000元,到了第六个月,我知道已经够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多做了一个月,以纯划水的状态,最后得到了3000元。最后,扣除了饭钱和电动车成本,打了六个月的工,终于还上一个月的房贷。
通过杠杆买的房,却用没有杠杆的方式去还杠杆的债,不得不说,在当下社会,这种“不聪明”的方式得出来的结论是夸张的,虽然我喜欢这种愚笨。
时间
以六个月的劳动对应一个月的房贷,时间上的戏剧性冲突,不是我故意造出来的,我原来也以为三个月就能完成。我从菜鸟,到进入“中正班”(中午-晚上班),再到进入精英班(早班或晚班),不同的阶段都有可能决定着项目的时长。实际上,不从事外卖行业,如果我有能力的话,从事金融,时间就能缩得更短。这是时间和代价的问题。
我想要努力地快点从这件事里面挣脱出来,但同时,我又希望时间能稍微长一点,这件作品的美学,是需要付出时间代价的,如果一个月就把事情搞定了,作品就没有了张力。如果我真的很想快点赚到两万多元,把脸不要了,去和某某说请把我的作品收了吧,那不是更快?但是没有必要。现实越困难,反而越有戏剧性。两个月能搞定的事情需要六个月,也证明了我的无能,带着书生的酸苦,竞争不赢真正的劳动者。
骗局
系统搭建者的骗局,是隐性的,但却是全人类的事情。资本越扩张,越需要人提供更高的生产力,时间就会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人越来越不得休闲。当人们都需要遵守契约,一步一步地,时间需要更为明确,在末端,当我在送外卖的时候,居然要明确到30秒,30秒之内到还是差了30秒,是否要扣绩效,系统的指示都非常明确。
底薪
底薪是跑出来的,400单才能到达拿底薪的资格,而低于400单,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下个月不用来了。实际上,平均下来一天的基本要求是14单,中午就能达标,一天送30单都只属于中位数成绩。就我所在的工作站,如果一个外卖员从早到晚不停歇,一个月最高能拿到一万六千元。我还算是勤快的,但真的熬不赢他们。
大神
大神级别的骑手,经验比你好太多,但经验不占主因。为了能跑更多的单,我后来调到了早班精英组,从早上开始到下午晚高峰之前,我能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站内前五名,甚至在那个时间段里一度超过那位大神。但从晚高峰往宵夜时段,我就慢慢落后下来,因为我已经没有精力和心力去抢更多的单。晚高峰时,系统自动会派给我们4个单,大神接了四个单后,还去大群里面抢别人不要的单,这时,他一趟至少比别人多两单。他可能面临的风险是这两个单会超时,他只需要核算一下所有的单加起来是否可以承担超时的扣费。我熬到晚上10点就已经极限了,他们还处于兴奋期,早上比你早1个小时,晚上还比你至少多3个小时。
我刚开始进组时,特别想进步,就去向他讨教经验,他很热心,教了我很多,但他的眼神从来不和我对视,像隔了一层灰。为了套近乎,我想请他喝酒,他说他不喝酒,我也没见他休息过。我看不出他的年纪,有可能比我小很多。我当时的师傅问我多大,我说1982年的,他诧异了半天,感觉有点伤感,说他比我小四五岁,但我看着比他小一轮。
我有体验,对骑手来说,风吹日晒是不夸张的,特别经历了暴晒和暴雨,皮肤的褶皱会起得很快。我进去才一段时间,明显感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时候,艺术圈有开幕式,我非要去的时候,骑着电驴就去了,停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看到我,很诧异,说你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黑!
劳动阶层
如果你仔细观察,送快递的劳动阶层比送外卖的还要高一点,人说两句话,就能感觉到差别。最能对接的是保安和外卖员,这两个同阶层的角色最容易起冲突,相互都瞧不起。通常相互为难的都是同阶层的人,我遇到过太多这种情况。有时,我跟随显示的地点到达小区,只是不知道从哪个门进,保安就把我拦住,问他该从哪里进,他不说话,再问,只挥手一句“走走走”。有一次,我遇到大暴雨,到了岗亭那里,保安直接把我拦下来,很不耐烦地赶我走,我很无助,问我应该从哪里进,“走走走”“干嘛这样,你告诉我从哪里进不就行了?”“就不告诉你。”“下这么大雨,大家都不容易,你干嘛要这样?”我很生气,我还是带着一点知识分子气,一般不容易吵起来,但这一次差点就要动手了。我没骂他,只是在雨中咆哮:“谁愿意上这班,下这么大雨!”他站起来一下,又坐下来,知道我快要崩溃了,最后,还是指示我离开。
暴雨
我们最怕的就是遇上狂风暴雨。我和我老婆做过实验,她认为的小雨,在我们骑车的时候,就是大雨,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不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大雨也许还能供以欣赏,但对于骑手而言,无非就两种状态,要不就是置身其中,要不就是躲在天桥底下。穿雨衣也闷热得难受,深圳这种鬼天气,雨下一下,又停,雨衣一脱,又下。而且,下雨时的订单会暴增,都送不过来,拎着东西在雨里面跑来跑去。
也许每个时代的底层劳动者,都在劳动和生活中直面过来自自然的原始压力,这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即使是在科技进步、温饱情况变得更好的今天。在我看来,越偏底层的劳动者,越有某种韧性,不是忍,而是习惯。我的感受是,刚进来越是什么都不懂的“萌新”,越会让自己更惨,因为不知道怎么招呼这些事情。掌握了经验、技术和业务能力,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看天要下雨,就开始准备穿雨衣,有经验的工友,一看天就能判断这是一种什么雨,会下多久。他们一定能锻炼出这样的经验来,而我们这种菜鸟到后来才发现他是对的。这种“对”,就是从适应困苦当中来的。难道他能辞掉这份工作,去坐办公室吗?他没办法的,只能通过肉身和经验,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的魅力,我不想夸赞,但是它确实在应对困苦过程中,产生了独有的经验,经验本身就是魅力。
劳动
《劳动》是“主作品”,这里面包含了我的生产力工具——电驴车、我的工资条、我家的房贷信息和房产证,构成了一个证据链逻辑。《劳动》和《消费》两个作品像是一个镜像,刚好跨越十年,既形成了对应的镜像关系,也彼此交叠。
这个展览里所有的物质都只是一种辅佐,单独的一件作品并不重要,但又一定要存在,它们相互构成一种氛围,让《劳动》这件作品冷静下去。所以,整个展厅会被环形马路所包围,沥青路、人行道、水泥路、大理石路、停车场地面,都尽量按照我所经历过的那些路面拼接起来,我搞这么大动作,修这么大的风车,都是为了《劳动》里的证据得以成立。
马路
我对马路的感觉就像床一样了,大部分时候我都在各种路面上奔波,所以我才想着把马路提炼出来。我更想表现有坡道的马路,爬上两米高的斜坡再下来,每次都有种畅快感,在坡上互相遇见,还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感觉。我最喜欢骑沥青路面,特别黑、特别平,骑着特别舒服。骑得最多的是小方格子砖路面,在上面骑过,格子砖还跳来跳去的,因为砖都是松的。马路和电驴一样,对我来说都是生产工具,还有一种亲切感。
大风车
在马路上,最常见的就是路障。有一次,快下班的时候感觉特别累,骑车在路上,感觉路障也动了起来,我越骑越快,路障就像风车一样,跑动得越来越快。我一直喜欢堂吉诃德的传说,一个疯掉的勇士要与大风车决战,浪漫而且幽默,隐喻了很多层面,不只是艺术。
拍云
这次展览的作品,大概率都源自去年送外卖的经历,唯有“赞美云”这个系列,从疫情前就开始创作了,虽然当时并没有目的。我这个人,很多时候都处于比较闲的状态,喜欢看天空。我经常说,我的工作室就在711便利店,每天坐在那里只负责看天。特别在深圳这种地方,有时间看天空,本身也是幽默,也算反讽,毕竟全市就我一个人感觉无聊。但深圳的云,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看的,我决定看到好看的云就拍摄下来,赞美几句,不知不觉已经拍了好几百个视频,我还会继续拍下去。
自从有了送外卖这个想法,我以为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到路面上去拍云,结果,那段时间拍云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少,几乎没拍了。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忙于处理手上繁杂的工作,顾着看路面、盯手机、躲车、避行人,偶尔坐下来休息,也是点着根烟刷手机,再没有抬头看云的心思。在展厅里,我会将过往拍的云做成视频装置,并且溅它一身泥。
女儿情,借过
每天骑着车上工的路上,我都会哼一个调调,那调调是小时候我爸经常吹的口哨。我后来一查,那曲子叫《女儿情》。我每天上班的路上就唱,到了集合地点就停了。我经常到北环边上的科兴科技园送餐,如果偶尔不幸遇上晚高峰,那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一条很窄的路上,挤满了人,我只能骑着车一味喊“借过”,有时喊也没有用,水泄不通。
两个场景似乎没有逻辑关系,但后来发现,我当时都是一个大疆Action戴头上,一个大疆Pocket挂胸前,拍摄车头的前方。一个很松弛,骑得很畅快;一个被堵塞,停在那里喊无奈。组合起来就舒服了。
空间
我的视角需要不时抽离出来,这个状态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说的,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单一的,是由多重面向并置和多种空间叠加而成,空间在这里并不是物理概念,是生活的规则和秩序。那段时间,我白天处在所谓底层人民的世界,晚上回到我要还房贷的所谓高档小区里。日常里,这两个空间似乎是交叠不起来的,我的穿插,就像书里说到的一个例子,齐格蒙特有一次去到一个国家,从机场到地方正常需要花1小时40分钟,后来为了赶路,司机带他穿过了一个贫民窟,全程节省了20分钟。实际上,他穿插了两个平时彼此隔绝的空间。就像我特别喜欢坐地铁,提倡所有的朋友都去坐地铁。其实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不坐地铁了,最多的反馈是人太多,宁愿自己开车或打车,这就是两个自觉或不自觉被隔绝的空间,在中文词汇里,“将心比心”比较接近这个理论。
我在作品里考虑过这个空间问题,如果我设法避免进入我所在的高档小区,比如另外租一个房子,这当中不对的地方在于,这种所谓的纯粹性追求,会破坏“劳动-房贷”的逻辑性,租房子是多余的。往极致里说,这件作品不可能达到我们认为的真实,就像我其实有很多别的方法去赚这笔钱,但是我还是去做了这件愚蠢的事情。
我喜欢这种笨拙和愚蠢,不太喜欢轻巧和聪明。如果我用聪明的方法,比如多做点讲座,多卖点作品,合作一点事情,也是可以解决房贷问题的,它们就像芝麻对西瓜一样简单,形成不了作品,只能解决我一时的生活现状。那是纯粹的现实,而我喜欢把现实拉到艺术里,也喜欢把艺术拉到现实里,但我不喜欢将艺术变成纯粹的形式。
真实
我不喜欢苦情,劳动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快乐的事情。策展人时不时来和我沟通,问我方案进行得如何,在那个过程里,我都有点忘了方案这件事,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去旅游,在一些场景里,我并不愿意拿出手机来拍,总觉得掏出手机的那一刻,就已经破坏了在场的真实性。所以策展人一来问方案,我总觉得他在打扰我。
这种真实性,也许是我对“工作室”这种新的工作方法的总结。我最开始尝试在711便利店想方案,实际上,怎么想都是空想,如果要和自己的生活环境相关,我是不是应该把工作室变得更虚拟。整个打工的过程虽然产生了一些作品,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工作方式,它就是虚拟的工作室本身。在美团打工送单的过程,所有的思考都不能说是主动的,这时的艺术,已经是一种气息。
其实,我永远没办法把自己真正地当作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我知道这是他们的生计,他们要一直待在这种环境里,而我知道我总有一天是会离开的,我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就是把时间尽量拉长一点,人尽量努力一点,不知不觉,我的肉身也经历了真实。我没有和他们提及过我的目的,辞职的时候,站长挽留我,说疫情马上来了,马上封城了,是一个躺着捡钱的机会。他想不通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辞职,而且居然还为了“艺术”。搞社会调查,应该是他们对这个行为和目的所能理解的极限。
我不是社会学研究者,我想让自己变成我认为中的他们,包括从体型、神态和关注点上成为真实的“他们”,再来观察我自己,而非抽出一个样本来。只不过,我经常会把自己抽离出来,去理解这件事,我也在克制自己过于发散。
我老婆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送一下外卖,你看你现在脾气多好。我们的确经常挨骂,而不还口。有一次我请假要去打疫苗,在车上,我老婆听到站长打电话来骂我,语言很难听,她差点要骂回去,被我拦下来,她很诧异,我居然能做到这个份上。要达到真实,就不应该是旁观者,应该正式地切入进去,越辛苦,就越畅快,越被压迫,就越觉得有所收获,越忘记我的目的,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件我该经历的事情。
语言
底层劳动者的语言通常粗暴而直接,特别是底层的管理者,好像会故意倾向于粗暴和辱骂的方式,还有,他们在规则上极度地细致。可能他们接触到太多的人,粗暴对他们是有效的,管理上极度细致到把人当成没有思考能力的白痴才是有效的。
语言有时候确实表现出来了阶层感,不只是说话的语言,也可能是在快手、抖音里看到的一些拍摄语言。经过修饰的语言,来自于教育后的共识,语言的措辞不一样,说话的方式也就能一下就看得出来说话者所处的阶层。如果说语言带来某种优越感,是来自阶层固化的结果,礼仪和趣味也一样,这是天然的,如果一直不被打破,就会走向城府状态,再也不能说“妈的”了。时不时还是应该去刺一下这个气球,稍微给它放一下气,不是消灭它,实质上,语言带来的空间区隔,正在成为某些商品的本身。
自卑
趣味来源于一种天然的自卑,自卑是很有趣的东西,为什么要自卑?因为格格不入,型号配不上。然而,正是因为型号配不上所产生的多余和挤压,才是我认为的有趣。我可以回避自卑,努力依附城市的趣味,但又因为我的倔强和选择,我不回避,故意把问题放大,把挤压的空间加大,让它变成了超越现实的现实。如果我回避,我会觉得我很不争气。
城市的趣味,就像语言上的区别,比如我从老家来,平时可能都把生殖器挂在嘴上,到这里来,你开始鄙视我,我收敛,但同时我还会嘲笑你,吐你一脸。毕竟我要继续待在这里,如何找到平衡?我学习你,同时你也要被我弄一下。
我们不能被自卑打败,但同时也要承认自己的自卑。城镇的位置特别尴尬,不完全是农村,人都没种过地,而镇上正在模仿着城市,什么都有,你以为镇上就是城市,瞧不起乡下人,但当你来到城市,才发现自己农民也不是,城里人也不是。这种拧巴里,其实有一种空间,它不用像农村的土根,又可以不被城市中某种国际化的审美趣味所规制,与城市性拉开距离,这里的空间就变成了复杂性。向往城市的同时又在反思,又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中国当代艺术的表现力,很多都来自于郊区和城镇。
肉身
当工作室背景是整个社会系统,我提炼的方法,首先是把范围缩小。如果对象是整个社会,其实待着家里就够了,以往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从社会中、从新闻里去找一个敌人,找到巧妙的方法去应对它、反抗它,而又不触碰红线。越到后面,反抗的对象过于具体并不是好事。如果说我关注的是资本本身,以及背后的国际关系、生产力关系,我的方法首先是缩小范围,把肉身放置进去,以肉身的体验来讨论关系,讨论空间叠加之后产生的心态,讨论事物在正常的维度里,突然掉在另外一个维度里,会如何改变,这种荒诞和人、和它的背景构成什么关系。如果不缩小,它面临的问题是二元化的,而我现在想把事情做得更复杂,但在表达上变得更简单。我把范围缩小到美团,因为这是很明确的体力劳动,下一次,我可能每天去山姆会员店门口坐着,或者进去里面逛。
体力劳动
画廊、美术馆,在我看来都是虚假的行业,像是戏台,对我而言没有真实感。我认为的劳动,是剔除了脑力劳动后的极端化体力劳动,这种劳动纯度更高。去工地搬砖可能会更纯,但这个时代最方便的选择是送外卖。现在我所能听到的,都宁愿选择送外卖,而不愿意选择进工厂打螺丝。但是,对比了送外卖和进工厂两种劳动,我发现还是进工厂舒服,送外卖比在工厂劳动累不是一点半点。工厂车间都有空调,无非就是乏味,外卖的忙,眼睛是看不到其他东西的,只能盯着手机和路面,记着订单有多少。更多人选择外卖,是因为工资幅度跳跃性很高,只要你愿意干,工资还是可以媲美很多白领,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更自由,它似乎提供了更开阔自由的空间,让人看上去像自由主义者一样。
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工人,技术的有效性已经不同往时。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工人的技能是有用处的,熟练的工种不容易被取缔,还有可能获得职称。现在的工人,培训三天就可以上岗,我在富士康里,看到每天1500人进来,1300人离开,对工厂而言都无所谓,只要再上一个机械臂,工厂就更不怕人员的流动。这种流动,就像他们不行就去送外卖,送外卖太累就去当保安,受气受够了,还可以到工地上赚钱。只是后者更危险,更辛苦。
杠杆
原始劳动力和杠杆社会之间的鸿沟是无法愈合的。城市的解决方案,是让年轻人来消耗,到一定的时候回老家盖房子,这应该算是好事,起码现在老家的房子都修得挺好的,虽然人们都还是愿意留在城市里。
实际上,这个展览,本身也是另外一套杠杆。我以愚蠢的方式做了《劳动》这件愚蠢的作品,那么,如果我按照一年房贷的价格将它卖掉,是不是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杠杆的操作?如果将它定义为艺术品,肯定是可销售的状态。杠杆是不可能以兢兢业业的劳动去对应的,既然是杠杆,它就要借力。我愚蠢地去打工,看似没借力,如果我借艺术这个支点,把它通过美术馆放大,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益,再来还所谓的房贷,我是否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愚蠢?我只能清醒地说,一定程度上,我也是系统的搭建者。
电驴
我长时间骑电驴之后,有一次需要开车出去办事,坐在车上,我感叹道:“还可以吹空调!”刚开始骑电驴的时候特别开心,因为感觉离地更近了,更空旷,时间一长,尤其经历了日晒雨淋,观感就变了。
电驴是城市里面的毛细血管,它能去好多地方,又不用担心停车问题。虽然有危险,也不享受,但我现在有时候还是喜欢骑电驴,它太方便了,多数时候,通勤可以通过电驴解决——通勤和享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电驴的危险系数并不高,真正遇到危险的,还是外卖行业的人,并且是系统导致的。我试过好几次,单与单之间的距离太远,预估的时间不够,这时,肾上腺素就会突然爆出来,已经看不到红绿灯,只要前方没车,我就冲过去。大部分时候闯红灯的,他手里一定是有单的,这是最容易出事情的时候,这是来自系统的压迫。
很多城市在建设的时候,并没有为非机动车预留位置,当需求突如其来,城市的架构已经稳定了,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工具,这种突发需求侵占了城市道路的使用习惯,在一开始甚至处于相当野蛮的状态。管理者是溜不过生态的,生态要形成的时候,只能去疏导和适应。深圳已经在改变了,我看到的是一些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相对变窄,挪出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城市不断地在与人调适。
我有几次迫不得已把电驴骑到了机动车道上,也被罚过好几次,一次50元,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的,打工的时候,我特别节约钱,为了想办法吃得又便宜又饱,我跟着工友们去吃特别油腻的快餐,十三块钱就能吃饱,当时胖了一大截。
餐饮
外卖行业已经完全颠覆了餐饮业,很多时候,不是店主找外卖员来送餐,而是外卖行业开了很多店,餐饮店这时已经成为了淘宝上的店铺。大部分的餐饮,基本上就变成城中村里有一个小门面,没有堂食,来的都是外卖员,只做午高峰和晚高峰,其余时候关门。餐饮往后发展,就是工厂里面出来的半成品越来越多。这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求人们更快速投入到生产。有的店为了迎合外卖模式,专门设计了餐厨动线,餐饮商业生态的设计很生猛,尤其在深圳。
毋庸置疑,他们对于时代的敏感性和想象力比艺术家强多了,艺术家的智商不适合创业,艺术家只是敏感,出不了解决方案,艺术家也脆弱,在前端站不稳,还是应该稍微与现实隔离一下,因为不在行,对这个世界没有那么懂。
小区
有时候,从路的北边到南边,穿过小区很快捷就过去了,围墙导致了无止尽的绕。大部分时候,小区的围墙讨论的都不是安全问题,而是在表达领土意识,将小区变成了区隔的空间,用以区别阶层,不希望外人进来,在电梯里,也不希望和送外卖的人坐一个电梯,我实在没有办法共情这种事情。
邻居
原来都说,多认识一个邻居是好事情,远亲不如近邻,时不时可以帮忙一下。现在却是不用互相帮忙的时代了,美团点个外卖就解决了。就算同住一个小区,同住一层,也不会成为邻居。要真因为有需要去找邻居,你也会觉得欠了邻居一个情,而你的邻居,不一定介意你的打扰,倒是可能会担心你尴尬。这种担心,居然变成了一个事情。如果给邻居送个礼物,想要建立关系,他可能会理解,但他会尴尬,因为已经没有这套系统,这套系统也没办法靠一个个体来形成习惯,可能要靠将来的某个APP来解决。
网络
外卖行业,是网络生活的外延,相当于触角,通过虚拟达到了真实。现在的人过得更加孤绝,更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所以需要越来越多的服务,最后可能连外卖员都会见不到。实际上疫情以后,已经形成一个习惯,外卖直接搁门口,连人都不见了。网络的,尽都网络了。
时代
从岳父作为因素开始,到《瘦身计划》《成为更好的人》,再到《劳动者》,是我在不同阶段,对外部的反应和思考。《劳动者》所记录的我身材上的变化,就像变色龙一样对当下环境产生了应激反应,形成了保护色。在《瘦身计划》里,我用十年前的生活费,在武汉同一个地方生活一个月,身体自然就瘦了。现在回想起来,《做更好的人》那个时代,似乎是最好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蒸蒸日上的状态,为了让自己更好地匹配资本的链条,努力工作、创业、健身、学英语,宁愿去欧洲旅游,也不情愿去黄山旅游,生活和前景充满了无限可能。当下的《劳动者》,真是机缘巧合,中产阶级居然去送外卖了,这不无意中隐喻了某种时代关系,“哦呵,你得靠这个了!”
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在潜意识里,我的确认为现在不是创业的好时机,已经不是《做更好的人》的年代了,虽然只隔了两年,周围所有人的心境都变了。就像我老婆现在给另外的公司供货,但那些公司极有可能垮掉。现在两个月就能垮一个公司,起来很快的公司垮得也很快,人不再像从前,将一个事情慢慢地做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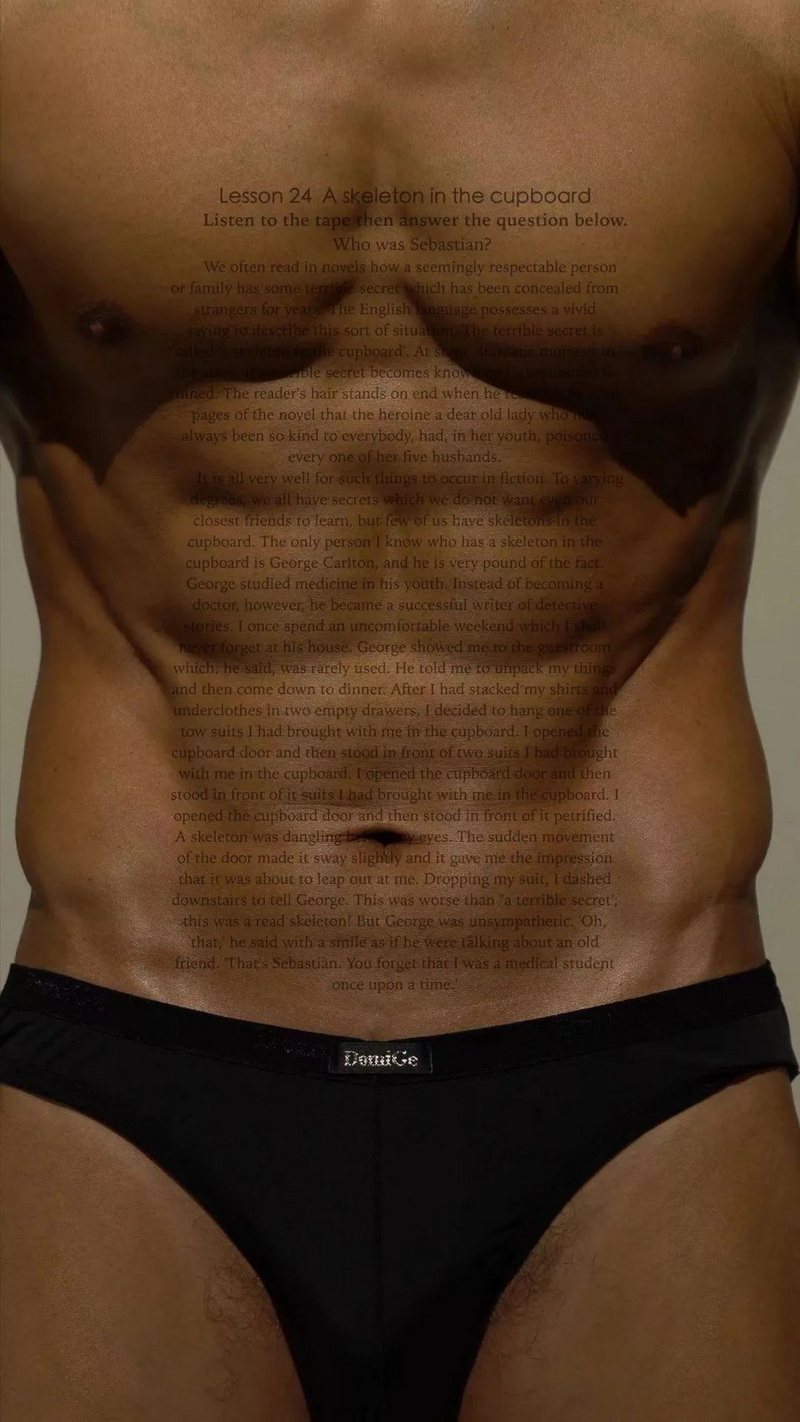
↑《做更好的人》, 行为、单频录像(彩色、有声),189’45”,2018-2019年
中产阶级
人们回到了求生的本能上,所有的事情都在放大。房价不涨,而且处于阴跌的状态,想脱手不可能,还要继续往里面填房贷,相当于是在亏钱。中产阶级反而是最苦,中产阶级最容易上套,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从前我认为中产阶级是比较有优越感的阶层,甚至产生了一些规制和形式感,我带着讽刺感地去学习它,调侃它,但中产都要去送外卖了。
作品直接反映出时代,因为直接取材于时代,工作方法就是把自己放在时代里面,这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不会过时,也不会超出时代的想象,整个链条,什么时候有幸能全部弄出来,实际上它和历史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劳动者》,行为、彩色照片,2022年
亚克力
送外卖的过程,本身就在观察深圳。我2010年来到深圳,从最开始的生产,到产业升级,它确实按着自有的逻辑在发展,置身其中感觉不到,回过头来,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人们从前很务实地提高生产力,后来发现要提高消费,就只冲着消费端去使劲,以至于从崇尚生产转向崇尚消费和金融。产业升级之前,深圳就像亚克力一样实用,很扎实,坏掉了,再压一块直接就能替代,永远都处于实用的状态。现在越来越像玻璃、铝合金不锈钢的样子,在材料上升了级,却更偏形式。
分泌物
事件在美术馆的再现,就像是一场分泌,而且分泌出了一个不太相关的事情,虽然元素看似来自现实,实际上,更像是做了一场打工的梦,醒了之后,把梦里面的东西去做一做,看能不能跟梦境接得上。所谓的采集,就是视角。不是别人看不到,就像空间与空间的区隔已经存在了,视角就是空间的穿插,通过艺术,我把这件事情穿插到另一个空间,然后抓回来再放到美术馆的位置里。我的选择,都是在当下我确实看到了它们,它们在路面上就已经很美,直接拿过来就好了。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