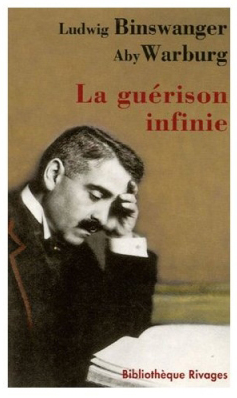
艺术史学家Aby Warburg(1866-1929)德国艺术史学家
《精神病学、想象力、与艺术》
之前通过法国文化处订购图书,好处是不用支付昂贵的运输费。忘了哪一期Art Press介绍新出版的文艺类图书,其中一本引起我的注意,很快就下了订单。
这是一本精神病学记录,由零散的通信与笔记节选组成。书名为《无望的痊愈》(La guérison infinie),我的译法不一定妥当,却可能比较贴近原意。书的作者,即为精神病学医生Ludwig Binswanger和患者本人Aby Warburg——两位都是20世纪心理学及艺术史学界不可忽视的学者。
且不说Aby Warburg在20世纪西方艺术史中的地位,他的精神状态本身,就已成为诸多学者口中的家常,甚至成为艺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说的更有噱头,不妨援引那个著名的例子。
1918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末期。一日,Aby Warburg仿佛受到强烈打击,他持枪威胁家人,声称自己是导致德国一战战败的原因之一。此后,1921年,Aby Warburg被送往由医生Ludwig Binswanger主持的精神病疗养院。所有人都认为他情况严重,并实施治疗。其间,Aby Warburg也有表现正常的时候,但医生始终认为,这位在艺术史研究上禀赋出色的学者,却最终不可能从自身精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精神的负荷——如果那是一种疾病——将永不可能得到治愈。
为了证明自己的精神状态适合研究,并且具备研究能力,1924年,Aby Warburg在疗养院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当时的环境原因,听众只有疗养院病人)。他所作的演讲主题为“蛇之仪式”。Aby Warburg不满足于当时艺术史的主流研究风气,对西方人自身所持有的文化优越感颇感厌恶,于是在1895年至1896年间离开欧洲,来到美洲,与少数民族部落Hopi人居住在一起,在那里进行研究。
Aby Warburg大概当时也没想到,这些原始Hopi人的文化,竟能为他苦思不得其解的某些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壁画提供关键的启示。在Hopi人的蛇舞仪式中,Aby Warburg看到了古希腊酒神狄厄尼索斯的力量与原型,而西方艺术的某种精髓,难道不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阐释的那样,并非来自阿波罗太阳神般理性的光辉,而是酒神迷醉癫狂的时刻?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即使被理性的力量占据了主体,但对作品的解读,往往在细节处无法进行下去。
Aby Warburg相信这样一句话:Le bon dieu se niche dans le detail(真神栖身于细节——我的翻译,我的最爱)。正是对佛罗伦萨壁画细节的关注,Aby Warburg在其中找到了栖息的狄厄尼索斯精神,把他从隐蔽所中拉出来,将阐释整幅作品意义的入口启开。
Aby Warburg是西方艺术图像志学的开山之祖,帕诺夫斯基继承并发展了Warburg的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但是,关于Aby Warburg对酒神精神的关注,却从帕诺夫斯基的文字中抹去了。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志理论在二十世纪受到追捧,但也很快受到抨击。过于理性的为象征、图像、符号规定意义,图像志理论适合于功用明确的宗教艺术作品,却解决不了艺术与非理性不可避免的挂钩。
Aby Warburg始终受困于某种精神危机,并且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研究体系。他致力于一种文化的哲学,但又受困于“文化”本身如何阐释。这是一个混杂的概念。西方文明与历史始终致力于文化的纯化论,但现实是,文化是一个可怕的杂交儿(métisse),除了它的光鲜外表,其下隐藏着不可言喻的黑暗力量。这个杂交儿可以优雅、得体的与人交谈,也可能突然掀翻桌子,像一个陌生人那样动怒,失去理智甚至做出骇人的举动来。而艺术,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不可避免的要将一只脚伸进那片幽暗泉水搅动。在人类理性光辉闪耀的文艺复兴时期,Aby Warburg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看到了隐藏的非理性力量,以及它们在形式上的表现。
在某种程度上,Aby Warburg的精神危机源自一种对非理性进行归类具象的不可能性。对非理性进行思考,其实是对人类想象力进行思考。而想象力在不同文化、历史的背景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运动轨迹。思考想象力的能力之一,便是超越常人的想象力。
在精神医生Ludwig Binswanger的眼中,Aby Warburg无疑是一个病人,但却是一个史无前例、极具挑战性的病人。对Aby Warburg的治疗,本身也是精神病学研究拓展的轨迹。Ludwig Binswanger医生在精神病学领域同样抱有雄心,正如Aby Warburg那“文化的哲学”一般。
今天,当我们试图说起文化哲学一词时,也许卡西尔的《人论》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平台。合理的看,我们无疑要放弃那块不可进入的晦涩非理性地带,让人类在理性可及的范畴内,探讨人类知识的能力、与极限。
艺术家的存在意义,如果这么看,仿佛又是明晰的。
回到那个被人无数次提起的轶闻——Aby Warburg持枪恐吓家人、并自认为引发了德国一战的失败。事实上,在《无望的痊愈》一书中,我们会看到Aby Warburg在发病时,怎样怀疑所有人,怀疑医生、护士都在谋害于他。也许,Aby Warburg的悲剧在于被自己的想象力所害。但又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这是一个绝顶聪慧的犹太人。犹太思想家的卓越,我们有目共睹。Aby Warburg作为艺术史学家,本身也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Warburg家族是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著名的金融家族,作为次子的Aby Warburg自幼痴迷图像与艺术,于是放弃家族金融事业的继承权,只请求兄弟们能够满足他的一个要求:为他购买所有需要的书籍,以便进行研究。也许是对艺术与文化的着迷、对根植于每种文化深处的狄厄尼索斯精神的难以离弃、对这种酒神精神显现的追问,最终导致了Aby Warburg那永无止尽的追问,那不可完成的“体系”。
在《无望的痊愈》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始终回荡着:痊愈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想象力无药可救,它是快乐的源泉,也是某种绝望的种子,它并不渴望痊愈。思想本身是一场冒险,在这一点上,它需要想象力,但又要逃脱想象力的阴影。艺术与思想是一对姐妹,驰骋癫狂与清醒克制,在永无止尽的交换角色。好的思想家,是一个心灵的艺术家,他的绝妙之笔,在于用理性的文字透视最不可理解的区域。而一个好的艺术家,在内里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只是他的手,更听从的是心灵。
疯狂的尼采提出“快乐的知识”,也许这才是必须理性的人,所可以采取的最明智的态度——在我们能够成为艺术家之前。
何蒨 2008-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