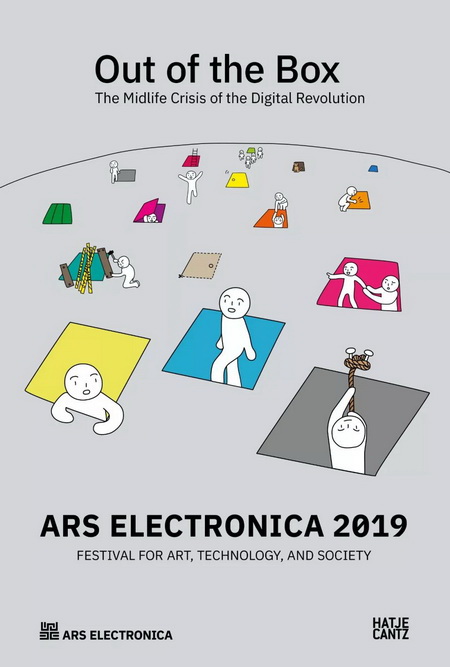[新媒体实验室系列专辑-序]
从 DorkBot 到 FabLab:新媒体实验室的文化版图与影响
撰文:PEI(2012)
「文化版图」,这是单一国家文化的野心事业?还是支配盲众的布局?在资讯与网路主导的当代文化,「文化版图」这个名词必须被重新解读。文化的形成可以是由一群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世代,不分母语,不分地域,不分信仰的人,因为致力于分享共同的兴趣或话题,透过网路快捷分享资讯,渐而形成的文化演进并创造知识。世界上多数国家历经工业革命后期,一战与二战的影响,1920 年代后立国的基点,就从来不再是以农立国,转而被工业、商业或政治运动等各种意识型态所取代,人们与自然界循环的关系被人造文化切割,线性时程上一个不可必免的进程。
暂且不论阿姆斯壮在月球上踏出一小步的全球连播是否为冷战期美帝极权设计好的阴谋论,2012年初夏,美国SpaceX公司发射第一艘商业用火箭「飞龙号(Dragon Capsule)」,正式开启了太空商业化的时代。首航任务其中之一,将308名梦想家的骨灰送上外层空间,洒落于日夜星辰间的收费行动,每坛3000美元,再次向世人证明,科技可以是实现个人亦或群体浪漫幻想的工具,科技可以是绑架人类共同资源及利益的利器,科技可以是知识的体现,科技可以是协助人类更了解自然和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催化剂。但我们如何定义这些擅于运用科技的族群的文化活动?如何重新定义媒体?又是否急于将文化定义于特定框架中?
公元 2000 年,地球公民的生活中还没有 facebook,没有 google map,没有创用 CC 智权条款1,台湾艺文补助项目里也还没有科技艺术2或跨领域的属性,当时纽约歌伦比亚大学电脑音乐中心的助教道格拉斯.罗沛特3发起了 dorkbot活动,不定期地、自发性地举办电子艺术创作分享,主旨只有一句标题 「People Doing Strange Thing With Electricity」。各类型创作者,研究员,业余玩家在此发表未完成的点子、已完成的作品,无厘头的幽默、只要跟「电」有关就好,或许是朗读一首关于电的诗,或许是分享最新的程序编码制作的数位互动。客厅沙发般轻松的环境,对各类型创作的包容态度与有趣的内容逐渐得到认同,从小圈子里传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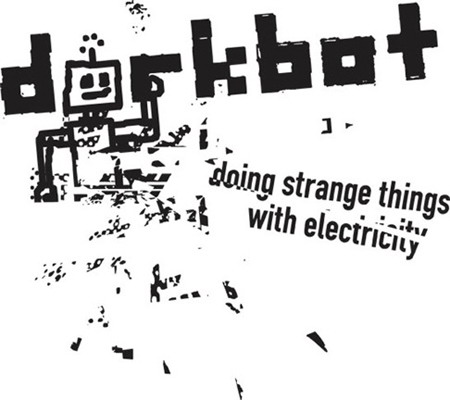
图:截自dorkbot.org
地球村里的 dorkbot活动于2004年前后在欧美各地达到高峰,这个学院内发起但非正规组织内的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发表,早期透过网路次文化之间的irc及mailinglist口耳相传,并欢迎全球各城市也在当地举办类似 dorkbot活动,正是如此开放的态度,自由心证的认同方式,无须缴交会费,年费,加盟费,名称使用费,旨于创意与技术分享的草根文化,截至今天为止,全球五大洲除了南极洲以外,已有106个城市不定期举办dorkbot,又因为每个城市文化背景的不同,举办dorkbot的型式,排程,组织,目的与地点也不尽相同。无论举办的地点是艺文替代空间,学校,社区文化中心,客厅,酒吧,咖啡店,各地 dorkbot的聚会中,业余玩家、卧室创作者与学者的交集,工程师与艺术家的交流,社会运动者、骇客与哲学家的交错,这样的人文风景及其传达的概念已经转化为一股对 Do-It-Yourself (DIY) 电子艺术创作分享的力量,并在社会面,科技面,艺术面都带来深远的影响,间接地体现当初网路发明者对于知识分享无界限的愿景。
影响中华民国早期教育思想至深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学者约翰.杜威在「艺术即经验」4一书中,延展实用主义以应对生活的变动衍生的实验主义,从经验中学习知识,应用于生活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与美的感知是经验的过程,美的经验是动态的过程5,艺术并不应是单纯物化的产物,美的观点也不该定论为主观或客观的二分论,艺术的体验应是连结主观与客观的过程。这些观点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虽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但2012电讯时代的今天,得到越来越多新媒体创作者与教育者的共鸣。
分工过细的分析派理论建立的学院体制造就了知识的象牙塔,专制且深奥,成就了精深的科学学问之外,促成了知识连结的断层而走入死胡同。当学院内的组织变成箝制知识发展的绊脚石的时候,看似草根的自己动手来DIY,各领域知识的混搭、融合,发展出来的remix文化效应,以实验精神出发的跨领域蔚成显学,不怕出错的实验精神为主轴,重新绽放;好奇心驱使的、有趣的、好玩的过程,重新探索知识的可能。这种看似毫无方法学基础的文化效应也逐渐地重新回到学院内,知识发生的环境变因种种,重新受到重视。在台湾,跨领域的一小步似乎走的小心翼翼,在艺术的范畴中,多媒体跨电子、电子跨舞蹈、舞蹈跨多媒体是当代艺术好声色的形态转换,多以可物化的产物为出发点。换个角度想,哲学跨舞蹈、舞蹈跨生物、雕塑跨太空、太空跨电子艺术的天马行空,背后的应用知识与技术,何以纳入艺术与文化的执行范畴内?
近年来,全球文化界的一个有趣现象,这些科学与艺术间从未间断过的对话,间接产生了许多开放、半开放式的讨论与活动空间,多以某某实验室XXLab以代之,无论是OpenLab、NewMediaLab、HackLab、DanceLab等等,遍地开花,席卷文化界。无论是实体的空间与组织、虚拟的网路平台、艺术节里的实验室、更或者是以教育为主的工作坊,多强调手动经验可以是创造知识与艺术的楔子;研究始于文化,而这样的名称假设了文化进程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使艺术不再制约于产业中的一个项目,而是知识的经验。而这些以实验室为名,行之认真玩乐的过程,看重的是不同领域的方法与应用,方法可以被重新利用6,应用也能重新衍绎,这不就是创意吗?
然而,学院内已制定的方法学,并不完全适用于此类自发性的实验室,并有违实验精神的开放态度。那么,「研究跨领域方法学」的实验室,或是「研究实验艺术工作坊操作方法」的实验室,例如: workshopology 7的存在也就不奇怪了。实验室Lab里的活动,蜕去由上至下的组织方法,凝聚兴趣的分享空间所创立的新媒体实验室,区隔了一般公共空间里因异他性产生的疏离感。参与者多来自不同的背景及专长,无论对主题的掌握度深或浅,来到实验室中,所有人共同的印记是对主题的好奇,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笨问题,因为有问题,一个社群进而共同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正是多数实验室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参与此类实验室活动的人所思考的方向,不应局限于xx界与xx界的对话,更应思考跨界或越界练习的问题核心,界限从何而来?界限又是如何被制定的?
FabLab – 以开放社群技术分享为设立宗旨,意思是大门必需是开放的,并非以赚大钱为目标的制造实验室。如一个小型的数位创制工作坊,提供在地社群一些平常看似高科技,且必须由电脑控制的各项数位制造机器与工具,相关的操作及设计课程,例如:电路版设计与制作、感应器运用、3D塑型机 (俗称 3D印表机)、镭射切割器应用等等,并研发 DIY各种机器与实体工具的可能性,挑战新素材的创作。

FabLab 图标,截自wiki.fablab.is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FabLab的概念「How To Make(Almost)Anything」最初由 MIT物理教授奈尔.葛杉飞发起,全名为Digital Fabrication Laboratory,简称FabLab。目前全球已有89个FabLab 的驻点,31个正筹备中。这可不是什么国际品牌进驻的新自由主义活动,FabLab 的驻点应由在地发起,跟进FabLab社群分享的目标并提出驻点计划书,尔后才能使用FabLab 的图标(Logo) ,若有需要再透过当地或国际间的教育或文化基金会申请补助,协助驻点的设立,其中缩短城乡数位差距当然是许多补助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欧美不少驻点的FabLab 都设立于科技学院、国高中之内,延承奈尔主导的
FabLab Academy,落实以数位程序撰写来创作实体对象「Learn to Turn Codes into Things」。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驻点都需具备昂贵的机器,除了已开发的先进城市、开发中的城市之外,阿富汗、伊索比亚、哥斯达黎加、秘鲁、埃及、印度尼西亚或日本乡间的小镇也有依文化背景适用的FabLab驻点。
接下来一系列的专栏中,我将介绍并访谈全球活跃或具代表性的,自发性的新媒体实验室。从艺术面,社会面,科技面分析当今全球媒体实验室的形成与影响,探讨过度制造的当下,消费主义当道,各个媒体实验室的动机与创意,其社群的连结与创作力,以及对于未来蓝图的远景或批判。参与自发性实验室的人多多少少都抱有一个共同的小秘密,知识无价!
注释
1. Creative Commons, http://creativecommons.tw/
2. 国艺会自民国 93 年至 95 年间以“科技艺术发表专案”型式特别补助定案,往后不分媒材纳入“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或”创作“等常态型补助。
3. Douglas Repetto, http://music.columbia.edu/~douglas
4. John Dewey, Art As Experience, Capricorn Books, 1934/1958
5. 张蕙慧,论杜威美学与国民小学音乐教育,页 5, 台中教育大学学报:人文艺术类 2011.25(2), 1-16 (http:// ord.ntcu.edu.tw/post_study_download.php?sn=227)
6. Repurpose 重新利用
7. http://www.kiblix.org/kiblix11/?en/symposium.html
作者简介: PEI,声音艺术家,电子艺术活动策动者
http://www.little-object.com
http://playaround.cc
新媒体实验室系列专辑(一)
艺术史的不意外: Access Space (UK)
撰文: PEI(2012)
当代艺术的语境下,艺术史一词的英文正确用法应以复数名词套用。当代艺术史学者及策展人强调以西方艺术为主轴来探讨当今的艺术内容是不正确的,单数的Art History 通常是为一个既定的框架中的延展,直指罗马文本中理性美的延伸与呈现。然而,作为一个名词的统称, 复数的Art Histories 一词更适于探讨当代艺术的复合本质,更贴近普罗大众对于当代艺术既定框架的认识,是从单一文化框架中移转至不同文化发展包容性的可能。过去50多年来,当代艺术史研究者努力地从艺术发展的纵轴时间线、横轴地域化分等,认识各门各派的发展及学说,而此广义的交流也必须在字面上的语义表明出来。某些无法一一细说的场合,艺术爱好者与学者更应自觉地使用艺术史(复数)一词,代换各个文明区域发展出的艺术与文化内容的存在,是为对艺术与艺术史的尊重与了解。单数复数的名词、这微妙的细节在中文或许多东亚语言中是以更细腻的量词表示,但这让情况更加尴尬的是,遥远的东方的我们,谈论艺术史相关的论点时,粗浅的一分为二之,那有东方的,这有西方的。东方的当代艺术抓着西方艺术的丝线努力地捆住一个着力点,然而欧洲文化的历史包袱就像姥姥的裹脚布一样,又长又臭;这让体制内的艺术发展好似堵塞住了的沙漏,不运动,细沙的速度不知是停了,还是不正常地慢上一百万倍,至今多是如此。
近一个世纪的一战前后,不想待在沙龙里为框而画的艺术家们辗转“自我放逐”到新大陆后,又哀悼着瑰丽图腾般的欧洲文化,这群在牛仔、罪犯与野人国度里的新移民,他们骄傲地继承了欧洲传统的理性批判,天时地利人和且精明如杜象,端出个便斗,美名为“喷泉”,Ready Made的概念从此改写了欧美艺术的发展史。这样的励志故事转了一手又一手,提升至一个文明的假象,成了一则寓言故事。至今,很多人自愿地当这个寓言故事里的机器人,大张小张的买着安迪.沃荷所复制的这个美国梦。而真的复制品所能带来的快乐,其也是艺术物质化的一部分,是待价而沽的工业品。艺术非物质化的那一部分也通常不怎么讨喜,却是无价的必需品;没有了这一部分,何以称之为一件艺术品?如果复制一张糖果包装纸的经验可以是艺术的过程,与其直接买下没有灵魂的复制品来缓和被物质欲望撕裂的伤口,何不回归原点,以传递技能为主旨,透过回收材料再利用,让个人能动手复制一个经验,再将经验中习得的知识传授给他人?英国的access space对于回收,特别是电脑设备回收有特别的做法。

截取自access-space.org
谢菲尔德 (heffield),位于英国中部三河汇流的城市, 英国的第一个钢铁大城,也是现代工业革命的起点。access space 新媒体实验室/社群空间的创立人与电子艺术家 詹姆士.华本克(James Wallbank)在1997 年一次革命性的展览1,以大量电脑装置为创作素材的装置作品,敏锐地讨论电子记忆体容量和工业过剩的累积是同步地以正比成长,这样爆发性的批判,在谢菲尔德(Sheffield)重工业转型的环境下得到相当大的回响。他说,当时以电脑实体为创作素材也相当麻烦,电脑不是一项便宜又随手可得的素材,但当时半导体及作业系统软体研发的速度正值巅峰,人们,特别是公司行号里有需求,追求更快、更新、可安装更大记忆体容量的电脑,一个小毛病或系统更新就淘汰尚可工作的电脑,汰换下来的电脑又因舍不得丢,堆在仓库间或地下室里永无天日。詹姆士透过电台记者访问的机遇,发起废弃电脑的回收,展览一个月后,出乎意料之外地收到了将近170台左右的回收电脑,这么多免费的创作素材,这下问题才开始。
尔后,詹姆士与伙伴们在市中心废弃的厂房区租了一个便宜的空间,存放这些回收电脑的同时,建立 access space 开放社群空间和新媒体实验室,积极以行动来回应自己先前的作品,而两年后在阿姆斯特丹的The Next 5Minutes 研讨会中发表 “低科技宣言(LowTech Manifesto)”2。从这时起,access space力行实践低科技宣言,不相信创意必需被企业宣导的高科技框架限制,欢迎任何人来帮忙整修,互相交流回收电脑的软硬体问题,并开放给任何有需要的人取用。人们可以从回收的硬体里 DIY拼凑出一台完全可用的电脑或其他电子器材,虽然没有人会拼好一台送你,但 access space 社群里随时都有人回答你的问题。想学电脑却没有机会的人也走进来了,整理好的电脑都重新灌上 Linux 作业系统及其他开源软体3,从基础的文书、美编到进阶的各种程序撰写、影音创作、3D动画皆可用回收的电脑操作。access space 社群如同一个微小的社会,渐渐地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学生、老奶奶、失业的数学家、领救济金的中年人、妈妈带来的小朋友、艺术家,待业的移民等等,每个人都有些故事,都有些技能,都有些点子可以分享,只要不是带有敌意或攻击性的干扰,access space 欢迎任何人。2012目前正迈入第十二个年头,英国最悠久的开放实验室,尔后更发起 “零元手提电脑宣言(Zero Dollar Laptop Manifesto)”4,回收并重新调整第一世界快速淘汰下来的手提电脑,转送至世界其它角落有需求的人。

截取自access-space.org
2002 年詹姆士访问巴西的一次演讲,分享了 access space 回收电脑创立开放社群空间的实例,这样的概念由巴西圣保罗当地的年轻人酝酿发酵,两年后,”Metareciclagem(Meta-Recycling) "5在巴西约有百余个电脑回收点/公共社区中心,听的詹姆士好生羡慕。而藉由回收硬体,开源软体应用的结合,这样雷同的概念在不同文化里形成的差异与回响引起我的好奇,笔者电邮访问詹姆士,问起回收电脑在台湾的现象以及开源软体在英国艺术圈的现况。(以下P为笔者,J为詹姆士。)
P: 文化上来说,台湾的电脑设备及电子产品日新月异,过度浪费的情况是很普遍的,然而,对于一些没有收入的族群来说,回收是他/她们的正职工作,台湾又该如何反思 “Low Tech” ?
J: 主要的问题在于你指的“回收/recycle”是什么,如果你指的是 “把设备拆开依材料分类(Break it down into its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那么就是低技术的回收,低收入的工作。但如果回收是以“ 诊断,修复,再利用(diagnose, repair and repurpose)”,那么就是高技能的工作,需要专业,技术及知识。我们相信这样的工作就算不赚钱也是值得做的,因为透过这样的过程,从零到累积,能够更进一步习得科技进展相关的深入知识,透过实做的练习,建立技术与机会,提供创意发展的可能。整个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产物并非电脑,而是“回收”。
P: 就你的经验,一般艺术圈对于开源软体的应用抱持何种态度?(有人在乎吗?)
J: 开源(open source)在英国的创意圈中已经开始成为一个被认可的概念,许多人对于开源其无限的可能性抱持着很大的兴趣,但同时,许多艺术家很紧张,认为他/她们的作品会被复制。这似乎兴起两个科技相关的艺术家族群:(a)不作批判的科技拥护者6 ——这类型的艺术家大多喜爱用最新的苹果电脑 (几乎都是), 自称不须要也没兴趣真正了解他/她们的作品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喜欢数位科技的“魔法” ,用此机制来制作或发布数位内容、录像、声音或其他产物。(b)批判数位的执行者7——这些艺术家不倾向于制作“数位内容”,但对于数位媒体的本质与/境更为有兴趣。他/她们创作的方向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附产品,可能性,或社会性的介入。这些艺术家的想法通常围绕着开源(open source)或开放文化(open culture)的概念。
当今也是有些艺术家从事着与科技无关的创作,在那,分界是混合的。某些艺术家完全了解分享与共创的精神,认为在这样的框架下发散他/她们的作品是正面的。这些艺术家知道,他/她们能在专业领域里继续创作好的、高品质的、有创意的作品,而无需永无止境的不断搬出旧作来宣示。同时,另一些艺术家很担心自己的创作被抄袭或转用,认定不自由的智慧财产权才是保护生计的王道。通常这些艺术家对于智慧财产权的理解如一片飘飘欲坠的叶子,很不牢靠,反正大多也不怎么成功!
注释
1 Size Matter, http://lowtech.org/projects/sizematters
2 http://lowtech.org/projects/n5m3/
3 Free Libre Open Source Software - FLOSS 中文又称 “自由软体”。
4 http://zerodollarlaptop.org/
5 http://www.metareciclagem.org/
6 The Uncritical Technophiles
7 The Critical Digitally Eng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