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少斌
简介
1963年 生于河北省唐山市
1983年 毕业于河北轻工业学校美术系
1991年 迁入北京圆明园画家村
1995年 迁入北京通州小堡村
个展
2000年 柏林亚洲艺术工厂 德国
2001年 伦敦中国当代艺术画廊 英国
2001年 巴黎Loft画廊 法国
2003年 Pruss & Ochs画廊 德国
2004年 北京现在艺术画廊 中国
联展
1992年
《首届中国职业艺术家联展》北京阿芒拿画廊
1992年
《现代艺术展》北京友谊宾馆
1994年
《8+8当代俄罗斯—中国前卫艺术展》香港SCHOENI画廊
《94新潮流》香港会议中心
《竹帘后的脸—杨少斌,岳敏君画展》香港SCHOENI画廊
《94年亚洲新兴艺术展》香港艺术中心
1995年
《5+5来自俄罗斯—中国的声音》香港SCHOENI画廊
《95年艺术潮流》香港会议中心
《展望中国—当代中国油画展》泰国
《岳敏君,杨少斌近期作品展》香港SCHOENI画廊
《北京三人展—杨少斌,张弓,岳敏君》香港SCHOENI画廊
1996年
《中国现在》日本大阪
《中国》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 德国
《中国》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
1997 年
《中国油画史—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GALERIE THEOREMS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馆
《中国现在》瑞士巴塞尔
《中国》KUENS TLERHOUS奥地利维也纳
《11位前卫艺术家画展》香港SCHOENI画廊
1997-1998年
《8+8-1》15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油画展香港SCHOENI画廊
1998 年
《当代中国七人展》NIKOLAUS SONNE FINE ARTS德国柏林
《5000+10》西班牙比堡
《是我》北京太庙
《中国当代艺术》瑞士鲁塞恩MEILE画廊
《两性平台》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河美术馆首届收藏展》深圳何香凝美术馆
1999年
《通道》沈阳东宇美术馆
《中国当代艺术》美国旧金山LINM画廊
48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 意大利
30届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 瑞士
2000年
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
《皮肤与空间》意大利米兰当代艺术中心
《未来》澳门艺术中心
《基本生存展》汉诺威2000年世界博览会 德国
《身体破坏和脸》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工厂
《我们的中国朋友》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美术馆
《当代中国肖像》法国佩里格密特朗美术馆
2001年
《映像与描绘》格拉兹博物馆 奥地利
《梦》红楼轩 英国伦敦
《煲》奥斯陆艺术中心 挪威
《宋庄》不莱梅美术馆 德国
《架上样板》成都双年展 中国
2002年
《妄想》温瑞精神病院 荷兰
《10年回顾》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 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足球世界杯》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雷克雅未克艺术博物馆 冰岛
《长征》昆明上河创库车间 中国
2003年
《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雅加达国家美术馆 印度尼西亚
《剩余的世界》Pirmasens 展览中心 德国
《曼海姆新艺术展厅2》德国曼海姆
《压力》日内瓦 瑞士
《生存的向度》广东美术馆 中国
2004年
《身体-中国》马赛当代艺术博物馆 法国
《被禁止的感觉》密特朗美术馆 法国
《我;20世纪自我肖像》巴黎卢森堡博物馆 法国
《桥》慕尼黑西门子论坛 德国
《中国人》普坦萨博物馆 意大利
《痛》匹斯堡麦克·伯尔本画廊 美国
《组织》纽约托马斯·阿本画廊 美国
《中国-古巴》加利弗尼亚美洲文化中心 美国
杨少斌是中国当代绘画与自身语言资源、社会趣味和艺术潮流的一个有意义的个案。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中,杨少斌最早是作为玩世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出现的。不少他的画作充满了暴力,但是他的暴力并没有像很多年轻的观念艺术家那样局限在暴力本身,相反,在无数次对于扭打的抽象化描绘中,通过单纯的绘画语言,暴力回归到本质,它们是身体对身体的攻击。本书精选了他的著名代表画作,展现了他的不同的艺术创作时期的思想及领悟,以飨读者。
杨文斌无疑是当代中国艺术中重要的一员。通过仔细地分析他创作的各个阶段,我们发现他的艺术从创造那一天起就是处在艺术潮流变革的中心。其艺术的动力不在于他积极介入潮流,相反,它们存在于艺术家内心世界与知识准备和艺术潮流与体制之间调和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中,作为一个诚实和成熟的艺术家,他的策略是不断发现这些断裂,沿着自身的逻辑改造和演进自己的资源-——即使他们有时和潮流是冲突的。也正是因此,纵观杨少斌的创作,我们发现了一条少有明确的线索,在这个线索中他从观念回复到绘画性本身,由从绘画性本身发现自己的观念,并不断丰富它们。
艺术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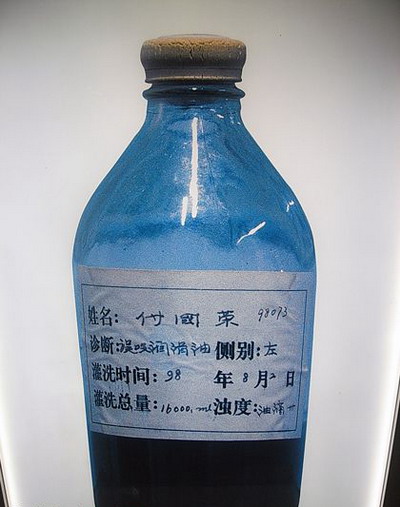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