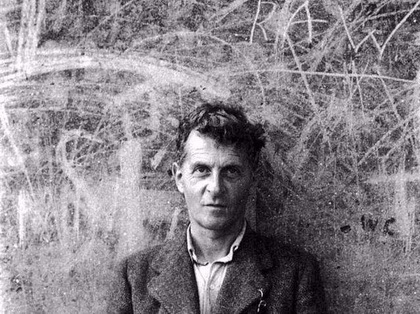文/夏开丰
我们已经知道“艺术”这一概念并不是确定而不变的,经过一种转换,特别是进入乔治·迪基所描述的“艺术界”,能使所有的事物转换为艺术。当然,之所以把一些东西确定为艺术那是因为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的 “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我今天关于赋予其价值的“作为艺术的艺术”的论述也难免带上那种由语境和身份决定的影响,比如我在此概念中更多地秉承了先锋精神。但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我必须先与唯美主义者所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作出区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概念更容易导致一种封闭性,常常忘记它的历史与社会动因,把赌注都压在一种自足的形式中,这样更容易致使艺术概念的僵化、艺术形式的装饰化以及缺少自我批判。而“作为艺术的艺术”这一概念,前一个词“艺术”是对后一个词“艺术”的突破、更新,希望能保持两个词之间的那种批判性的张力,而推动艺术穿越体制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壁垒继续前进。此概念已不仅仅在探讨“什么是艺术”,而更是在追问“艺术是什么”。
但在我们的时代里除了“作为艺术的艺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与之相混淆的艺术——“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两个概念一直处在同一个范畴下(即艺术之名下)使用而至今未得到过细致而明确的区分,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混乱,保守派、激进派,民众与当代艺术的隔阂都是这种混乱下产生的副产品。在我试图对这些由来已久的积怨作出澄清时,我们不得不提到格林伯格早在30年代末写成的那篇敏锐的文章《先锋派与庸俗艺术》,由于光从题目上看容易引起本文所讲的东西已经在他的文章中得到了阐释这个误解,因此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分才能继续我的论述。我所要阐述的与格林伯格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所说的“庸俗艺术”更多的是流行的商业艺术,包括广告、插图、封面、黄色小说等等,适应的是都市的消费文化;而我所讲的“作为文化的艺术”除了包括格林伯格所讲的那种“庸俗艺术”,也包括民间艺术,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那些曾经是真正的艺术经过“文化化”后,或者说被体制化之后而进入文化领域的那种艺术。尽管格林伯格模糊地讲到了这点,但他把“庸俗艺术”看成是相对固定的领域,它向真正的艺术借鉴技法、诀窍、策略等,而他未尝考虑到真正艺术自动地“文化化”,甚至庸俗化这一现象。也就是说格林伯格更多地从雅和俗这两个概念来划分艺术,我却要拒绝这种传统的做法,因为雅的艺术并不必然是属于真正的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权力话语。
由于我是把先锋派当作是“作为艺术的艺术”所产生的一种“互文语境”,因此我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总是频频谈到先锋派,我在使用“作为艺术的艺术“这一概念时,一方面是在描述一种现象(恰好等同于先锋派),同时也在提出一种方案(试图克服先锋派的困境)。
一
首先我要从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开始我的论述:可读的是不可写的,可写的则是不可读的。此话准确而简明地概括了写作中的悖论,可读的即是已进入体制中的作品,不可读的则是还未被体制化的东西。那种可读性就是艺术的“文化化”。更多的人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艺术、评价艺术,任何对此种阈限的跨越都被看成是一种背叛与亵渎,即使论及创新也更多地是局限在该范畴的自身逻辑中。
一个人遵照毕加索的模式画的一幅画算不算是艺术?回答是,那不是艺术。因为艺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毕加索的画在当时是艺术,而现在还有人这样画就不是艺术。当然决定它们已经不是艺术了则是由于“新”的东西的产生,阿多诺正是把新异这一概念来作为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雷蒙德·威廉斯这样说:“在新创造、新建构方面,创造力就是一切:一切传统的、学院的、甚至习得的模式,实际上或潜在地都同它敌对的,都必须被扫除掉。”[i]
先锋艺术正是在这里获得了产生的契机,先锋艺术在这种反对传统中获得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在这种反传统中我们必须联系“自律性”的概念才能对先锋派的意图有所了解。“自律性”即指艺术作品具有自身的规定性,从康德的“审美的无功利性”这个观点中就可看到自律性概念的来源。彼得·比格尔认为最终由唯美主义开始了艺术的体制化,自律性成为资产阶级的范畴,而艺术与生活实践的脱离则成为资产阶级艺术自律的决定性特征。格林伯格等人就拥护这种观点,强调纯粹的形式,他们从传统的“内容决定形式”或“内容也是某种形式”这个命题中解脱出来,而把问题置换为“形式即内容”或“艺术的内容是艺术”而获得艺术自治。但由自律性引起的艺术扩大了与生活之间的距离,艺术作品逐渐流为形式主义、装饰化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先锋艺术家们的不满,正如比格尔所论述的先锋派希望重新把艺术结合进生活实践当中,那么已经体制化了的“自律性”概念自然成为他们需要予以抛弃的东西。
在与“自律性”有关的论述中,我们绝不能忘记阿多诺的观点,“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艺术凭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ii]。在阿多诺的思想体系中,艺术是被视为一种对世界的拯救力量的,“由于没有能力把进步的解放趋势置于历史现实中,批判理论家们被迫到审美领域去查找否定力量的替代性源泉”[iii]。
阿多诺将这种否定性力量或多或少给予了“自律性”,虽然阿多诺将自律性看成是艺术的双重性之一,但在他的论述中也在隐秘地透露他之所以看重艺术的自律性的原因正在于它是反抗资本主义的“非同一性”力量,正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切事物均是为他者的,“艺术的这种社会性偏离是对特定社会的特定否定”[iv],从而使艺术也代表着同“理论和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迫”相对应的某种救赎形式。[v]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阿多诺与先锋派的某种汇合之处,在阿多诺那里正是因为艺术自律与社会的非同一性而得到重视,在先锋派那里自律已成为资产阶级体制化的东西而必须加以扬弃,其实都是对同一化倾向的拒绝。而两者各自的局限在于,对阿多诺来说他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自律被体制化以后艺术作品所失去的批判性诉求而逐渐形式化,自律性开始成了对现实的虚假否定,而对先锋派来说面对的是由于艺术作品失去了自律性原则而逐渐混同于生活这一问题。
也许“自律性”这一概念从一开始的提法就并不准确,我们需要重构一种自律性。虽然并不能说为建立一种自律性而使内容沦为形式的“残渣”,但内容必须是被形式“劫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张力,也限制了两者各自逃逸。因此形式必须有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洞孔”,正是通过它自律性才不会沦为自我封闭,保证艺术的发展,代价是就像俄耳甫斯带欧律狄克离开地狱时要做的一样,形式不能回过头来看内容,形式只有通过“洞孔”才与内容保持一种建基于语境之中的联系,两者具有永远的“不可通约性”。只有这样,形式才能完成对内容的救赎使命,假如艺术保证不了这一点,它就难免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淖之中。
阿多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更把自律看成是艺术对自身本质的挑战,“新异”被看成是自律性形成的场所。“对阿多诺来说,新是一种冲出现时的允诺性的、甚至是一些不同的乌托邦冲动,涉及到艺术自律性,新是通过传统的明确否定的艺术自律性的构成之所”[vi]。
阿多诺将新这个概念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因此他是把新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从而确立了现代主义是否定性的这一概念,而且这种否定性是区别于前现代主义艺术的,“昔时,风格与艺术实践为新的风格与实践所否定。然而在今天,现代主义否定传统本身。如此一来,便把资产阶级进步原则的影响延伸到艺术领域之中”[vii]。
有意思的是尽管阿多诺坚持自主的美学,但这不影响他仍然明确地指出新异与商品的一种同构性,艺术盗用了这一经济范畴,即一旦商品停止提供新的东西,就将会失去竞争力。而彼得·比格尔批评阿多诺的这种等同,因为在商品社会中新异范畴只是表面的,“如果艺术只是适用于商品社会的这一最表面的因素,就很难看到它怎样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适应来反抗这个社会。在那里,很难找到阿多诺相信他在艺术中发现的、并迫使人们不断采用新形式的对社会的对抗”[viii]。最后他认定作为阿多诺美学的核心概念“新异”范畴并不适于描述先锋艺术,它也没有提供一个区分时尚与历史上必要的新异的标准。
比格尔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必须对阿多诺的观点抱有同情的态度。阿多诺之所以强调“新异”以及与商品的同等作用,正是由于“艺术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异律性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艺术本身的自律性充满商品社会的意象”[ix]。也并不是说阿多诺没有意识到新事物会沦为时尚这个弱点,他说:“新事物乃是对新事物的渴望,而非新事物本身。这正是所有新事物的祸因。”[x]而比格尔的忽略之处在于自律性是新的必然诱因,新是自律性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自律性由于与引入新这一范畴而得到了重构(一个反例是,文革时期的艺术多么貌似先锋精神,彻底地反传统,崇尚“破旧立新”的理念,然而没有发展出自律性概念而最终流入说教性与工具理性之中),“新艺术可以通过包括一种反自律性的要求而独自建构它的反传统的自律性”[xi]。而“作为艺术的艺术”这一概念则正是在此处插上了它自己的旗帜,但它在此处必须回答由比格尔提出的现代艺术对“新”的强调而导致趋向时尚这一难题。“作为艺术的艺术”与时尚都强调对“新”的渴望,但两者本质的差别在于:前者总感到自己与它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因此它试图从未来中找到突破点来对抗这个已麻木不仁的时代;而时尚总能认可它所处的时代,并且试图处处与时代相吻合,它所崇尚的“新”停留在大众消费心理之上。
二
后来的先锋派并不明确再提新这个范畴,与现代派不同的是,现代派由于强调“新”而跑到了时代的前头,而先锋派是想跑在时代的前头而导致了“新”。从这来看先锋派的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新而带出来的结果的滋养。使得先锋派能够把整个传统以及艺术本身他者化而使自身抽离出来获得了历史意识而来思考自身成为可能。并且恩将仇报地将新和自律性这两个概念实体化为被体制化了的艺术而加以反对,同时也将新这一范畴改头换面为一种“陌生化”以抵抗自身被体制化、被“文化化”而最终成为一个历史范畴的趋势,先锋派的本质决定它是最不愿意成为一个历史范畴的,而作为文化的艺术则是一个历史范畴。很明显,先锋派并未停止对新的渴望,但正如有人所说,先锋的幻觉之处在于它以为只要将过去清除出去,新会自然而然到来。
由于先锋派的任务在于将艺术重新结合进生活实践中,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并非是最重要的使命,先锋派重要的使命在于引进一种叫“陌生化”的技巧对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事物的突然侵凌而造成一种震惊的美学效果。(正是这一种方法被后来的后现代主义者用一种折衷的方式发展)。这样的结果便导致了先锋艺术自身的辩证否定,阿多诺认为,这才是高级艺术应具的品质,只有将一种“必死性”纳入自身之中,才会够得上真理性概念。也正如安德鲁·韦伯所言:“先锋艺术试图去坚持一种立场,但这个立场又必须是临时性的,它一被规范下来就必须被超越。”[xii]先锋派相信正是这种“临时性”或“必死性”才能使得艺术得到绵延,而这种“临时性”就是“陌生化”的保证,或者毋宁说,“临时性”就是“陌生化”。先锋派吸取了现代主义的教训用这样的策略将自己的“房子建立在流沙之上”(马尔坦·多尔曼语)而反抗体制对艺术的不断的“文化化”,在该体制中,先锋艺术遭到了双重束缚:一是作为文化的艺术对它的掠夺而被平庸化(如进入学院、研究机构等);另一个是体制对它的限制与压迫。
我们从“先锋”一词的本质上来看,它自身之中就已经包含了反叛、突变的精神,对新的可能性的实验也是它本身的逻辑结果,但对那些已经获得了历史意识的当代艺术家来说,还是要把先锋一词实体化、历史化而早早地宣布了它的死亡。彼得·比格尔认为先锋派困境的最早征兆在于震惊美学的无效性:“震惊的美学有着一种它与生俱来的困难,即它不可能使这种效果永久化。”[xiii]结果震惊是可预期的了,陌生变为非陌生,震惊被消费了,先锋艺术可以被归类了,而逐渐滑向了文化领域。而在另一部分人看先锋派的死亡在于它已穷尽了自身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太过于笼统,过于把先锋派风格化了,先锋派所包含的阈限要远远大得多。卡林内斯库是少见的一个将先锋派的死亡内在化为先锋派自身的:“否定要素在各种艺术先锋派的实际纲领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表明,它们最终是在致力于一种全面的虚无主义,它们的必然结局是自我毁灭。”[xiv]
其实先锋派的死亡以及对先锋派的扬弃和重新寻找另一种可能性仍然是属于先锋派的,尽管先锋派理论存在着很大问题,甚至有先天不足,但在艺术领域中我们除此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另一种能够被称为理论的东西了。一般而言,我们不能轻易讲先锋的死亡,但将这种先锋还原到历史上,我们发现先锋确实存在着死亡的迹象。吊诡的是先锋派的终结之处恰恰在于它还未等自身进入文化之后就开始否弃自身了。这使得它自身变得过于抽象化,还未确定敌人是否出现,它自己就先四处开火,结果人们只记住了这开火本身,形式没有劫持住内容,而先锋派得以架构的基础如反叛、陌生、震惊等等都暴露在外,而逐渐被体制化,使得先锋派毫无新意可言。另外对未来的信仰和对文化的拒绝使它进入一种完全虚无主义的世界,对文化的虚无态度也是对自身的虚无态度,不能成为一种文化,那么新就毫无意义可言。先锋派得始终记住一种否定辩证法,先锋艺术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反对文化的东西。在这里让我想到了利奥塔的“到来”或“在吗?”这概念正好可以来说明先锋艺术的这种特点。利奥塔似乎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先于存在者这一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到来”先于“到来者”,“它(思想)试图确定已被思考、写作、绘画和社会化了的东西,为的是确定尚未被思考、写作、绘画和社会化的东西”[xv]。在艺术中,新事物的到来看似任意其实并非如此,它首先要确定已在的事物,然后才能使未在到来,也就是说艺术始终在追问“在吗?”这个问题,它所朝向的是不在场的事物,这样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这样的话“(艺术作品)主要是一种交互参照的极其复杂的话语中的参与者。”[xvi]
而在那种否定辩证法中,先锋艺术的悖论就被深深地揭示了出来:无论多么隐秘,能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对先锋派最好的褒奖。贡巴尼翁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一书中认为先锋派的悖论在于它的历史意识,“两个矛盾的基本点构成了先锋:解构与构建、否定与肯定、虚无主义与未来主义”,“先锋则意味着对未来的某种历史意识和在时间上抢先一步的意志”。[xvii]
从这里来看,先锋派并非是不想成为一种中心的,但它的本质决定它不能接受与占主导的艺术形式保持一种同一性而得到认可,它必须要以自己的价值建构(即它最初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面目)来获得一种主导。易英先生已经在他的《前卫与边缘》一文勾勒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那种对抗与转换的模式。
波吉奥利在他的《前卫艺术理论》一书中认为前卫主义者也要妥协与调整,与时代的主流文化配合,而这些则需要通过潮流的推动,所谓潮流“就是把原来(一分钟之前)异常或反复无常的东西突然接受为一件平常的东西,待它成为每个人的“东西”,变成平凡之后马上又抛弃它”[xviii]。波吉奥利并未细讲为何要抛弃它,但仍可以从他的一句话中推测出来:“但是对现代的艺术来说,尤其是前卫艺术,最大的错误就是重复模仿、走入传统的艺术创作。”[xix]古典大师创作出了“刻板型象”,而现代艺术也无可避免地产生这种型象。艺术必须抵制这种固定型象的庸俗化倾向而拯救艺术,正是在这一拯救中艺术重新爆发它的乌托邦潜力。正如诗人庞德把艺术的美解释为“从一个陈腐艺术进入另一个陈腐艺术中间所呼出的一口气”。
但当我们联系到刚才所讲的先锋派的隐秘的欲望,就可以发现制造这种“刻板型象”为取得一种权力话语却是必须的(其实也是建立一种新的艺术所必须的),正如易英先生所言先锋艺术“在摧毁了古典主义的权势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势”。[xx]古典主义通过确立它特有的价值体系(往往强调一些技巧来设置一种准入制)不断地再生产它的权力话语而形成一个特权阶层,以艺术的名义其实是将一种文化的东西扩展出去而成为一种普遍价值。虽然先锋派已经对形成一种普遍性抱着怀疑的态度,但它还是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要解释这一点,布尔迪厄在《言语意味着什么》中的一句话值得引用:“作家们之间关于写作的合法艺术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斗争的存在本身,既促进了合法语言——按照其与‘通用的’语言之间的距离来界定的——的生产,又促进了对其合法性的信仰的生产。”[xxi]悖论由此可见,先锋艺术家要生产一种艺术语言就必会导致该语言的合法性之争(这种斗争是无法避免的,否则就不存在先锋派的生存空间),在合法化之途中必然导致信仰与信徒的生产而被“文化化”。
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在此合法化的过程中,先锋艺术通过何种方式来作为这种合法化的基础?那就是市场,或者是如格林伯格所讲的先锋艺术还是割不掉金钱这条“脐带”。我并不想说是市场而导致先锋的庸俗化,而是要说市场可以说是先锋艺术存在与得以运行的保障(不然,作为文化的艺术就是一种最自律的艺术了)。尽管在学院和正统机构中,传统艺术仍然占据主导,但在当代,先锋艺术依靠市场而日益完善与整个艺术系统的关联,从而逐渐将正统艺术边缘化。
当先锋艺术深入人心之时,也就是这种艺术市场系统统一之时,区分性保证了在交换中利润的获得,区分使得艺术家强调自己独特的个性,以不同于他人的“陌生化”与“震惊”等核心手段创作艺术品与艺术事件,从而逐渐形成艺术家个人的交换价值,使他的大规模艺术生产成为可能。
在艺术家得意忘形之时,他们也深深陷入困苦之中,在奥利瓦所揭示的那种相互关联的“艺术系统”之中,艺术家已不是必然的主体,特别是在前卫艺术观已成为一种主导力量而形成特权之时,自律已经受到歪曲,艺术家已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这系统的制约与影响。有一部分人幻想退入到私下空间里而坚持一种纯粹的主体自治,而不顾外在的正式场域,殊不知这种主体性自律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而落入自得其乐的“自欺”之中。一旦他们的作品用于公共交换中,便要重新接受正式规则的检验。当然有两种类型是不被外在系统重视的,一种是转折性人物,由于我们的短视还无法认识他的价值;另一种则是“老生常谈”,只能归入文化范畴之中,而没有艺术价值,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不具“施事性”(不是指言辞必须有所指,而是它必须是有作用的)的,或者也可以说它们会由于文化政治原因而产生虚假的施事效果。而“作为艺术的艺术”则是“施事性”的,即对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市场并非是先锋艺术的噩梦,失去它先锋艺术也将无以为继。从这里我们便可以将真正艺术与庸俗艺术区分开来,尽管两者都受到市场与交换的影响,但很明显后者是对惯例的依赖而前者则是对结构的依赖。
在这里已经讲明不能将先锋派的困境归咎于市场,但随着交换的扩大,市场确实应该对先锋派逐渐失去原先赖以成功的那股生猛的力量,使它进入后现代的折衷之中这一结果承担责任。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中说:“交换恢复了一切,使貌若弃绝它者适应了它。”[xxii]本来作为一种社会的异在力量和对现行的否定力量的先锋艺术,如今却被政府接纳而频频出现于公共空间之中,先锋艺术展览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名片,“格格不入”被纳入到体制之中,使得当代先锋艺术家的反叛成为一种姿态。这也正是很多理论家认定先锋艺术最终的终结之处:赏识先锋艺术的却是它原来一直反抗的阶级。先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悖论的结晶体,与它相联系的一切也都是悖论的,它包含着一种向着“生”的“死亡驱力”。
三
王林先生的《野生的价值》一文可以被看作是他着力恢复先锋精神的一种努力,认为艺术与体制的关系只是一种相交圆的关系,而永远不会重合,而体制未能覆盖之处即艺术的野地。同时野透露出艺术能继续发展的出路:“当艺术和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大众、媒体、官方都不能左右艺术……不是前卫艺术因体制而改变,而是体制因前卫艺术而不得不改变。”[xxiii]从文中可以看出来王林先生仍然信任艺术的那种乌托邦力量,并且也是从一般层面上来看先锋的,先锋精神是能够自我更新自我突破的,它被实体化又不断地从实体化中挣脱出来,它是艺术发展一种恒在动力。而我在这里要补充的则是,面对先锋派的使命以及它本身的悖论,主体必须是要分裂的,必须面对“多元化”而不断地将自己客体化,才能完成使命,才能面对充满否定的外在世界。先锋艺术家必须将先锋艺术的生和死内在化为自身,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但鉴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戏拟与娱乐,我们是否应该呼唤一种“终极在场”,难道我们应该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绝望之处重新期盼上帝的亲临?
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经处于“后上帝时代”,一切价值当被重估。我要说的是,原来的价值确实被摧毁了,但那价值却不是上帝的价值,而是我们信仰上帝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事实上上帝是仅仅在我们这个时代才真正复活,整个古典时代上帝从未亲临,而只是处于一种对上帝的亲临的期盼状态之中,这种状态我们可以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体会到,两个无望的男人在等待戈多的来临,而所有的价值就是建立在这种等待中的。古典时代相信上帝随时会亲临,而“上帝死了”那振聋发聩的口号打碎了建基于期盼之中的整个价值体系,造成了整个幻觉世界的崩溃。上帝的复活则必须建立在这种价值世界的崩溃之上,而他复活的方式则依靠的是命名,而人类在行使上帝这种特权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上帝的亲在。艺术就是一种命名,这在古典时代还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这样才使“人人是艺术家”成为可能,这正是先锋派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这里我要将“命名游戏”与“上帝的命名”区别开来,我们不能接受当代样式主义者的命名游戏,我们唯有实行上帝的命名才能“随便什么都可以”,才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而“作为艺术的艺术”所要探讨的就是使不可能可能,使不能呈现者呈现的“上帝的命名”,它始终要追问的是像利奥塔表述过的“在吗?”那个问题。
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家轻信“上帝已死”之论并埋怨上帝未能兑现他所承诺的东西就开始对旧有世界、现有体制发起同归于尽的攻击,是市场和交换挽救了它。不死的先锋艺术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它必须经过死而后再生。在后现代主义者抓住市场这根救命稻草之时,将这种死亡变成了在应对危机之时不断玩弄的一种修辞,构成了当代艺术面貌的漫画化,取得一种“结构性的狂欢”。因此艺术必须在艺术死亡之时重新建立起它的威望,并得到某种程度的救赎,而净化一种作为艺术的艺术。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雪莱的名言:“诗人,是不被承认的世界立法者。”或者可以称为匿名的上帝,而一种自律性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得到理解。
四
在整篇文章中我都努力从一种先锋派预设的艺术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并且已经认为文化必须与先锋联系在一起,轻易不顾及文化将可能造成先锋的不可为继,我甚至在行文中隐约表示文化也许是先锋的一种“命定”。我们另外还会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交界之处。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他们正是从学习作为文化的艺术而开始他们的艺术之途的,他们也是在这种文化的症结之处开始提出艺术的新的出路,正如前所述一味只对准新的艺术就将毫无新可言。另外作为文化的艺术并非是注定的“残渣”,它总是存在着重生的可能,特别是由于当代艺术不再相信艺术作品的整一性或者叫宏大原则,一些局部可以游离出来而重新构成作品这一趋向,以及主体的分裂为这种重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通过一种转义它们仍可能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视角。最后我要以利奥塔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艺术中的创新是这样的:人们采用被以前的成功证明了的形式,将它们和其它原则上讲不协调的形式相接,使它们失衡……。”在革新进行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在吗?”的问号。[xxiv]
[注释]
-------------------------------------------------------------------------------
[i] [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6页
[ii]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同上,第37页,第38页,第57页
[iii]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3页,第115页
[iv] 同2
[v] 同3
[vi] Stewart Martin:Autonomy and Anti-Art:Adorno’s Concept of Avant-Garde Art.Blackwell Publishers Ltd,Volume7,No2,2000.PP.198.
[vii] 同2
[viii] [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4-135页,第159页
[ix] 同2
[x] 同2
[xi] 同6
[xii] Andrew J.Webber:The European Avant-Garde 1900-1940.Polity Press Ltd,2004,PP.4.
[xiii] 同8
[xiv]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4页
[xv]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2页,第118页
[xvi] Maarten Dooeman,Sherry Marx:Art in progress:A Philosophical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Avant-garde.Amsterdam Ame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9.
[xvii] [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7页
[xviii]雷纳托·波吉奥利:《前卫艺术的理论》,张心龙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63页,第65页
[xix] 同18
[xx]易英:《前卫与边缘》,见《美苑》,1995年,04期,第8页
[xxi]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8页
[xxii]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屠有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xxiii]王林:《野生的价值》,载《艺术新视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xxiv] 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