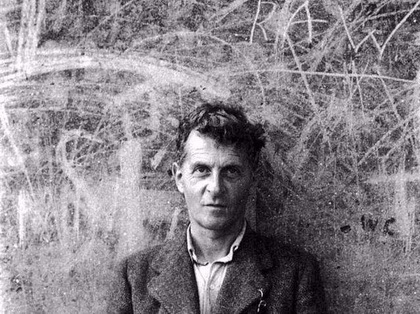作者: 席格
东郭子向庄子问询道在哪里时,庄子语出惊人,说道可以在蝼蚁,可以在稊稗,可以在瓦甓,也可以在屎溺。这种“目即道存”的道家哲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对如何借助具象来展现“大道”探求。由于山水以形媚道,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山水占据主导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但由于体道境界的差异,同是山水却又各有妙处,神似而形异。事实上,庄子已明确告诉人们作为众妙之门的道,无所不在。“道生万物”,理应如此。而山水又何以能引得画家情有独衷?大概是出于山水形美的缘故吧。是否入画家法眼的必须是形美之物呢?未必如此,苏东坡之枯木怪石便是明证。进而言之,枯木也好,怪石也罢,并非直接入画,均已成为画家心中的意象之物。那么,万物之本的“道”与后现代艺术遭遇时将会是一番何等景象呢?
杜尚的现成品艺术、达达主义者们的拼贴创作,对于抱定传统艺术观念的人们来说,无论如何也无法见其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之所在。确实,谁又能够说清楚倒过来的马桶究竟会带给欣赏者什么美感?乍看子明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魏晋书者何处去》、《画的重叠》等作品时,或许会在脑海里闪现这不过是带有中国元素的拼贴的观念。果真如此吗?犹豫之际驻足玩味,会蓦然发现原来恍惚中别有韵味。现实感触的质感与平面影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错位中蕴含的就是子明对事实真相的寻找,对生活之真的探求,对道的追问。
道家的道无所不在,释家的禅又何尝不是如此?禅宗公案中有这样一则对话:有僧人问:“佛法的大意是什么?”法常禅师回答:“蒲花和柳絮,竹针和麻线。”道与禅,并非神秘莫测,道在万物,禅在生活,二者均可于当下去体悟。至于道与禅所藏身之物,既并非全是美善之物,也并非全是艺术家所创造的神似之物。《佛经考古说》、《禅花》等便是借助黄土、麻线、棋子、衣物、报纸等现成品与书法、篆刻、油画、工笔画等艺术品,来作为悟道体禅的筌。子明的创作显然已经突破了所谓中西画法的界限,将其自然而然地打通为一,并非是毫无内涵与深意的做秀,而是他长时间对中国传统哲理体悟的后现代表述。这必须细细玩味。 中国古代画家对花草的执著,或是受儒家比德思想的影响,借梅、兰、竹、菊、荷花等暗喻自己的人格;或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山水体“道”,展现人与自然的合一;或是受禅宗影响,借助几株花草来蕴含整个宇宙的生命气息,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但画家们都无外乎是借助自然来展现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感悟、对“道”的体悟。这种绘画传统可以说已经潜移默化到了中国画家的骨髓之中,成为一种潜在的定式。这一方面为画家提高自己的艺术境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一方面也限制了画家对艺术传统的突围。
子明虽外表文弱,但骨子里却充满了一种源于自信的霸气与狂妄。因而,他敢于喝祖骂佛,敢于表现自己,标榜自我。尤其是在他习禅之后,人生境界为之提升,画风也骤然大变。禅使他于外界的浮躁中保持清静的自我,洗去先前的狂躁,而增加一份深沉。但并非陷于一种传统的枯寂感,而是通过生命的碰撞展现一种对生命的深度思考。
这些曾经绽放的美丽只能进入生命的轮回。这就将为花草绘画带入了一个新的向度,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由于中国画学依托于中国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依然是呈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人能够忘情于山水,山水可游、可居;同样,人也能够任性于花草,花草尽显人之性情。而这种思想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能够和睦相处。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却是另一番景象。人,原本属于大自然的成员,已彻底走向与自然的对立,自然之母成为人彻底征服的对象,结果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子明运用绘画的方式,将残酷的现实用一种唯美的方式展现出现,无疑具有强烈的对比意义。子明的这种思考,无疑充满了浓郁的当代气息。“感恩•生灵”,确是耐人玩味。
子明将佛家对生命的关爱充分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以恬静的方式把人带入幸福的多姿多彩的梦幻之中。梦,作为被压抑的潜意识的释放,是捉摸不定的,并由此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暗示和解读。现实中,我们可以向周公咨询梦的征兆,卜问吉凶。但我们却无法直接进入他人的梦境,作为一个清醒的观察者去审视他人的梦。子明却以一个梦游者姿态,通过线条将我们慢慢拉进他们的梦境,使我们获得了“游梦”的机会。,你到底是美梦连连,是梦回千古,是梦通五经,是梦里飞仙,还是游梦惊魂。
席格于河南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