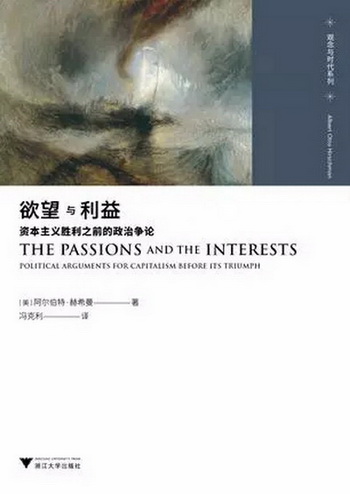
按:本文选自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第一章第四节,标题为:欲望制衡原理,冯克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27页。
导语:
理性是、也只应当是欲望的奴隶。
——休谟
欲望与欲望是对立的,人们能够用一种欲望制衡另一种欲望。
——沃夫纳格
人类是不安分的,受欲望驱使的,此乃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这使压制和驯服欲望的办法都缺乏说服力。压制的办法是在回避问题,而更加现实主义的驯服办法,被其炼丹术一样的转化过程所玷污,也与那个时代的科学热情不太合拍。
17世纪的道德学家所处理的事情——对欲望的详尽描述和研究——注定引出第三种解决方案:是否有可能区分欲望,以毒攻毒?——利用一些相对无害的欲望去反制另一些更危险、更具破坏性的欲望,或者说,以“分而治之”的方式,让欲望之间相互对抗来弱化和驯服欲望?人们一旦对道德教化的功效感到绝望,这似乎是个简单明了的想法。但是,尽管有圣奥古斯丁偶然的暗示,形成这种想法很可能比同时抨击所有欲望的方案更加困难。在文学界和思想界,长久以来主要的欲望都被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常常表现为一种邪恶地三位一体——从但丁的“傲慢、嫉妒和贪婪,是点燃人类的三束火花”到康德《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General History)中的“野心、权欲和贪婪”。人们认为,就像人类的三种灾难——战争、饥荒和瘟疫——一样,这些基本欲望也相互孳生。它们通常被视为一个违反理性命令或救赎要求的集合体,这进一步强化了它们不可分割的习惯看法。
中世纪的寓言常常描写美德与罪恶之战,人的灵魂就是它的的战场。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中世纪的这一传统,使后来更加务实的时代能够设想一种大不相同的斗争,让欲望对抗欲望,同时像早期的想法一样,使它仍能给个人和人类带来好处。不管怎样,这种想法出现了,而且实际上是发生在17世纪两个思想和个性截然相反的人身上:培根和斯宾诺莎。
就培根而言,这种思想是他力求全面摆脱形而上学和神学枷锁的结果,这种枷锁阻碍人们以归纳和实验的方式进行思考。在《学问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论述“人的嗜好和意志”的部分,他批评传统的道德哲学家的作为像是专门讲授写字的人,只展示写有字母表和单词的漂亮小册子,对于手的姿势和构造单词不提供任何规范和指导。他们搞出美好的范例和范本,摆弄着“上帝”、“美德”、“职责”和“幸福”这些棋子……可是如何达到这些美好的目标,如何塑造和驯服人的意志,使之与这些追求真正一致,他们全都抛到了脑后……

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
虽然这种批评自马基雅维利以来便为人熟知,但这个比喻还是具有明显的启发作用。几页之后,培根亲自动手尝试他所提出的任务。他在这样做时佯装赞美诗人和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相反,他们极为生动地描述欲望如何被点燃和煽动起来;如何加以抚慰和抑制;……它们如何展露自己,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变化,如何聚集并壮大;它们如何相互纠缠,相互对抗,以及一些诸如此类的细节。其中最后一点对道德和公共事务尤其有用。我要说的是,如何让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互相牵制,正如我们用野兽猎取野兽、用飞鹰捕获飞鸟。……因为就像各国政府之间有时必须以一派制约另一派一样,政府的内部也要如此。
这段铿锵有力的话,尤其是它的后半部分,充分表明它是基于作为政客和政治家的培根的丰富个人经验,而不是基于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成就。此外,通过用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的方式来控制欲望的想法,也与培根充满叛逆精神的经验主义思想倾向高度吻合。但是另一方面,他这些言论在当时似乎不是特别有影响。只有现代学术研究为说明培根在这一点上是斯宾诺莎和休谟的先驱才注意到了它,它们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赋予了这种思想更为核心的位置。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阐述他的欲望理论时提出了两个命题,这对他展开自己的论述至关重要:
除非借助相反的更强烈的欲望,欲望无法得到限制或清除。
和有关善恶的正确知识并不能因为其正确而抑制欲望,只有把这种只是看作一种欲望时,它才能做到这一点。

注: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年),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代表作有《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
斯宾诺莎有形而上学倾向,相对缺乏参与实际生活的经历,他却提出了与培根相同的学说,乍一看这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让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能够使欲望得到有益的抑制和操纵,这种想法与斯宾诺莎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主要是用来强调欲望的力量和自主性,旨在使人充分意识到抵达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的旅行目的地的显示困难。这个目的地就是用理性和对上帝的爱战胜欲望,而欲望相互制衡的观点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旅程中的一站。同时,这种观点是斯宾诺莎此书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可由它的最后一个命题得到证明:
【我们不是】因为抑制我们的欲望而喜欢幸福;相反,因为我们喜欢幸福,我们才能够抑制欲望。
可见,把只有利用一种欲望战胜另一种欲望的思想置于崇高地位的第一位大哲人,并不想将这种思想引入道德实践和政治操作领域,尽管他对这种可能性持鲜明的赞赏态度。实际上,这种思想并未重现于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著作中,否则,在如何使人性的诡黠有利于社会方面,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著作也就不会缺少实践性建议了。
虽然休谟指责斯宾诺莎的哲学“令人厌恶”,但他关于欲望及其与理性的关系的思想却很接近斯宾诺莎的观点。休谟在宣称欲望不受理性影响方面简直更加激进:“理性是、也只应当是欲望的奴隶”,这是他最著名的论调之一。他明白这是一种极端立场,因此亟须用另一种思想加以调和,即一种欲望能够发挥制衡另一种欲望的作用。他确实在关键性的同一段话中表明了这种观点:“除了相反的冲动,没有东西能够抵抗或阻止欲望的冲动。”

注: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有《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人类理解研究》、《英国史》等。
不像斯宾诺莎,休谟很乐于实际运用自己的见解。在《人性论》第三卷讨论“社会的起源”时,他立刻就这样做了。在谈到“攫取财物和资产……的贪婪”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具潜在破坏性和独特力量的欲望,制约它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它自己制衡自己。这不像是个易于操作的办法,但以下是休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
因此,没有哪种欲望能够控制利己之心,只有通过那种欲望本身改变它的方向才能做到。这种改变是稍加反省就必然发生的,因为显而易见,约束欲望比放纵欲望能更好地使之得到满足;维护社会比孤独状态能够在获得财富方面有更大收获……
对此当然可以吹毛求疵说,承认需要某种理性或反思,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这意味着将一种异质因素(而且是把它设想为“欲望的奴隶”)引入另一个领域,而那里的假设是只有欲望在与欲望对抗。不过,这里的要点不是指出休谟思想的瑕疵,而是证明制衡欲望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例如他在评论曼德维尔时认为,奢侈固然是一种罪恶,但较之“懒惰”它可能是一种较轻的罪恶,后者会因禁止奢侈而发生:
所以,我们姑且满足于宣布:两种对立的罪恶并存可能优于它们单独存在;但我们还是千万莫说罪恶本身也有益吧。
更全面的阐述如下:
赋予人类各种美德,使他摆脱各种罪恶,不管这种神奇的转变可能有和结果,都与只致力于可能事态的行政长官无关。他所能做的,常常只是用一种罪恶消除另一种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选择对社会危害最小的罪恶。
下面我还会提到,休谟在其他地方主张用“爱财”去抑制“贪图享乐”。甚至当他不赞同将这种观点运用于其他事情时,他显然也对它十分着迷,例如线面这段引自“怀疑论者”一文中所说:
“对于野心和征服欲,”方坦尼尔(Fontenelle)说,“没有什么比正确的天文学更具破坏性了。与浩瀚无穷的大自然相比,甚至整个地球也如此卑微。”这种遐想显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或者假如它有的话,它在摧毁野心的同时是否也会摧毁爱国主义呢?
这一反驳表明,聪明地利用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18世纪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实际上,有一大批作家,无论名声大小,都曾以一般或实用的方式表达过这种思想。《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的“狂热”(Fanaticism)条目就以后一种方式阐明过这种思想;这个条目基本是对宗教制度和信仰的猛烈抨击,以专门论述“爱国者的狂热”一节作为结语,对它倍加推崇主要因为它能用来抵消宗教狂热。比较而言,沃夫纳格以最一般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思想:
欲望与欲望是对立的,人们能够用一种欲望制衡另一种欲望。
在霍尔巴赫更为详尽的阐述中,亦可发现同样的语言:
欲望是欲望的真正平衡物;我们切不可试图扼杀它们,而是应当努力引导它们;我们还是用有益于社会的欲望来抵制有害社会的欲望吧。理性……无非是指为了我们的幸福而选择必须遵从欲望的行为。
制衡欲望的原理在17世纪便已出现,其基础是当时对人性所持的阴暗看法,以及对欲望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普遍信念。到了下一个世纪,人性和欲望再次得到广泛讨论。在法国,欲望最勇敢的捍卫者是爱尔维修。他的立场在《论精神》(De l’esprit)一书的章节标题中有充分的表达:“论欲望的力量”、“论有欲望之人的智力优于重情感之人”和“人无欲望就会变愚”。然而,正如卢梭一再俗套地呼吁要观察“真实的”人那样,尽管他的人性观完全不同于使他有此呼吁地那些人最初提出的观点,人们也同样继续提倡制衡欲望的手段,虽然现在欲望已不再被认为有害,而是能够提振人的精神。事实上,爱尔维修提供了对这一原理最出色的表述之一,他又回到了培根最初的说法,当然也增加了一些轻浮的笔调:
懂得如何让我们的欲望相互对抗……以便使他们的劝说得到采纳,这样的道德学家少之又少。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忠告都是遵从欲望十分有害。可是他们应当认识到,这种伤害打不败情感,只有欲望才能战胜欲望。例如,假如有人打算劝说轻佻的女人(femme galante)端庄而收敛,他应该利用她的虚荣心去克服她的轻佻,让她明白端庄稳重使爱情和优雅享乐的来源。……如果道德学家采用这种方式,用利益的语言代替欲望有害的说教,他们便有可能成功地使人们接受其箴言。
对于我们下一步的论证特别有意义的是,这里的“利益”一词是一个用来指称一类欲望的概念,这些欲望被赋予了制衡的功能。
这种思想从法国和英国传到了美国,在那里它被国父们当作一个重要的知识工具用来制定宪法。《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第72篇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从最近总统权力的经验来看,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汉密尔顿在这里为总统连选连任的原则作了辩护。他的论证主要是根据禁止连任会对在任者的动机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说,除了其他不良后果之外,这将导致“卑劣念头和侵吞公帑的诱惑”:
如果恰好是个贪婪之人在职,他预见到在一定的时间他无论如何必须放弃他享有的薪酬,他就会感到一种对他这种人来说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会尽量利用现有的机会,无所顾忌地以最腐败的方式大肆中饱私囊。而同一个人,如果前景不同,他有可能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带来的正常收入,甚至不愿意承担滥用机会所招致后果的风险。他的贪婪可以成为防止他贪婪的卫士。这同一个人除了贪婪之外,可能还爱慕虚荣或者有野心,如果他能够期待以良好的表现延长自己的荣誉,他可能不愿意牺牲荣誉以换取财富。但是面对难免即将卸任的前景,他的贪欲很可能压倒他的谨慎、虚荣或野心。
最后几句话显示了运用制衡思想的娴熟技巧,甚至让没有对这种思路接受过多少训练的现代人目瞪口呆。
看起来与此十分相似的论述制衡思想更为著名的一例,见于《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该篇以“必须用野心来反制野心”这一论断,雄辩地证成了政府不同分支之间的权力分立。它的意思是,政府一个分支的野心可以用来对抗另一个分支的野心,这非常不同于上一情形,欲望之间的争斗在那里被视为一个灵魂之内的事。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权力分立的原则只是换了一身装束:这种比较新颖的制约与平衡的思想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采用了制衡欲望这一得到普遍认同并为人们所熟知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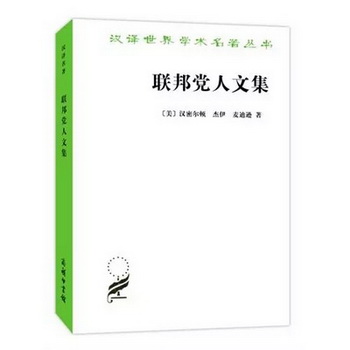
这当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其实,上述警句的作者(汉密尔顿或麦迪逊)似乎成了它所引起的混乱的第一批受害者。因为他接着说:“对人性的反思,也许使这些限制政府滥权的设计成为必须。然而,政府本身不就是对人性的全部反思中最了不起的反思吗?”在这里,“对人性的反思”确实是在主张,只有把人的不同欲望安排得相互对抗和制衡,才能抑制他的罪恶冲动。另一方面,权力分立原则不太像是对人性的侮辱。所以,写下“必须用野心来反制野心”这一警句的作者看来是要让自己相信,制衡欲望的原理,而不是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原理,才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
更一般地说,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前一原理为权力分立原则奠定了认知基础。如此一来,这里所研究的思想脉络便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它本是以国家作为起点,然后转向对个人行为问题的思考,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见解又被适时重新输入政治理论之中。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