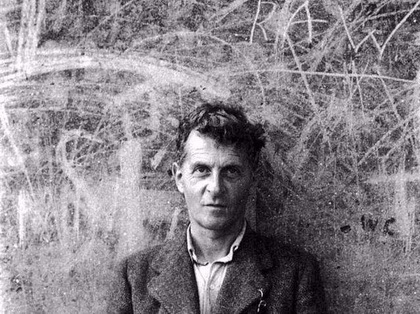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许多地方都涉及到黑格尔,而在这些涉及到黑格尔的地方,表扬的话比批评的话更多。然而,就黑格尔辩证法而系统地、完整地分析和评价黑格尔的,要首推他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该文是海德格尔1942—1943年为他举办的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班所做的报告,1950年被收入《林中路》在法兰克福(美因)出版,后编入《全集》第5卷。在该文中,海德格尔逐段地、在一些地方甚至是逐字逐句地梳理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的十六段文字,进行了一种表面看来严格按照文本、实际上是“六经注我”的诠释。这些诠释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把黑格尔在这个导论中相当系统地发挥出来的辩证法,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辩证法,以及体现为“意识的经验科学”的概念的历史进展的辩证法,全面扭曲为某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视为他自己的“基础存在论”的一种不成熟的表达。当然,孤立地来看,海德格尔对黑格尔这个文本的解释似乎具有某种自洽性,但这种解释难以与黑格尔的其他文本相容。海德格尔这种任意解读经典的态度常被思想史的研究者所批评。但他自有自己的辩护。他曾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说:
无疑地,任何一种解释不但必须获取本文的内容,它也必须不加注明地把从它自己的内容而来的某种东西加给本文,而不是固执于本文。……一种正当的解释对本文的理解决不会比本文作者的理解更好些,而倒是不同的理解。不过,这种不同必定是这样的,即,它切中了被解释的本文所思考的同一东西。(海德格尔,第220页)
我在这里不想否定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或者其他人)的有意误读的思想价值。我只想通过对这种误读的分析,寻找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他的哲学前辈发生关联的内在线索,即他是从什么地方与黑格尔分道扬镳的;而这一分析如果成功,也许能够不仅加深我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也加深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
一、“意志”的引入及在场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要把黑格尔解释成自己所意想的那个样子,必须要有一套脚手架,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他从外面引入的一个概念:意志(Wille)。这个概念我们在黑格尔的这个文本中并没有找到(该文本被载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前),海德格尔的唯一凭据只有黑格尔的一个“附带的”从句:“(绝对)自在自为地就已经并且就愿意存在于我们这里”(海德格尔,第130页,参见第127页)①。黑格尔这个从句的意思本来是,“绝对”并不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远在天边(或彼岸)的东西,它已经在我们这里,并且愿意通过我们的认识活动体现出来。黑格尔这几段话(至少如第一、二、三段)一直都在不点名地批判康德的认识论。所以黑格尔这里的“愿意”(wolte)只是不会拒斥的意思,并没有“意志”行为的含义。但海德格尔抓住这个连半句话都算不上的从句做起了文章:“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意求绝对之意志,亦即意求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第133页)他引用黑格尔的话:“只有绝对是真的。只有真理是绝对的”,并解释说:“这两个命题是未经论证的,但不是在随便断言这个意义上的任意的。这两个命题是不可论证的。它们设定了最初建立自身的东西。在这两个命题中,那种自在自为地已经愿意存在于我们这里的绝对之意志在说话。”(第135-136页,有改动)这种解释就把黑格尔变成了尼采。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黑格尔哲学中、包括他的认识论中,本身确实包含有尼采式的意志主义(乃至生存主义)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决不是他的无条件的、不可论证的第一原则,而是经过逻各斯主义所中和了的,否则黑格尔就不可能在哲学史上被视为“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
而海德格尔之所以强行引入“意志”概念,是为了把黑格尔哲学、尤其是精神现象学解释成“在场的形而上学”。例如他说:
精神现象学存在于它的表现之中。……科学以自己的方式只意求绝对所意求的东西。绝对之意志就是自在自为地已经存在于我们这里的东西。眼下这就是说:就绝对这样被意求而言,当我们是认识者时,在我们这里只有绝对真理。……但这就要求,科学随其最初的步骤就已经进入绝对的在场(Parusie),也即存在于它的绝对性那里。……科学因此必须把自己带到那个法庭面前,只有这个法庭能够裁定科学的考查何在。这个法庭只能是绝对的在场。(第137页,有改动)
所以,海德格尔对第四段话的解释是,认为黑格尔在这里“指出在绝对的在场中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即自在自为地存在于我们这里的意志,对我们认识者所提出的要求(第139页)。这与黑格尔的原意相差甚远。这里只有一点是和黑格尔的原文重合的,这就是黑格尔反对像康德那样把我们的认识当作一种可以用来把握绝对的工具,因而反对想在认识之前预先对认识进行一番考查的“额外做法”;而海德格尔把认识看作绝对意志的在场(“在我们这里”),同样也可以避免“流行的对哲学认识的批判不假思索地把这种意志看作一种手段”(同上)的做法。因此我们能够把科学的认识视为“在在场内部因而从在场而来,我们必须把我们与在场的关系产生出来并带到在场面前。……科学的辛劳勿宁说起于它与在场的关系。”(第140页,有改动)所谓“在场”,就是已经在我们这里出现了,给予出来了,现成在手了,而无须事先作一番抽象的推导。这就是意志。海德格尔就是利用这一重合之点,认为黑格尔的绝对只是意味着意志的在场,也就是说,它以科学之光的方式显现出来:
科学作为绝对认识乃是光线,这种光线就是绝对,是照耀我们的真理本身的光。从这种光线的照射中显现出来就意味着:在自我呈现着的表现的灿烂光辉中在场(Anwesen②)。显现乃是真正的在场本身,是绝对之在场。依照其绝对性,绝对自行存在于我们这里。在存在于我们这里的意志中,绝对是在场着的。……唯由于在场的意志之故,对显现着的知识的陈述才是必然的。这种陈述必须始终致力于绝对之意志。(第143页,有改动)
这就涉及到对黑格尔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有意误读。自古希腊以来,“光喻”就是本体论(存在论)的一个象征的说法。这种比喻当然也是黑格尔本人的一贯做法,他的“反思”(Reflexion)就是借用的光喻。海德格尔把它用在现象学(显象学)的本体论上,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但问题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和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虽然在“显现出来”(在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在显现出来之后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称之为“本体论”这一点上,却是大不相同的。在黑格尔,现象学后面当然是有其本体论的根基的,但是那个根基并不叫做“现象学”,而是叫做“逻辑学”,现象学一开始就被视为逻辑学的一个入门表现和应用功能。而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本身就是本体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本体论。换言之,黑格尔的光喻后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发光者,即柏拉图所谓“不动的推动者”、“善的理念”,海德格尔的光喻后面则什么也没有,只有光线的“在场”和照射。正是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存在论做了极大的扭曲。他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释成他自己的那种“显象学”,然后他代替黑格尔发挥其“显象学”的存在论意义。这就是他对黑格尔的“陈述”、“自然意识”和“怀疑之路”这三个概念的误读。
二、对“陈述”、“自然意识”和“怀疑之路”的另类诠释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反思精神体现在,他的现象学不只是把具体显现的内容作为对象,而且还把对这些内容的陈述以及陈述的方式作为更重要的对象。而这种陈述在现象的不断更替中便形成了一条(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向真知识发展中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的本性给它预定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第143页)。这正是黑格尔的逻各斯精神对努斯、灵魂的更高层次的引导。但海德格尔的工作就是要把陈述过程中的那种逻各斯精神淡化和消除掉,他批评说:“直到现在,甚至哲学也认为,精神现象学乃是一个旅行指南,是一本游记,它伴随着日常意识走向哲学的科学认识。但如果这样理解,则精神现象学在表面看来的样子就不是在其本质中的现象学了。”(第144-145页)“陈述绝不是领着自然表象在意识形态的博物馆四处游荡,以便在参观结束时穿过一扇特殊的门,把这种自然表象释放到绝对知识中去。……但陈述仍然是一条道路。陈述仍然不断地往返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个在自然意识与科学之间起支配作用的中间地带。”(第145页,有改动)在这里,他所批评的“哲学”其实就是指黑格尔哲学。正是黑格尔自己把精神现象学看成一份“旅行指南”(或他所说的“梯子”),用来指导日常意识“走向哲学的科学认识”即“绝对知识”;但这在海德格尔看来就“不是在其本质中的现象学了”。那么,要如何才是“本质中的现象学”呢?海德格尔认为必须“不断往返(gehen stndig hin und her)在一个中间地带”,也就是去掉这一过程的目的性,使这条“道路”成为一条回旋之路,以便不断地“在自然意识与科学之间起支配作用”。现象学不是一条“通往”绝对知识的“道路”,它本身就是绝对知识,问题只在于如何去“陈述”它。陈述严格说来并不是在走着一条“道路”,而只是在这条路上往返徘徊,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层次,一种“看”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直接地在“自然意识”中“看”出“科学”来。这就是现象学的描述法,也就是所谓“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至于如何将自然意识还原为科学,海德格尔所说的与黑格尔也是貌合神离。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自然意识把显现出来的东西直接当成是知识,但随着这些“知识”的一个个被否定而成为假象,自然意识陷入绝望的怀疑之中,所以自然意识就体现为一条绝望之路、怀疑之路。但只要我们关注在这条道路上的陈述方式,就会发现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意识向科学、向真正的知识的形成史。自然意识在它的自我否定中提高了它的层次,对它的陈述则揭示了这种层层提高中的逻辑必然性,最终将达到它的纯粹意识的逻辑终点——绝对知识,从而扬弃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海德格尔也看到了使自然意识得以显现出来的陈述方式在使自然意识提升到实在的知识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他看来勿宁说是一次性到位的或总体性的,而没有一个逻辑发展过程。“陈述借正在显现着的知识把存在着的意识表象为存在着的,也即把它表象为现实的、实在的知识”(第149页,有改动),这种表象作用是直接的,而不是推出来的。因为,虽然“自然意识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并不关注存在,但又不得不关注存在。它不得不一般地把存在者之存在一起表象出来,因为如果没有存在之光的话,它甚至不可能失落在存在者那里”。(第151页,有改动)这其实已经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立场,而是胡塞尔“现象学直观”的立场了。表面上看,海德格尔说着黑格尔式的语言:“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知识实际是同一的,因为前者作为还不真实的东西与后者作为前者的真理性,必然是共属一体的。但两者恰恰因此也是不同的”(第153页,有改动)。但黑格尔的意思是,实在的知识就是通过自然意识的历程而形成起来的,因而两者既同一又不同;海德格尔的意思却是,我们从自然意识中、从这些“存在者”中通过现象学还原的眼光,即可直观地“看”出它本身的“存在”,从而达到有关存在的实在的知识,所以现象即是本质(存在),只是在日常自然意识中人们看不到这一点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怀疑之路”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自然意识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因而它经过自然意识通往真理;在海德格尔这里却意味着将自然意识所自认为的真理悬置起来,从而揭示出自然意识之所以成为自然意识(存在者)的“根”,即存在。所以他借助于黑格尔的术语而“重获了‘怀疑’一词的原本含义;σκεψι意味着:看、观望、察看,去看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和如何存在。这样来理解,怀疑就是在看的同时追踪存在者之存在。它的观望预先已经看到了存在者之存在”。(第154-155页)但这种“预先看到”并不是自然意识的事,而是“我们”的一种“额外做法”,一种对事情本身(存在)的“先验还原”的操作。
三、对“存在”(Sein)的两种不同的“语言用法”
如果说,海德格尔在此之前还是尽量想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存在”这个最关键的术语上,他就不得不公开表明他自己独有的立场了。“在这里,我们已不能回避一种对语言用法的说明”,因为他看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das Sein)作为如此被称呼的存在者(Seiende)的名称,乃是表示实际上根本还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那个东西的名称。黑格尔用‘存在’来命名在他看来还非真实的实在性”(第156页,有改动)。所以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存在”只是单纯的存在者,只意味着客观性或对象性,而不具有“现实性”(Wirklichkeit);另一方面,“与黑格尔的语言用法相区别,我们所使用的‘存在’这个名称,既表示黑格尔以及康德所谓的对象性和客观性,也表示黑格尔所设想的真正现实的东西和他所谓的精神的现实性”。(第157页,有改动)“存在”的这种双重身份使它既通过“在场”状态而显现出自身,但同时又在这种“在场”状态中遮蔽自身,因为存在并不仅仅是在场状态,而且是在场之所以在场。当我们看到在场时,我们往往只看到它的在场状态,而遗忘了在场本身,遗忘了它是如何“在起来”的。
显然,上述区别远远不只是一种“语言用法”上的区别,而且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概括也完全不准确。在黑格尔那里,“存在”并不表示“还非真实的实在性”,而仅仅表示一种“抽象的”实在性;它与“真正现实的东西”之间因此也不是一种外在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个东西的内在层次关系。在这种内在层次关系中,“存在”是一个最低层次的范畴;但正因为它是最低层次的,所以它又是无所不在的:即使是最高的“精神现实性”层次,也必须将“存在”这个最低层次包容于自身才得以成立,因为它本身不过就是最“具体”的存在,并且是由存在本身主动地(从抽象到具体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海德格尔说黑格尔的存在是一种“尚未获得其本身的主体性的直接表象的对象性”(第157页)是不对的,其实黑格尔在《逻辑学》的整个“存在论”中要批判的就是这种对存在的误解,因为黑格尔的存在本身正是“主体性”的,它表明它的对象(实体性)是由它自己建立起来的。在《精神现象学》中,与“存在”范畴相当的是“感性确定性”,它一开始就呈现为一条“怀疑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被否定的是“感性”,而被坚持下来的则是对“确定性”的追求,它最终是通往“真实的实在性”即真理性的。所以,被否定的方面和被坚持的方面都为绝对精神的形成作了贡献,如海德格尔在后面引用的《精神现象学》的结束语所表述的:“两者汇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第211页)
所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不但本质是真正的存在(他表述为:“本质是存在的真理”),而且就连概念、包括最后的绝对理念本身,也无非是具体理解的存在,所有这些都汇合为一个主体性的能动的“存在论”(Ontologie)。《精神现象学》则不过是在经验的层次上对这种存在论所作的一个导论而已。从这一点来看,黑格尔对存在概念的理解恰好与海德格尔有接近之处,即都是着眼于存在者是如何“存在起来”的,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存在状态和存在者本身。换言之,海德格尔至少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他所自以为的独创性。把一切存在者理解为“自己存在”,理解为不仅仅是各种存在状态而且是存在活动、存在过程和存在的历史(变易),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区别只在于,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历史”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它只是人类回避不了的“命运”,就像我们说不犯错误也就不知道真理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从人类必犯的“存在遗忘”的错误中翻然醒悟过来,就可以独具慧眼地从存在者中看出存在,从在场中看出无蔽的“真理”,而这个人就是海德格尔。总之,黑格尔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否定并因此达到自我肯定的过程。海德格尔也承认这种自我否定(怀疑之路),但他其实骨子里和笛卡尔一样,认为“这种置疑仅仅是为了保持在起始位置上”(第153页);他从这个固定的位置对人类历史进行“一切价值重估”(尼采)。
四、对“矛盾”(Widerspruch)的回避
黑格尔在第九和第十段文字中,在谈及科学的“系统陈述的方法”时,发现了这种陈述本身的一个矛盾:科学的陈述必须有一个尺度,但这个尺度本身又必须由科学建立起来。黑格尔把这一矛盾引回到意识本身的自相矛盾性:
如果我们首先回忆一下知识和真理在意识面前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抽象规定,则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消除就将表现得更加确切。因为,意识把某物和自己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第169页,有改动)
对此,海德格尔完全是避重就轻。他说:
在第十段中所进行的这种考察的方式表明,黑格尔并不是通过逻辑论证来缓和及消除陈述的本质中的这一矛盾的。表面上不可统一的东西并不在于陈述的本质。它在于那种不充分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我们总是还处于自然意识的表象方式的统治之下来看待陈述的。(第170页,有改动)
可见,当黑格尔把陈述的矛盾归结到意识本身的矛盾结构、从而使这种矛盾得到深化时,海德格尔却把这种深化解释为一种浅薄化,解释为一种尚未摆脱“不充分的方式”即“自然意识的表象方式”的结果。既然黑格尔不是从形式逻辑来谈陈述本质中的矛盾,而意识自身的矛盾性又是一种“不充分的”、“自然意识”的表象方式,所以海德格尔就处处刻意回避“矛盾”(Widerspruch)这个词,而代之以“模棱两可”或“两义性”(均为Zweideutigkeit之译)。在他的整个文本中,他已经把“矛盾”这个词废掉了。而这就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体能动性废掉了。众所周知,黑格尔对一切运动、变化的解释最终是建立在概念自身的自相矛盾性之上的,由于这种自相矛盾性,所以才带来了事物内在的“不安”,这就是一切运动之源。海德格尔也承认事物内在的不安,但他把这种不安归咎于自然意识本身的那种不充分性。他说:“但自然意识对自己掩盖了在它里面起支配作用的自身超越的不安。它避开这种不安,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这样来与之相联接:它把自己的意见视为真理,这样来要求自为的真理,并证实凡是它视为是它的东西都不是它的东西。它所自有的意见总是泄露出那种不可遏制地被拽到自身超越中去的不安。”但“运动的不可遏制性只能由不安在自身中所遵循的东西来规定。这种不安遵循着那个把它拽走的东西。那就是实在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只有当它在自己的真理性中显现自身时才存在”(第163-164页,有改动),所以“意识在其不安中本身就是对目标的先行设置”(第164页,有改动)。意识的前进运动不是由于它内在的矛盾性的推动,而是由于意识预先设置了一个外在于它的遥远的目标,所以意识才被这一目标的“吸引力”拖向前进:
在意识的形成史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进程并不是由意识的每一次形态而被推向前进,并被推(gestoβen)到那尚未规定的东西中,而是从已经设置的目标中被牵引出来的。在这种吸引中,发出吸引的目标把自己带到它的显现中,并把以前的意识过程带进它的完整性的完成之中。(同上)
显然,海德格尔所有这一系列的用词:“拽走”(fortreiβen)、“被牵引”(gezogen)、“吸引”(anziehen),还有后面的“被撕裂”(hinausgerissen)、“奉献”(opfert)、“遭受”(erleidet)等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黑格尔所说的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推动的主动运动转变成由某个外部目标所牵拉的被动过程。当然,黑格尔也谈到知识的进程必须确定一个“目标”,即对象和概念相互符合的目标,从而使“意识感受着从它自身发出的暴力”(第161页);但其根源正在于意识的自我超越和自相矛盾。所以意识并不是遭到了什么外来撕扯的暴力,而是自我撕裂;不是服从抽象的“绝对意志”的力量,相反,这种“绝对意志”本身倒是矛盾、痛苦和烦躁不安的表现,而并非真正绝对的。这些都是海德格尔所未能见及的。
其次是,取消了意识在存在论上的自相矛盾的逻辑必然性。虽然海德格尔把“意识的根本的模棱两可——即意识是表象的区分,而表象又不是任何区分”称之为“意识本身的本质统一性的标志”(第174页),但在他看来这种“本质统一性”不过是将意识中“被衡量的东西和衡量的尺度这两者”“聚合在意识中”,而且“意识的本性乃在于两者的结合”。这让我们想起康德对知性本质的规定,即知性的判断无非是用“是”把主词和谓词“联结”起来,这种“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是“知性运用的最高原理”,只有通过它,一切杂多经验才能“聚集到一个意识中来”。(参见康德,§15、16、17、19、20)显然,意识联结、聚集现成杂多事物的这种能动性与黑格尔那种克服自身矛盾分裂而生存的能动性完全不是一回事,海德格尔基本上是用康德的视角来理解黑格尔的矛盾学说的。同样,他也用康德的视角来理解存在和存在者的内在矛盾:
由于ον既意味着“存在者”,又意味着“存在起来”,这个ον作为“存在者”就可以被聚集(λεγειν)到它的“存在起来”上。这个ον按照它的两义性甚至已经作为存在者而被聚集到存在状态上来了。它是存在论上的。这个ον的两义性既指在场者,也指在场。它同时指这两者,而绝非指其中之一。与ov的这种本质上的两义性相应的是,对假象(δοκουνтα)的意见(δοξα),亦即对在场者(εοντα)的意见,与存在(ετ,ναι)之思想(νοειν),亦即存在(εον)之思想,是共属一体的。思想(νοειν)所觉知的东西,并不是与单纯假象不同的真实的存在者。勿宁说,意见(δοξα)直接觉知在场者本身,但并不觉知思想(νοειν)所觉知其在场的那个在场者的在场。(第182-183页,有改动)对ον、对存在的这种解释,与康德对“先验对象”的解释何其相似!康德的先验对象也是既指现象的聚集(在场者),也指激发这些现象的自在之物(在场);而现象和自在之物也是共属一体的,它们在思想中就是所指向的同一个对象,只是在现象的经验知识中我们并不能认识思想所想到的那个自在之物的存在。正如康德断言在认识论中自在之物和现象的混淆构成了以往形而上学的本质一样,海德格尔也认为在本体论中存在(在场)与存在者(在场者)的混淆构成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对黑格尔来说,存在作为主体(在场)和作为实体(在场者)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转化、相互矛盾而又相互同一(主体即实体),才是他自己的哲学、尤其是《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方式则是康德式的、知性式的,他避开存在之矛盾的办法就是对同一个ον严格区分两种含义。
五、对“意识的经验科学”的颠倒
海德格尔在对黑格尔文本的最后三段的分析中,着重对《精神现象学》的另一称呼“意识的经验科学”、特别是其中的“经验”(Erfahrung)一词进行了独出心裁的解释。黑格尔根据他前面的论述说:“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替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的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第186页)意思是,经验无非是意识在有关对象的知识方面的辩证运动。海德格尔则把经验纳入到有关存在者和存在的这样一种存在论的层次上来分析。他说:
黑格尔以“经验”一词所指为何?他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此间已成为了主体,并由此而成为了客体和客观的东西。……经验现在不再是表示一种认识方式的名称。就存在从存在者本身中得到知觉而言,经验现在就是存在之语词。经验指的是主体的主体性。(第187页,有改动)
经验就是存在,就是主体的主体性,就是意识的运动。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运动是由意识本身的辩证矛盾所造成的,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则恰恰要用经验的主体性来消解和淡化意识内在矛盾的辩证性。例如,“意识本身是它自己的概念,同时又不是它自己的概念”;“意识自身给自己提供尺度,同时又没有给它提供尺度”;“意识自身考查自己,但又没有考查自己”(参见第188-189页)。黑格尔把这种自相矛盾称之为“辩证的”,这使海德格尔极为反感:“关于辩证法的探讨犹如人们根据静止的污水来解释喷涌的源泉”(第190页);所有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描述(正反合、否定之否定等等),在海德格尔看来都顶多“只是一种派生出来的描述”(第191页),而这一切派生的基础则是经验。“经验乃是那个根据主体性而把自己规定为主体的存在者的状态。”(第191页,有改动)换言之,辩证法不能用来解释经验,经验则可以用来解释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只是对存在者的运动的一种解释,但不足以对存在本身作出解释。他试图把这种想法强加给黑格尔。但他自己对存在本身的经验解释只限于一些比喻,如木匠建造房屋、人的迁移、“牧人外出放牧,护送牧群上山”(参见第191页)之类。他当然可以把这些比喻当作更加根本的,甚至断言“经验是绝对之绝对性,是绝对在彻底的自行显现中的显现”(第192页),但这与黑格尔毫无关系。因为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就只是“意识的经验科学”的对象,这门科学只是一个导论或“梯子”,它还未达到“绝对知识”,更遑论绝对精神。
那么,海德格尔又是如何理解黑格尔的“意识的经验科学”这个提法的呢?
在“意识的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中,加了着重号的“经验”一词位于中间。它在意识与科学之间起中介作用。……只要我们还按照自然意识的习惯来读解这个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就还没有得到理解。“经验的”和“意识的”这两个第二格并不是指一个第二格宾语,而是指一个第二格主语。主语(主体)是意识,而不是科学。意识才是以经验方式存在的主体。而经验乃是科学的主体(主语)。(第205页,有改动)
在这里,海德格尔利用了黑格尔自己经常强调的主词和宾词的辩证法,即在辩证的理解中,主词和宾词是互相转化、互相颠倒的:宾词并不是主词的某种属性或关系,而就是以宾词形式出现的主词,是主词本身的变体或深化。例如“本质是过去了的存在”,也可以理解成“过去了的存在就是本质”,它们谁也不是谁的“属性”,其实就是一个东西。那么,“意识的经验的科学”既可以理解为“科学是意识经验的”,也可以颠倒地理解为“意识的经验是科学的”。“意识的经验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颠倒”(第196页,有改动)。然而海德格尔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的“颠倒”(Umkehrung,又译作“转化”)并不是随意地颠来倒去,而是有方向的,每次颠倒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逻辑层次;而“意识的经验的科学”最后就上升到逻辑学的层次。但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把“真正的科学”归结为“逻辑学”不满,认为“这个名称是从传统中拿来的”,它表明“关于这种概念的逻辑学乃是有关绝对的本体论上的一神论(Theiologie)。它并不像意识的经验科学那样陈述出绝对之在场,而是陈述出它在向自身在场中的绝对性”。(第205页,有改动)这就把逻辑学本身降为仅仅是对“意识的经验科学”的一种神学化的说明方式了。
海德格尔这一诠释显然违背了黑格尔全部哲学的体系结构,它不但无法解释黑格尔为什么最终抛弃了“意识的经验科学”这一标题——他猜测是由于黑格尔对“经验”一词“感到畏惧了”(见第208页)——更无法解释《精神现象学》本身在《哲学百科全书》中被贬为《精神哲学》的“主观精神”之一个环节的事实。他仅限于列出这一事实,未作任何说明(见第209页)。其实问题在于,黑格尔的意识经验当然可以成为科学,但科学不仅仅是意识的经验,它更不能停留于意识的经验,而是必须继续向上升。当它达到“绝对知识”、达到逻辑学上的“存在”概念时,这种科学就不再是意识的经验,而成为了纯粹概念即范畴。所以意识的经验在黑格尔那里虽然潜在地包含着绝对的主体,但绝对主体决不会满足于意识的经验,而是要在纯粹的形式中展示自身,这就是逻辑学。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阐释,用来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则可,用来把握黑格尔的思想则不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读懂黑格尔,而只能说他在黑格尔那里看见了他所关注的问题,因而“切中了被解释的本文所思考的同一东西”。
【注释】
①但黑格尔原文为:“wenn es(das Absolute)nicht an und für sich schon bei uns wre und sein wolte,……”(Heidegger,S.112),海德格尔在行文中对句子稍有调整(ibid,S.126)。孙周兴先生在上引中文本中将此译为:“(绝对)自在自为地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存在”,似有不妥,且造成后面多处不好理解。其实bei uns sein在德语中就是很普通的“在我们这里”的意思,不一定指“近旁”。以下凡引《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均只于引文后面括号注明孙周兴译本的页码;且凡注明译文“有改动”者,均依照上引德文本。
②此处Anwesen与前面也译作“在场”的Parusie为同义词,海德格尔经常将它们换用。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1997年:《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 校,人民出版社。
[3]Heidegger, 1980,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注: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代表著作《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