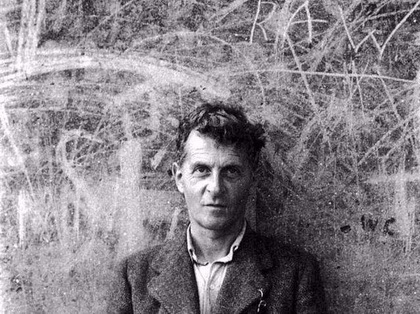作者:柳慕非
海德格尔在1927、1928年以《现象学与神学》为题作过两次讲演,讲演后,他随即对文本作了考订和补充说明。然而,过了四十年后,他才把1928年在马堡的讲演中题为《神学的实证性及其与现象学的关系》的第二部分整理发表,同时把他1964年3月11日的一封书信作为附录,那是他为一次关于《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的问题》的神学对话所作的主要观点的提示。两文合起来发表时题名仍为《现象学与神学》。我们的讨论便由此文本出发,也主要依据此文本展开。哲学网出品zhexue.com.cn
海德格尔之所以这时才把这两篇文章合起来发表,其中贯彻了他后来对待自己思想的一个基本态度,即:他关于所涉论题的一些观点,大都是些探索性的思路,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结论性的观点。他常常担心人们以常识想当然的所谓理论方式把他的一些表述看作可以固定概念来把捉的结论。他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其实不过是他思路上的路标。为了避免上述误会,他甚至认为一些问题只可对话式地面谈,而不愿直接诉诸书面文字(《论人道主义的信》)。因此,在这里我们试着把他事隔37年而又合着发表的两篇文章中的有关叙述,当作标示他漫长而又曲折的思想道路上的路标对照联系起来看。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引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这意思是说,对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思路,有所启发。我们大概不能,或许也不该希望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那会离他的意思太远。
文章前言的后三段,海德格尔提到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奥维贝克的《论我们时代的神学的基督教义》两本书,从而引出了一个话题。如果说,他注意到尼采书中道出了“美好的荷尔德林”,是海德格尔的个人偏好的话,他所说的后者在书中“把弃世的末日期待确定为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特征”,则点明了海德格尔这里所关心的话题。他认为,就是道他那个时代,这两本书也是不合时宜的。说它们不合时宜,是说,它们所涉及的话题对大多数人说来,也许毫无兴趣——如今也许仍是如此,大多数人被引导去追求的是有用和有利的十分现实的具体目的。尼采们所孜孜以求的,则只是对少数思想者——当然是无数精于利益算计的人(Rechnern)中间的少数思想者——才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他们“指示着那种执着,那种对不可通达的东西的道说着,追问着,建构着的执着”[1]。
信仰是海德格尔这篇文章里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
信仰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大概是因为,信仰自古以来就与人的生命及其终极意义相关,从而成为人最为关切,最为坚持,而又分歧最大的问题,如今由于信仰的泛滥着的缺席,问题变得愈发严重。时值今日,一方面似乎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提供给人们信仰的东西也五花八门,而人们对信仰的各自坚持却形成对立,信仰对立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形成的矛盾冲突越来越互不相容,越来越尖锐,信仰原是对人心灵中的时时的生命紧张的安抚,如今却常常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社群或族群之间的重大冲突的原因或借口;信仰冲突与利害冲突纠缠在一起,而人们在冲突当前时又往往极其小心地避免触动信仰这根固执、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另一方面我们人类的信仰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面对人类的其他精神生活,失去了魅力,越来越成为多余的装饰——不仅经常遭到置疑和蔑视,还使人们对信仰的坚持越来越少了固有的真诚。寻求真正的信仰成为一种几乎令人绝望的希望,建立一种信仰似乎成了很容易却又不那么简单的事情,坚持真诚的信仰成了莫大的困难。人类在无望中追寻信仰,信仰却在坚持的妥协中构建未来。
对当代人来说,信仰成了问题。原来笃信无疑的,现在变得不太可靠,不太可信,反而可疑了。不仅如此,本来依信仰来支持生命意义的人,似乎也不那么需要信仰,生命自身就可以充实。信仰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怎么了?难道真的“上帝死了,人什么都可以做”?对我们人来说,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和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人们通常是从信仰所相信的东西来规定信仰。对人来说,信仰是外在地被给与的,是天启的。人们往往当自己对理智不可理解的那些现象、力量、道理、事情而感到迷茫时会无所适从,信仰便出现了。信仰似乎并非由人而来。面对这种由信仰而来的流俗的解释,海德格尔也对信仰作了一个形式上的界定,好像有些不同:他把信仰规定为“人类此在(Dasein)一种生存方式”[2]。但是,这并非把上帝创造人颠倒过来说成是人创造了上帝那么简单。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个生存论-生存状态上的一般规定,是他进入作为基本存在论的此在生存论分析的起点。这还与他把作为信仰的科学的神学当作一种实证科学的看法相一致。在那里,他除了批评神学——当然是西方基督教神学——由于西方形而上学和西方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干扰堕落为实证科学外,他的意思还在于,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要求某个现成的存在者为对象,而它是前科学地已经实存着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并非抽象的概念分析,它要求一个实在的对象为起点,在这里就是实在的此在生存方式——信仰。
信仰并非唯由信仰所信的东西来规定自身。信仰首先和人类此在其他生命活动:劳动、科学、技术、艺术等一样,是人类此在的生存方式之一。人们当下讨论的信仰,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且是人在讨论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存现象。我们关于信仰的检讨就从这里开始。以此,他得以把信仰放到此在生存的原始基点上,得以开始对信仰作生存论的分析。这是海德格尔前期对其所关注的问题进行生存论分析的一般方法论起点。“向着事情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玄妙的事情,它首先要求的就是回到当下讨论问题的初始存在状态,从事情本身的原初现象出发,他在这里所寻求并发现的就是此在的信仰性生存本身。
然而,信仰非同一般的此在生存方式。海德格尔同时指出,信仰并非由本身之为此在生存方式而自由地依愿成其为信仰。其实,信仰是人类此在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信仰并非首先地,更不是唯一地按此在及其生存来获得规定的。信仰是由从这种生存方式中并随着这种生存方式公开出来的东西,也就是信仰所信的东西(Geglaubt)来规定自身的[3]。至此,海德格尔对信仰的界定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信仰作为此在的生存方式而是此在的信仰,另一方面,此在的信仰并非由此在自身来规定,而是从这种生存方式所揭示出来的东西那里获得规定。这种生存方式所公开出来的东西,之所以有这般规定的力量,海德格尔并未指认是因为它来自超验的世界,是神的启示,在他看来反而恰是由于其本身是一历史的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直接与此在的生存相关。而这样说的意思是,这一事件由于此在的信仰式的参与才向此在公开出来(即启示)的,更由于其历史的传达中的活生生的此在实现的参与而愈发成其为历史的事件。信仰所信的东西,信仰这种此在生存方式所公开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启示——由于此在的参与——并非外在于人类此在,此在——人,历史上实际地参与其信仰所信仰的东西的建构,也就分有它。信仰是此在的信仰,此在亦由于这种信仰式的参与而是信仰的此在了。
海德格尔这种关于人与其信仰对象的关系的理解和解释,把传统意义上的单向授受关系规定,转换为在张力状态下的互动性的描述。这一方面消解了信仰文本的神话性质及其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超验规定性。信仰在形式上,建立在此在生存的原始性基点上。人,当下而又是历史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此在,通过信仰而对信仰所信的东西的建构性参与,使得本来外在地指导和规定着此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超验世界自身失去了独立自足的超然的生命力。那个超验世界离开了人类此在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信仰自身的超乎信仰者的规定性领域被消除了,其存在的意义和根据要从现实的信仰此在的生存中去求得。我们可以把这在信仰中发生的现象与文化思想史中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社会学中的所谓“脱昧”现象,在解释性存在的意义上,看成同一个现象过程。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描述显示这样的现象过程至今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超验世界的神圣性权威的消失,使得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人的理性得以张扬和充分地发挥作用。人的主体性摆脱了超验世界神圣性权威的束缚。由于启蒙——无论人们如何批评它——恰恰是由于它,人们不再可能不经思考,不经反省的检验,便轻易信仰不可理解的东西。相比之下,启蒙这一历史现象发生后,人在把握事物时,越来越相信和依赖自身的思考和反思——如果我们对“理性”这个概念还有所保留的话。
然而,信仰与思的关系,远不是摆脱了超验世界的人类此在以简单的对象化、客观化方式所能把握的。信仰向来只在思由于力所不及而停止的地方出现,极端地说,信仰就是不思而获。信仰不但不要求思从外部的检验来确立自身,信仰还轻蔑思的无力并拒绝思。信仰中所敞开的东西也无须经过自由的思的论证才成为可信的。于是,海德格尔说,“信仰始终只在信仰上来理解自身。”[4]这意思是说,信仰对信仰的东西自有自身独特的把握方式和领会方式。信仰的把握和领会方式不同于此在的一般领会,它拒绝概念性解释,信仰状态中发生的启示事件,仅仅向信仰并且唯有通过信仰才敞开。信仰这种精神性生存活动,只是在信仰中,通过信仰才可实现。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那种以概念方式来理解和解释信仰及其信仰的东西的所谓信仰的科学——即神学——都在本质上与信仰不合,它缺少信仰以自身的方式来领会自身这样一个本质性环节。唯有按照信仰的实际内容及其特殊的存在方式,而且“唯如其在信仰中为信仰所表达自己的那样来把握”[5],才是我们领会信仰的恰当方式。
信仰自有其完全不同于通常理解方式的进入途径。因此,信仰是自足的,只有信仰被赋予更多的责任,要求它能够以易于传达的概念式表达而普遍被接受时,信仰的科学才需借助科学理性的概念方式。如此,信仰被当作理性的知识来传达,却已违背了信仰的本质。以信仰的自身特有的方式获得信仰的此在,便进入完全不同于信仰之前的生存状态,此在还是那个此在,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海德格尔说,这种信仰等于再生。
如今,寻求信仰的此在把再生的希望寄托在普遍可理解的知识性传达上,似乎有些“缘木求鱼”。海德格尔似乎也没有指明通向光明的希望之路。他只告诉我们,此在本是领会的此在,信仰的此在是以信仰方式领会地生存着的此在。经过了信仰的扬弃,此在领会着以前信仰的生存中的把捉来校正信仰科学即神学的表达。到了晚年,海德格尔指出这种领会并非对象化、客观化的表达所能及,他想的大概是那纯粹的存在之思吧。
注释:
[1] M. Heidegger: Wegmarke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Zweite, ung durchgesehene, Auflage 1978,p.46
[2] 同上,p52.
[3] 同上。
[4] 同上,p53.
[5] 同上,p57.
(作者系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