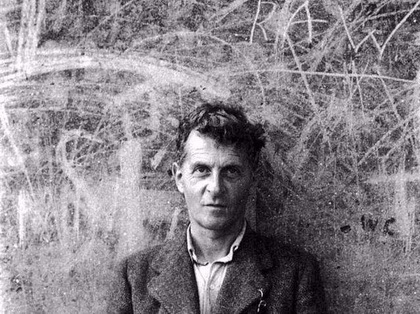雷良 蒋美仕
美国哲学家罗蒂的著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一经出版,便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从元哲学角度对欧美传统哲学进行激烈的批判与反思,以实用主义为依据建构了自己的“后哲学文化”理论,目的是要将哲学消解于文化之中。尽管这种理论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但他的这种努力却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本文试图对他的这种理论作一述评。
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罗蒂虽受教于欧美分析哲学的泰斗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奎因以及亨普尔等,但他却对传统西方哲学深怀不满,并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客观主义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发现“善于思索的人类一直企图按照两种主要方式使生活与更广阔的领域联系起来,从而使生活具有意义。”[1](407)第一种方式就是追求协同性,即人们通过在兴趣、目标、准则等方面的一致性来描述生活与真理,而并不牵涉到人与外物的直接关系。第二种方式则是人类在他们与外界现实的直接关系中描述自身的生存,它体现了人类追求客观性的愿望,即坚信真理是独立于或外在于人自身的客观实在。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启蒙时代的以追求真理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是企图由协同性转向客观性以使人类生活有其意义的典型例子。而“我们是这一客观主义传统的子孙,这个传统的中心假设是,我们必须尽可能长久地跨越我们的社会局限,以便根据某种超越它的东西来考察它,这也就是说,这个超越物是我们社会与每一个其他实在的和可能的人类社会所共同具有的。”[1](408)这一客观主义传统发端于柏拉图。柏拉图看来,感性生活与理智生活被一条宽阔而不可逾越的鸿沟所分离:知识和真理属于先验系列,属于一个永恒理念的王国,人的认识就是对理念的分有,而真理就是与这种外在与人的理念的符合(即与自然符合),知识则是对自然的正确表象。故哲学就是关于表象的一般理论。占有准确的表象就是获得知识、占有真理。这实质上乃是一种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点,把人当成自然界的一面镜子。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始将人的认识转向人的心灵,开创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此,这面镜子开始向内移动,认识在心灵中发生。知识成了外界实在的内在表象。康德致力于研究科学、艺术、道德的基础,并回答人的认识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发起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识确定合理的和客观的标准。此后的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都可以说是康德哲学的变种。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力图建立一种“严格的科学”——为其他科学评判和奠定基础的科学的哲学。而分析哲学企图对人的意义世界进行逻辑重建,把表象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而且,“对语言的这种强调,基本上未曾改变笛卡尔——康德的问题体系,因此并未真正地赋予哲学一种新的自我形象。因为分析哲学仍然致力于为探求、从而也是为一切文化建立一种永恒的、中立的构架。”[1](5)因此,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是以视觉隐喻为先导的。“心灵是一面伟大的镜子,它包含种种表象(其中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并能够用纯粹的非经验方法进行研究工作。”[1](9)全部传统哲学都发端以这个“心为自然之镜”的比喻。而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等人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
因此,罗蒂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镜喻”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对抗传统哲学的有力武器就是当代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第一,现代科学哲学表明,根本不存在中立的观察命题,观察渗透了理论,受到理论的污染,故客观的、中立的感觉材料也不存在,即使是所谓的科学事实,也不是在偶然的观察或仅仅在感性材的收集下所给予的。“科学的事实总是含有一个理论的成分,亦即一个符号的成分。那些曾经改变了整个科学史进程的科学事实,……都是在它们成为可观察的事实以前就已经是假设的事实了。”[2]这恰好有力地驳斥了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第二,奎因抨击了传统哲学关于“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指出并不存在康德所谓的“偶然”与“必然”的严格区分,摧毁了语言与事实的界限。在奎因看来,任何特定的陈述(命题)的意义都与陈述的整个体系和网络的其他陈述有关,不存在恒真性的必然的分析命题,分析命题与可真可假的偶然综合命题的区分亦不存在。而且,作为科学体系中之一部分的分析命题也回因体系内部的需要而修改,修改的标准是实用性原则而非它是否与“事实”相符。这样一来,“视觉隐喻”假说被摧毁、“心灵镜像”被打碎了。罗蒂随即用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取代传统的作为各种准确表象之集合的知识论。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的符合关系,而依赖于它所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和行动方式,取决于它的有用性或者说效用。
在“协同性”与“客观性”之间,罗蒂坚持的是“协同性”原则。他试图用此原则对抗传统的建立在主客、心物二元分立基础上的客观主义原则。在此原则下,传统的“心身问题”不复存在了。因此他说
“人类能了解他们自己的某些心理状态的事实,并不比他们经过训练能报道他们血液中存在肾上腺素、报道自己的体温、或报道在危机情况下缺血一事更为神秘。进行报道的能力不是‘出现于意识中’的问题,而只是教会使用字词的问题,教人们如何使用‘我相信P’这类句子的方式,与教会人们使用‘我发烧’这类句子的方式一样,因此我们没有特殊理由使‘心的状态’与‘物的状态’截然分开”。[1](436)
据此,个人与宇宙、心灵与世界、真理与信仰、语言与逻辑、理论与事实,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极力主张的“家族类似”。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人生活在“语言游戏”之中,“语言游戏”就是人的存在形式,而不同游戏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本质,它们仅仅是相似点重叠交叉的复杂网络:有时是大部分相似,有时是小部分相似。既然人与世界、心与物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区分,“心身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么,认识论的客观主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后哲学文化”理论的建构
抛弃客观主义的传统,由客观性转向协同性,并不表明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罗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构筑哲学的未来。
哲学是一个“撕杀的战场”。近代认识论哲学将之前的以神学为核心的“神话文化”驱逐出神圣的殿堂,使以认识论为核心的哲学成为人类思想史的新景观。这种认识论哲学认为只有它才能够达到外部的终极实在和永恒的终极真理,从而成为审查和裁判各种文化知识的法官。一种新的的神话从此诞生了,罗蒂称之为“后神话文化”。这种文化以哲学为中心,又可以叫做“哲学文化”。
罗蒂就是要摧毁这种文化,将“王者之尊”的哲学消解于他所倡导的新文化之中。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一代代哲学大师的批判宣告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死亡。不仅哲学不再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核心,而且知识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基础和核心。此时,哲学已经没有任何特权,成了“小写的哲学”。但正如宗教并未在启蒙运动之后走向终结,“哲学”一词也许永远不会终结,不过它必须改变自我形象和转换其活动方式。故这种新文化相应地称为“后哲学文化”。
如果说“哲学文化”相当于现代主义,那么“后哲学文化”则对应于后现代主义。在“后哲学文化”中,既无所谓的实在,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时代中“怎么都行”。“在这一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3]然而,失去了“王者之尊”的哲学被消解于文化之中后,哲学或哲学家还能干什么呢?在罗蒂看来,“后哲学文化”中的哲学或哲学家看起来干什么都行。但此时的哲学仅剩下两种主要功能——对话与教化。
罗蒂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心仪以久。因为这种解释学并不是作为“获得真理的方法”,而是以“意义”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的新方法。哲学解释学展现给人的是一幅 “效果历史”的巨大画卷,它强调历史性的、体验性的“理解”是保持和扩展那种既非人的感觉印象又非抽象概念的“意义”的独特方式。因此,它是“人的自我认识的科学”。
哲学既不是知识,也无法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因此,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不受任何东西(如实在、真理、善和合理性等)的限制,它是敞开的和开放的,没有标准,没有方法,也没有主题。”[4]因此,“后哲学文化”可以谈论任何东西,或更确切地说这种文化就是“谈论”或“对话”本身。通过各种范式之间的不断对话,调解和克服各学科和各学说间的分歧。而解释学的目标就是通过其媒介作用,促进对话的不断进行。但解释学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它并不以一切人或一切学说的普遍基础(即“可通约性”)为逻辑前提,恰恰相反,它的出发点是承认所谓时代差距或文化差异的那种“不可通约性”。一句话,并非由于存在着可通约的普遍基础才使对话成为可能,恰恰相反,正是以对话为前提,才能谈的上“通约”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因此,对话是一个不断克服不可通约因素的解释过程。哲学家就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调停者。
解释学的任务除了促进不同范式的对话外,它还担负着教化的职责。所谓教化,在罗蒂看来,就是令人们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有成效的谈话方式。当人们读的更多、谈的更多和写的更多时,就会成为不同的人,就能改造自己。当然,人类获得自身教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客观知识的追求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人在自身以外别无探求的目标,我们只是不断地在千方百计寻求谈论自身的各种新颖的、有趣的方式。谈论事物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可见,罗蒂是要把对话作为人类最普遍的活动方式,而认识只不过是对话中的一种声音而已。
由此,罗蒂勾勒出一幅“后哲学文化“的图景。所谓“后哲学文化”,就是对我们人类创造的各种谈话方式之利弊的比较研究。换言之,人们可以自由地批判和评论一切人类活动。哲学家的角色已转换成为文化批评家,其任务就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不同范式之间、在理解事物如何相关的各种尝试之间,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处。同时,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科学与文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已不复存在。科学仅仅是文学的一种体裁;伦理学也并不比科学更为主观、更为相对,更不需使之科学化。因为人们主张什么命题、看哪些图画、听什么叙述、评论什么叙述以及复述什么叙述,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们的目的有关(实用主义面目昭然若揭)。据此,哲学也无需在“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狭缝中为自己的身份而担忧了。哲学家成了“解释学的实践家”,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孜孜不倦地进行“精神助产”活动,将人类推进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三、结论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理论体现了他的哲学观,或者说植根于他的哲学观之中。其哲学观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本体论上的反实在论;二是认识论上的反基础主义。这集中反映在其实用主义真理观上。在他看来,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赖以存在的前提——观念与对象、语词与事物、语言与世界、命题与事态、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区分——已不复存在,建立在主客观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客观真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真理只与人们的目的有关。凡是符合人的目的、有效用的知识就是真理。西方哲学的客观主义传统被罗蒂扫地出门,“客观性”一词也被赶下了祭坛,取而代之的是对“协同性”的追求。但是,“客观性”和“协同性”是人们认识和描绘世界和自身的两种根本方式,二者缺一不可。尽管罗蒂也曾羞答答地承认客观性的探求是可能的,然而,其实用主义的倾向又使他明显倒向“协同性”一边。可见,在“客观性”与“协同性”的关系问题上,罗蒂的心态是矛盾的。也许他心仪已久的解释学可用来调和这种矛盾,但他自己又在这方面羞于启齿。实在令人遗憾。此外,作为实用主义的信徒,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难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
在罗蒂看来,“后哲学文化”实质上就是对话本身。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单极化趋势日益明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成了这场对话的“权利话语”。在这种情形下,罗蒂所倡导的对话实际上成了“文化殖民主义”的工具,其“教化哲学”实际上就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代名词。
罗蒂有关“后哲学文化”的思想理论,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首先,教育、教学活动,从根本上说,它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需要以某些传播为中介与受教育者进行心与心的碰撞。在此活动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活动的主体性上是平等的,因此,对话便成为顺利完成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保障。其次,教育、教学活动在世界各国范围内有着共同的规律和特点,但并不能据此而抹杀各国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有其特色的教育传统。随着西方各国的经济逐渐走强,共享的教育资源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日益不均匀,各具民族特色的教育传统也有“统一”的趋向。与此同时,教育强国依靠其有力的经济为后盾,以诱人的学习科学研究条件,不断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丰富智力资源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失去了赖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生力军,而愈显贫困。也就是说,在世界教育领域内,也存在着另一意义上的“南北问题”,对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将会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为此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即教育对话。
参考文献
[1]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74.
[3]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5.
[4]姚大志.现代之后[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271.
(原载于《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