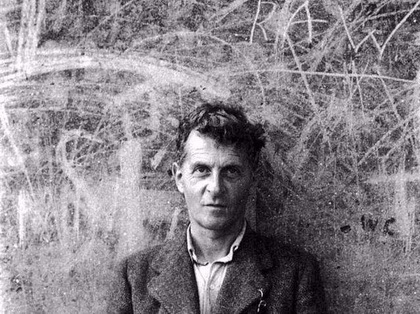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文/阿兰·巴迪欧︱伊索尔/编译
我认为,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这个问题很重要,谈起来也很难。更准确地说,是怎么样才能避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这就像把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新形式的绝对渴望,总是需要新的形式。现代性就是对新形式的无限渴望。而另一方面呢,迷恋身体,迷恋限定性,迷恋性,暴力,死亡。在这两个方面之间有一种相互矛盾的紧张感,就像是形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合题,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主流。下面我提出十五个命题,想回答这个问题:怎样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第一条命题:艺术不是一场崇高的降落,从无限降落到身体和性欲的有限的不幸,而是通过物质减法的有限手段生产无穷无尽的主体级数群。
我认为艺术的目的是通过精确并且有限的概括,去生产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光亮。所以,现在的矛盾存在于对新形式的无限渴望和诸如身体,性之类的有限性之间。而新的艺术有必要改变这一矛盾的语汇,为无限性这一方添加新的内容,新的光亮。所以,第一条命题几乎是对现有矛盾的颠覆。
减法:减法这个词有两个意思第一,不要沉迷于形式的新奇性。我认为,在今天,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新奇的渴望就是对新的形式的渴望对新形式的迷恋。对批判,对再现之类的迷恋,实际上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对新奇新颖的迷恋,就是形式的持久革新。我们有必要看到对新的形式完完全全地迷恋并不真是对真实世界的批判立场。有一种可能性,真正的愿望,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愿望,是对永恒的渴望。渴望某种稳定的东西,某种艺术,某种自身闭合的东西。因此,这是一个可能性,因为对形式的持续修订并不是真实的批判立场。所以说,对形式的渴望在艺术中的确很重要,但是对形式稳定性的渴望同样也很重要。
减法的第二个意思是不要沉迷于有限性,迷恋暴力,身体,痛苦,迷恋性和死亡,因为这只是颠覆了快乐意识形态。在艺术创造中,我们常常迷恋受苦的身体,性欲的艰难之类,以此颠覆这种快乐意识。我们不需要那一类的沉迷。艺术创造有批判快乐意识形态的必要性,然而,通过一个新的视野,一种新的光亮,某个可以称之为积极的新世界,也是一种艺术必要。所以,艺术的问题也是生的问题,而不总是关于死亡的问题,这就是第一个命题的含义。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艺术创新,它不迷恋形式的新奇,不迷恋残暴,死亡,身体和性欲。
第二个命题:艺术应当不只是一种特殊性(不论是种族的,还是个人的)的表达,艺术是向每个人说话的真理的非个人的生产。
这里的重大问题是普遍性:艺术创作有没有一种普遍性? 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是全球化,是世界的一致性问题。全球化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抽象的普遍性。金钱的普遍性,信息的普遍性和权力的普遍性。这就是今天的普遍性。这样一来,面对金钱和权力的普遍性,艺术的问题,艺术创造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艺术创造的功能在于对抗吗? 在于从普遍性中抽象出种种特殊性的独一性吗? 类似某种东西,对抗金钱和权力的抽象能力?还是一个反对全球化的社群组织?或者,艺术的功能在于提出一种别样的普遍性? 这是一个大问题。今天更重要的议题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金钱,权力市场的普遍性和各种独一性,特殊性,以及社会群体的本性之间的重大矛盾。这是两种普遍性之间的主要矛盾。一方是金钱和权力的抽象普遍性,另一方是真理和创造力的具体普遍性。
我的立场是,今天的艺术创造应该提出一种新的普遍性,不仅表达社群的本性,而且,艺术创造有必要为我们,为共有的人的状况,提供某种新的普遍性,我把它称之为真理。真理就是一种新的普遍性的哲学名字,它反对全球化的强制普遍性,金钱和权力的强制普遍性。在这项主张中,艺术的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艺术往往主张一种新的普遍性,艺术是第二个命题的内涵。
第三个命题:艺术是一个真理过程,而这真理往往是知觉或感性的真理,知觉之为知觉这就是说:知觉转化成了理念的一个事件。
这是艺术普遍性的一个定义。艺术真理是什么?艺术真理和科学真理,政治真理以及别种真理都不一样。它的定义说明,艺术真理是关于知觉的真理,是感性的概要。这不是静态的知觉传达。艺术真理不是感性世界的临摹或者静态的感性表达。
我的定义,艺术真理是理念自身在感性世界中的事件。而新的艺术普遍性在于创造,在那种感性之中的理念事件的新形式。重要的是必须理解,艺术真理是关于在世的感**的一项主张。它主张一种新的定义,关于我们和世界的感性关联,这是反对金钱和权力抽象化的普遍性的一种可能。所以说,今天,艺术看来尤其重要,因为全球化赋予我们一项创造新的普遍性的任务,它往往是一种新的感性,一种和世界的新的感性联系。因为今天的压迫是一种抽象普遍性的压迫,我们不得不沿着和世界发生新的感性关联的方向想象艺术。也因此,今天的艺术创造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而不是装饰,不是用于美化的装饰品。不,艺术的问题很关键,因为我们必须创造出和世界的新的感性关联。事实上,没有艺术,没有艺术创造,金钱和权力的强制普遍性就成了真正的可能性。因此,艺术问题在今天是一个政治解放的问题,艺术自身带有政治性。不仅仅是艺术的政治维度的问题,那是昨天的情况,今天,这是艺术自身的问题。因为艺术是真实的可能性,它创造某种新东西,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抽象普遍性。
第四个命题:艺术有必要是复数的,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去想象各种艺术可能交汇的路线,不能想象对这项复数进行总计叠加。
这个命题反对总体化的幻想。如今,有些艺术家在考虑熔合所有艺术形式的可能性,这完全是一个多媒体之梦。但这并非什么新想法。这是理查德•瓦格纳的想法,总体艺术,绘画,音乐,诗歌等等。第一位多媒体艺术家是瓦格纳。但是,我认为多媒体是一个虚假观念,以为它是绝对整合性的力量,就像在艺术中投射了全球化的梦想。这是艺术一致性模仿世界一致性的问题,它也是一种抽象化。所以,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艺术,当然包括新的形式,但是不该幻想所有感性形式的总体化。怎样和那些并非总体化的典范的多种媒体,意象的新形式以及艺术关联起来,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幻想。
关于第五条和第八条。五,每一种艺术都由一个混杂的形式发展而来,而这一混杂的逐步提纯的过程使一种特殊的艺术真理及其消亡殆尽的历史得以成形。八,艺术的真实也就是通过提纯的内在过程所构想出的理想化的杂多。换句话说,形式的一个偶然开端决定了艺术的原材料。艺术对于迄今为止形态不明的一个形式的降临进行了再度的形式化。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新形式的创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当代艺术的难题就是对新的形式的无限渴望。我们必须准确说明新形式问题的内涵。什么是新形式的发明? 我想提示的是,事实上,从来没有完全纯粹的新形式的发明。我认为那是一个梦想,就像总体化一样。事实上,从一种类似形式的东西到一种形式之间总有某种通道似的东西。我的想法是我们有某种形式的不纯,或混杂的形式,接下来是提纯的过程。因此,如果你想说上帝发明了世界,好吧,但接下来就是逐步地纯净化,然后是形式的复杂化。马列维奇画了著名的白色中的白色,白方块上的白方块。这是一种创造吗? 某种意义上,是的,但实际上,这完全是形状和颜色关系问题的一次彻底的纯净化。实际上,形状和颜色关系的难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长故事,马列维奇的白方块上的白方块给了这个难题终极的净化。这是一种创造,但也是一个终点,因为在此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再也无法继续。所以,我们有一次彻底的提纯,在马列维奇之后,形状和颜色之间的一切关联性看起来都陈旧了,或者不纯净了,但是,这也导致问题走进死胡同,我们不得不从别处重新开始。我们可以说,伴随着艺术创造的并非完全是新形式的提纯,就像是由始至终的提纯净化过程似的。所以,我们要的是有先后顺序的提纯净化,而不是纯粹创造力的纯粹爆发。这就是第五和第八个命题的内容。
现在来说一说第六条和第七条。第六条,艺术真理的主体是由艺术作品构成的那个集合。第七条,这个组织过程是一个无限的构造,在我们当代艺术的背景中,这是一个一般的整体性。
这里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艺术的主观存在? 什么是艺术的主体,在主观意义上的主体?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古老。艺术的主体是什么? 艺术的中介是什么? 艺术的主体不是艺术家。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很重要。因此,如果你认为艺术创造的真正主体是艺术家,你就把艺术创造当作了某个人的表达。如果艺术家是主体,那么艺术是那一个主体的表达,因此艺术就是某种个人的表达。实际上,当代艺术有必要争辩,说艺术是个人的表达,因为你缺乏创造普遍性的新形式的可能性,所以你不得不通过自我表达和社群表述来反对普遍性的抽象形式。这样一来,我们理解了各个难题之间的关联。
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说明的是艺术创造的主体不是这样的艺术家。对艺术来说,“艺术家“是一件必需品,但不是一种主体的必要性。因此,结论相当简单。艺术的主体存在就是艺术作品,此外无它。艺术家不是艺术的主体代理人。艺术家是艺术中被牺牲的那一部分,也是最终在艺术中消失的那部分。艺术的伦理就在于接受这一种消失。艺术家通常总是想要公开露面,但对于艺术,这不是一件好事。对于艺术,如果你希望艺术在当下,在创造普遍性的活动中获得一种极其重要的功能,如果你认为艺术差不多就是市场的主体性表达,那么,理所当然,艺术家的隆重出场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艺术是创造,差不多是秘密的创造,如果艺术不是市场的玩意儿,而是市场普遍性的阻力,那么艺术家就必须消失,不要在媒体中出现。艺术批判和对绝望的批判很像。如果艺术的伦理看起来是一种绝望,那是因为得到展示的是艺术作品,这才是艺术自身真实的主体存在。
第九条,当代艺术的箴言是不要成为帝国的这也意味着:如果民主暗示了和帝国观念中政治自由的一致性,它也不必是民主的。
我不想多评论为什么艺术的伦理是不要成为帝国艺术。绝望是因为总是存在类似于帝国的运作机制,因为有效的法律,在当下,就是帝国的法律。
关于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第十条,非帝国的艺术必须是抽象的艺术,就这一点来说:它把自己从一切特殊性中抽象出来,把抽象这一姿态形式化。第十一条,非帝国艺术的抽象化不关心任何特殊的公众或观众。非帝国艺术和一种贵族式的无产阶级伦理联系在一起:它单独地实践它的诺言,对人群不加区分。
我想我们可以说明,在当下,帝国艺术就是可见的东西的名字。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就是帝国艺术。这是一个历史命题,也不妨说是一个政治命题。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混合就是帝国艺术。今天是这样,而且,举例来说,罗马帝国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状况和罗马帝国晚期很相似。这是一个正当的比较,而且你们看,把美国和罗马帝国比较尤其准确。这样一比就相当有趣,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因为晚期罗马帝国的艺术创造中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方面,非常像浪漫主义,有表现力的,狂暴的,而另一方面,某种极端形式主义的东西,政治上的坦率正直。为什么? 当我们处理类似于一个帝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不妨说是在处理这个世界的形式一致性,不仅是美国,最终是庞大的市场,当我们有了类似世界的潜在一致性的东西时,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就有了形式主义和浪漫主义,有了两者的混合。
为什么? 因为有了帝国,就有了两条原则。第一,一切皆可能,因为我们有巨大的潜能,有世界的一致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皆可能。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形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言,并没有真正的法律,规定什么是可能的,什么不可能,一切皆可能。然而,我们还有另一条箴言,一切皆不可能。当代艺术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一切皆可能,并且一切皆不可能。那就是当代艺术的真实内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说明有些东西是可能的,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也不是一切都不可能,然而有一些别的东西是可能的。某些别的东西是可能存在的。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可能性。
但是,发明新的可能性不同于实现一个新的可能性。这个区别是关键的,实现一个可能性意味着设想可能性是现成的,我要做的不过是想象这个可能性。比如,一切都有可能,我就必须实现什么东西,因为一切皆可能。然而,创造某些东西的可能性显然是另一回事。可能性不是现成的。因此,一切皆可能不是事实,有些事情并不可能,而你必须为那些不可能的东西创造可能性。这就是艺术创造的重大问题。艺术创造是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呢,还是发明一种新的可能性? 说出某种东西可能性的可能性? 如果你认为一切皆可能 (也就是认为一切都不可能),那么你对世界的信念就完了,世界就是一个封闭的东西。它带着一切可能性,也就是带着一切不可能性被封闭了,而艺术创造性也就被封闭了,它在确认一切皆可能,一切皆不可能的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中被封闭了。
然而,今天的艺术创造,它的真实功能就在于说出某些东西的可能性,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但是,某些东西似乎没有可能性,我们又如何为它开创一种可能性呢? 正因为某些东西本身没有可能性,我们才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果一切皆可能,你就无法创造任何新的可能性。所以,一种新的可能性的问题也就是某些事物不具有可能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设定一切皆可能是不真实的,而且一切皆不可能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有些东西不可能,我们就必须说这些东西不可能。我必须创造新的可能性。这样,我认为,创造新的可能性就是今天的艺术的重大功能。在流通,信息交换,市场等等活动中,我们总是不断实现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无穷无尽的实现着种种可能性。但是,我们拒绝创造可能性。因此,这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政治的真实含义在于创造新的可能性。一种生活的崭新可能性,这个世界的崭新的可能性。因此,今天艺术创造的政治决定性就在于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化给出的信念是,彻底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认为共产主义结束了,革命政治结束了,即给出了关于这一切的主流解释: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在于实现一种可能性,关键的是创造一种可能性。我们理解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艺术创造的问题就在于此。它向每个人证明,对于人的共有的状况来说,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
第十二个命题,非帝国艺术必须像数学范例一样严密精确,像黑夜伏兵一样令人惊讶,像星星般崇高肃穆。
这是一个诗学命题。艺术创造的三重决定性。把艺术创造和一次演算示范,黑夜中的伏兵以及一颗星星相提并论。你可以理解这三重决定性。为什么是一次演算示范? 因为,最终,艺术创造的问题也是关于某一个余数,某一种具有永恒性的东西,某一种不在纯粹传达,纯粹流通之内的东西,某一种不属于持久更新的形式的东西。它拒绝,而拒绝也是今天的一个艺术问题。拒绝之物是被赋予了稳定性和坚固性的东西。有逻辑等式,有逻辑一致性,连贯性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第二个决定性是某种令人惊讶之物,无疑是新可能性的创造,而新的可能性总是令人惊讶。没有某种惊讶,就不会有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加以估算。它就像一种决裂,一个新的开端,总是令人惊讶。这就是第二个决定性。它如此不可思议,就像黑夜中的事物,在我们知识的黑夜之中。一个新的可能性对我们的知识而言是绝对的新,所以,在我们知识的黑夜,它就像一道新的光芒。和星星一样崇高肃穆,因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犹如一颗新星。就像一个新的天体,一个新世界,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和世界的一种新的感性关联。
然而,重大的问题在别处。对当代艺术来说,形式问题不是一个决定因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三者一个接一个地联接起来。成为星星,成为伏兵,成为一次演算示范。由此,创造一种艺术的新形式,世界的一个新视野,我们的一个新世界。而且,这个新的视野并不是纯粹观念性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完全是政治的,这个新的视野有它特有的形态,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可能性,为新形态的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知识。
最后一个命题,为了那些帝国业已承认其存在之物,为了使它们变得可见而添砖加瓦地发明各种形式和方法,还不如什么也不做。
我想,这里重大问题在于艺术和人的状况之间的关联。更准确地说,艺术创造和自由之间的关联。艺术创造独立于民主意义上的自由之外吗? 我们应该不把创造新可能性的论题完全等同于自由的问题,就常识而言。因为今天,自由是由帝国来定义的,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定义。艺术创造和那种自由相差无几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艺术创造的真实决定性不在于关于自由的常识,也就是帝国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去创造具有新的形式的自由,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逻辑框架,新知识的惊讶以及星星之美,这三者的连接是自由的新定义,它比"民主"决定的自由要复杂得多。
艺术创造,对我来说,就是在民主定义的自由之外,创造一种新的自由。我们可以这样说起类似于由艺术定义的自由,它是思想的,也是物质的,就像逻辑框架之内的共产主义,因为没有逻辑框架就没有自由,就像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可能性,新的决裂,最终类似于一个新的世界,一道新的光亮,一座新的星系。这是由艺术定义的自由。当今的问题不在于艺术讨论中涉及的自由和专政,自由和压迫的问题,在我看来,根本上,在于自由自身的两种定义。
附:当代艺术的十五个命题
第一:艺术不是一场崇高的降落,从无限下降到身体和性欲的有限的不幸而是通过物质减法的有限手段生产无穷无尽的主体级数群。
第二:艺术应当不只是一种特殊性(不论是种族的,还是个人的)的表达艺术是向每个人说话的真理的非个人的生产。。
第三:艺术是一个真理过程,而这真理往往是知觉或感性的真理,知觉之为知觉这就是说:知觉转化成了理念的一个事件。
第四:艺术有必要是复数的,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去想象各种艺术可能交汇的路线,不能想象对这项复数进行总计叠加。
第五:每一种艺术都由一个混杂的形式发展而来,而这一混杂的逐步提纯的过程使一种特殊的艺术真理及其消亡殆尽的历史得以成形。
第六:艺术真理的主体是由艺术作品构成的那个集合。
第七:这个组织过程是一个无限的构造,在我们当代艺术的背景中,这是一个一般的整体性。
第八:艺术的真实也就是通过提纯的内在过程所构想出的理想化的杂多换句话说,形式的一个偶然开端决定了艺术的原材料,艺术对于迄今为止形态不明的一个形式的降临进行了再度的形式化。
第九:当代艺术的箴言是不要成为帝国的这也意味着:它也不必是民主的,如果民主暗示了和帝国观念中政治自由的一致性。
第十:非帝国的艺术必须是抽象的艺术,就这一点来说:它把自己从一切特殊性中抽象出来,把抽象这一姿态形式化。
第十一:非帝国艺术的抽象化不关心任何特殊的公众或观众,非帝国艺术和一种贵族式的无产阶级伦理联系在一起:它单独地实践它的诺言,对人群不加区分。
第十二:非帝国艺术必须像数学范例一样严密精确,像黑夜伏兵一样令人惊讶,像星星般崇高肃穆。
第十三:今天,艺术只能以 - 对于帝国(帝国)来说 - 不存在的那个出发点为起点通过它的抽象化,艺术使这一不存在变得可见,这一点应该统领每一种艺术的形式原则:努力使人人都能看到对于帝国(因而延伸到每一个个人,虽然是通过不同的观察角度)来说不存在的东西。
第十四:既然它对自己的能力信心十足,通过支配着商品流通和民主沟通的各项法律控制了可见的和可听的全部领土,帝国再也不审查任何事物一切艺术,一切思想,在我们获得消费,交流和享受的许可之时就被毁掉了。我们应该成为我们自己最无情的审察员。
第十五:为了那些帝国业已承认其存在之物,为了使它们变得可见而添砖加瓦地发明各种形式和方法,还不如什么也不做。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