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M+,摄影:Virgile Simon Bertrand,© Virgile Simon Bertrand,图片由Herzog & de Meuron提供
伴随香港宣布于4月21日起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的措施,由于疫情而在今年年初宣布闭馆的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M+)于4月末重新向公众开放。
采访/叶滢、胡炘融
撰文/胡炘融
2022年是皮力从北京来到香港M+担任希克资深策展人的第十年,这也是M+从无实体的、游击式的项目筹备到最终占地65,000平方米的视觉文化博物馆建筑在西九文化区落成并于2021年11月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变化的十年。
2012年6月,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Uli Sigg)将其收藏的总价值1.7亿美元的共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捐赠给M+,使M+从一家正在筹备中的艺术机构转而成为艺术世界举足轻重的参与者。1463件见证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四十年及社会变迁的藏品进入到一座背靠中国内陆,面向亚洲及世界的公立视觉艺术博物馆中,“M+依靠香港的制度灵活性,构建起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能够对它们公开地进行展示,并进行自由的策展表达以及藏品的管理和保护。一段珍贵的历史能够被保存、被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皮力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说。
从2012到2022年的十年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香港的社会环境、M+的功能及藏品扩充都发生着迅速改变,“没有哪一个十年像现在这样不断发生如此多的事情,M+在这十年里建立起自己的美术馆建筑、策展团队、藏品、数字平台,挑战很大。”在这十年间,M+与华人相关的藏品从最初希克捐赠的一千余件增加到现在的三千余件,时间线向两端蔓延,藏品数量和内容持续扩充。在作为策展人对希克藏品进行研究、梳理、增补的同时,皮力也从2019年开始同时担任M+策展事务主管的工作,负责视觉艺术、建筑、影像部门的展览、交流、运营事务。
希克藏品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见证,对希克藏品持续十年的研究与扩充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潜流、盲点与未知的未来不断探索的过程。在与《艺术新闻/中文版》的对谈中,皮力从M+开馆展“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说起,在其中谈及视觉文化博物馆的研究视角、工作方法和对于新问题的发现与思考,以及自己在这十年之变中的身份转化与个人感触。
.jpg)
▲M+希克资深策展人及策展事务主管皮力博士,摄影:Winnie Yeung @ Visual Voices,图片由香港M+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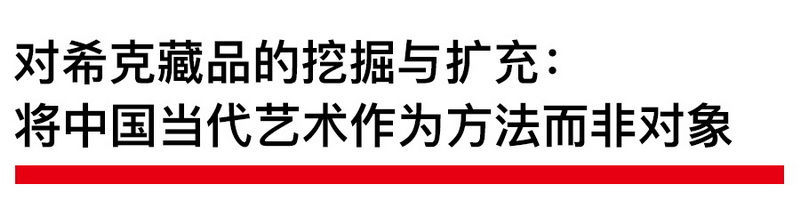
Q:希克藏品在整个M+的馆藏与研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A:我们称之为“backbone”(脊骨)。希克收藏涵盖了1972年到2012年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跨度,这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不是全部。任何藏品都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我们现在的工作分两头展开,一头是延续2012年以后的收藏,一头是填补原来希克藏品里没有涉及到的地方,包括新的研究和对历史的发现,例如早期的观念艺术;以及海外华人艺术。此外还包括我的同事们在做的工作,例如前M+水墨策展人马唯中不久前促成的来自赵善美女士的赵无极作品捐赠,这属于对早期现代主义的收藏。希克藏品就像一粒种子,它在不断向两边和上下生长。
与此同时,我们在工作中不再将艺术史视为唯一的关注领域,而是希望将艺术史和包括设计、建筑、流行文化在内的视觉艺术打通。我们希望将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当成一个方法,而非通常所说的对象,同时研究它和全球艺术之间、和其他视觉文化门类之间的关联。
Q:将中国当代艺术作为方法和作为对象之间的区别具体如何体现?
A:作为一个对象,你是将它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起因、经过和结果。在这里你永远仿佛要找出谁是最重要的艺术家,谁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艺术家,哪件是最重要的作品。
如果我们将它作为一个方法来研究,则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在整个现代主义的发展中扮演的环节。例如,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抽象艺术中,情绪性的抽象会多一些,冷抽象则少一些。而从三十年代到现在,超现实的内容在中国出现得特别晚。这些脉络和亚洲其他国家中出现的脉络是怎样的关系?中国的艺术在吸收、容纳、接受这些脉络时,它的方法、路径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现实主义传统很强,在具象的、叙事性的表达上有很强的基因,这些因素对此后观念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导致了中国艺术十分特殊的面貌。
另外,在中国当代艺术对艺术的理解中,包含了中国传统观念中成教化、助人伦的部分,这一部分加之社会主义的资源,造就了中国当代艺术在语言表达上很强的叙事性。这和日本、韩国这些冷战时期在不同阵营的亚洲国家很不一样。我们对传统经常采取的是不破不立的态度:在一段时期后就要将它摧毁,然后诞生一个新的东西。
在这些上下文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研究出许多中国艺术的形态。将中国当代艺术当成一个方法来研究,它就成为了一个我们看事物的滤镜,我们能够重新在一个全球文化的路径里来捕捉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人们经常说,中国当代艺术在八十年代将世界艺术全部重演了一遍,真的是这样吗?就算我们认定这是“重复和模仿”,它是否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这个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上下文关系是怎样的?这是我们在研究上一些不同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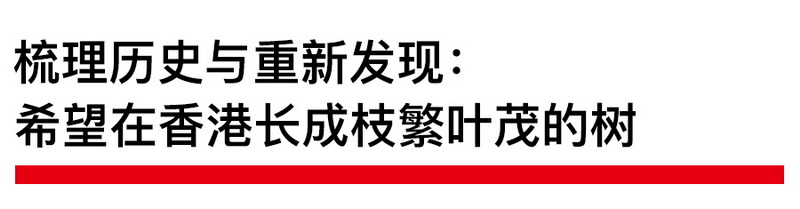
Q:2015年,在M+还未落成之前,你们曾从博物馆收藏中挑选出八十余件藏品在太古坊的Artistree做过一个展览,按照时间顺序组成展览“M+希克藏品: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这次的开馆展“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也依然是以时间为主线。编年叙事对梳理希克藏品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A:开馆前的展览和M+现在的开馆展都是以编年为线索,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另外一个艺术机构,能像M+这样有条件相对完整地来描述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一段历史从来没有很好地被梳理过,能够公开讨论的东西越来越少,每一代新的艺术家出来,都好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自己摸索。但是我们很有幸能把这一段历史保留下来,并给公众看见。
中国艺术这么多年的发展,像是在一个没有历史梳理的环境中不断生长的东西,就像是在一根营养非常丰富的木头上不断长出的许多蘑菇。历史应该是一棵树,能不断有枝叶发展出来,我们希望成为那枝树干。但我并不认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是唯一的、权威的,而是更多地在抛砖引玉,我相信更多的同行在看到这些藏品之后,对于艺术史的梳理会越来越不一样。
Q:M+的开馆展“从大革命到全球化”的编年叙述是怎么展开的?你们在这其中希望强调的关键结点有哪些?
A:这个展览将中国所谓的当代艺术的上限再往前推。我们以前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叙事,会将1976年文革结束后,活跃于1979年的星星画会作为第一拨艺术自由、言论自由的起点。但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将许多早期艺术创作的萌芽拓展到了1972年、1974年包括无名画会等在文革后期出现的团体和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中已经包含了许多自我表达、自我发现的成分,以及与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非常不一样的实践。
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将1979年作为一个叙事的开始?因为1979年这个叙事是和邓小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这里作为一种反对文革集权文化的新的文化被带出,并因此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当然,中国艺术和主流一直是对抗的,这种合法性非常脆弱。但久而久之,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叙事结合在了一起,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叙事是不准确的。过去五六年里,许多研究者和机构开始对这种历史叙事产生兴趣,我想一方面是由于对于已有历史叙事的这种怀疑,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十年间,中国艺术的发展变化太迅速了,对当下的不确定转而让人去寻找历史中的脉络。
第二,我们在展览中着重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里观念的成分,这从八五后期开始,包括了吴山专、谷文达、倪海峰、张培力这些艺术家,探讨他们的创作怎样引发了后来1980年代末的众多行为艺术。我们的一个重点是将八五新潮分为1987年以前和1987年以后。1987年以前的创作实践还处于一种自发的、朦胧的、超现实主义的、聚焦于生存的表达和聚焦于真理性的焦虑上。1987年之后,这种焦点突然变了,开始越来越观念化,从早期非常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的表达很快转向为包括1987年厦门达达、池社、吴山专等人那种非常观念化的梳理。
第三,九十年代的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际对中国艺术的理解,但在89年现代艺术大展中,是观念艺术的那部分激发了后来九十年代早期的一系列创作,包括张培力、宋海东在上海做的“车库艺术展”,以及后来耿建翌做的一系列展览实验、邱志杰的录像艺术,以及北京的朱加、宋冬、尹秀珍的创作。这些观念艺术是在九十年代初玩世现实主义同时期,作为一种逆商业化、反玩世现实主义的潮流出现的。因此,我们希望强调九十年代社会内部的这种张力。
我们关注的第四点是中国艺术怎样看待传统。这包括徐冰对于传统的解构、谷文达对文字书法的批判,到后来胡晓媛、洪浩等艺术家主动对传统的回归、将传统当作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谈论这四十年间中国艺术家对待传统的态度怎样发生了变化。
总而言之,我们在尝试将四十年间原本漂浮在表面的一根线索之下被掩盖的东西慢慢打开,在其中看到当代艺术的场域里不同的话语、力量之间的交战、竞争、妥协和最后综合发展出来的面貌。
Q:M+与华人相关的藏品从最初希克捐赠的一千余件增加到现在的三千余件,占总体馆藏数量的将近一半,从接收希藏品到现在,M+在此基础上做了哪些方面的补充?
A: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扩充是海外华人的部分。90年代后期的全球化图景迅速展开,这一代的中国艺术家和世界上任何地区一样,有许多都呈现着流动的状态,例如刁德谦、黄永砯、杨诘苍、陈箴等等。因此,在过去几年我们完成了许多海外华人的专题性收藏。
另外一块的增补是我之前谈到的观念艺术。我们很有幸在2014年得到了收藏家管艺的一批捐赠,接收了共37件能够反映上海和珠三角地区观念艺术的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
第三块是对2012年之后时间上的延续。我们因此很激进地收藏了许多在当下十分重要的艺术家,例如郝量、沈莘、于吉、崔洁……过去十年活动在艺术现场里的艺术家我们全部都有收藏。这部分收藏我们主要通过在2018年成立的“M+新艺术委员会”实现。“M+新艺术委员会”邀请到十余位重要的收藏家,每年通过两次开会讨论,对40岁以下、没有被M+收藏过的大中华区的新锐艺术家在过去五年内创作的作品进行收藏,并捐赠给M+。这也是年轻华人艺术家进入M+收藏的唯一通道。
对于年轻华人艺术家的收藏,我们先把这些重要的作品收集起来,以获得对艺术现场的记录。我希望我们将来能有一个展览聚焦2008年以后的中国艺术现场。我一直认为2008年是一个非常大的分野岭,我们在未来会越来越看到它在重新改写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商业力量的钳制、社交媒体带来的人们谈论政治和艺术方式的变化、批评和出版的衰落等等,这都对艺术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最后,现在新出现的一个版块是对早期现代主义,包括刘国松、赵无极、曾海文等艺术家的创作在内的收藏。这些战后的抽象艺术既和东方美学有关,又和整个战后日韩的抽象艺术、单色画、具体派连接在一起。

Q:与扎根中国内地的本土机构相比,您认为在香港M+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梳理工作,它的优势与限制有哪些?如何消除或者缩减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由文化、社会环境不同所产生的距离感,以深入大陆本土的艺术生态并与之建立连接?
A:一国两制的制度有它的灵活性。M+建构起这么大的一个收藏,并且基本能够公开地对它们进行展示,我们策展的表达自由、藏品的管理和保护都能在一套制度下进行,这是它好的一面。我希望M+是对每一个中国人开放的视觉文化博物馆,这一段珍贵的历史能够被保存、被看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近年香港和大陆的旅行受阻,但我们在通过一些项目努力降低我们和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隔阂。这主要包括三个途径:一是于2019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希克奖。我们将国内的研究者邀请过来进行讨论,邀请艺术家来举办展览,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场,表明我们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局限,并试图去超越它。第二是“希克中国艺术研究资助计划”,也是两年一届,支持聚焦中国艺术的全新研究。第三就是我之前提到的“M+新艺术委员会”。今年我们也在计划很多新的研究题目,希望未来与中国大陆的学者一同展开研究。
另一个挑战是,香港近年变成一个很政治化的地方,视觉文化博物馆变得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环境有时候会从另一个角度影响我们公正、客观、在一定距离下来梳理中国的艺术现象和整个视觉文化的发展。
Q:M+是一个地处亚洲,面向全球的视觉文化博物馆,除了面向中国内地的当代艺术环境展开工作之外,如何面对海外艺术界来解释和传达希克藏品及其艺术内核?
A: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属于国际上几个大型美术博物馆中唯一一个身处亚洲的视觉文化博物馆。我们依然在讲当代艺术、当代世界文化的故事,但我们是在东亚这个现场,我们会拿出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的眼光和叙事框架。
第二,我们谈到全球化的艺术史,更多是站在不断扩展的南方概念上。香港本身地处在一个南方的位置,现在很多中国的美术馆也在关注南方。南方不光是一个地理和经济上的概念,更多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
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是在反问西方中心主义,但当你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会发现一种潜在的中国中心主义。我们谈中国和西方,不谈中国和日本、和印尼,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外国。所以这些年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和我们同事都在规避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问题,这和我们在九十年代经常强调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在研究艺术的时候,越来越超越之前所提到的把中国艺术作对象的叙事。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家一样,在21世纪必然面对人类许多共同的问题。而中国过去四十年特殊的政治结构仿佛把中国艺术家关注全人类共同问题的权利给剥夺了,但实际上,今天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是一个艺术家无法回避的,比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数字文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也是M+在未来会很关注的方面。

Q:十年之前你选择结束在北京的工作,来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和全新的工作环境,现在的M+是否符合你当时对它的想象?从作为策展人对博物馆藏品展开研究和展览工作,到作为管理者投入到博物馆的各种组织和规划事务中,这种角色变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观察和感受是什么?
A:在M+开馆前,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但直到2021年开馆那一天走进博物馆,我发现它比我十年以前想象的要大很多。走进大堂的体感是超过MoMA、Tate Modern的。
到今年7月,我来香港就是一整个十年了,M+从2012年到去年11月12日博物馆向公众打开大门,我们忽然变成了一个有具体运营形态的空间,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观众。我们能带给观众什么?观众怎样看待你的这些作品?这和我原来做独立策展人时非常不一样。作为独立策展人,过去一个展览开幕,开一个研讨会,最多中间再穿插一次讲座。博物馆现在一个礼拜开放六天,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每天无时无刻都在面对观众。
M+的开馆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香港视觉文化的陈列,这个表达也是对香港艺术的一个提炼。这十年来,人们对M+的评价在不断发生变化,近年来很少有人再像十年前一样,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想在这其中M+起到了它的功能。我们每天一万多观众,这个视觉文化博物馆从此以后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任何一个展览都是十八个月以上的固定陈列,它已经成为你的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与其我们抽象地谈把哪些艺术家带到了国际现场,我们不如谈这样一个视觉文化博物馆给这座城市的未来、给这个城市的市民带来的更多文化上的可能性:激发他们对香港之外的、当下之外的文化和艺术的好奇心。
这也是我这十年最大的收获。博物馆的规划、运营、对观众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修复、保护、收藏方面制度性的建设,这些都是我当年没想到的,也是我在过去十年收获最多的。它们也是我觉得未来M+和我最能够为中国贡献出来的:它们是除了围绕藏品、艺术和视觉文化的研究工作之外,我们能够带给中国文化现场的最积极的部分。
M+正在展出
“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
展至2022年10月7日
“香港:此地彼方”
展至2022年11月27日
“安东尼‧葛姆雷:亚洲土地”
展至2022年7月3日
“纳里尼·马拉尼:视界流动”
展至2022年7月31日
“博物馆之梦”
展至2022年9月18日
“物件·空间·互动”
展至2023年5月21日
“个体·源流·表现”
展至2023年2月5日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