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后人文和艺术的思考走向
文︱朱其
每一次大的影响全球的世界性事件,都会导致人文和艺术的深刻转变。就如20世纪的思想和艺术的巨变,发生于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与两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关系。但1980年代以后,一些重大事件,从前苏联解体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并未如事先预料的引发哲学和艺术的深刻改变。这次持续近两年半的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以及俄乌战争导致的新冷战,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基本格局以及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是否会引发一次文人和艺术的转型?
前苏联的解体,不仅未给人文和艺术带来变革,相反造成了长达30年的搁置性的停滞。虽然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失败了,但民主资本主义也并非完美无缺。此后,除了对乌托邦、大毒杀及其理性绝对主义的反思,人们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失去了想象的热情。离开了这一未来的思想和希望的慰籍基础,任何与总体人文主义相关的思考,因此就缺乏了想象力。
取而代之拉动人文和艺术想象的动力,意外的来自硅谷的量子力学、芯片和网络科技为基础的技术以及生物基因学和生态主义。当代艺术的语言方式,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概念艺术、贫穷艺术以及新媒体影像,有时甚至好莱坞科幻影视剧的想象力甚于当代艺术,这得益于量子力学、平行宇宙以及基因学提供了剧本叙事上在时间空间以及后人类等新的概念。事实上,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人们也不再以意识形态和制度变革的讨论为中心,而是着眼于技术革新和扩大全球化分工带来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变化。
柏拉图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告一段落
由18、19世纪的乌托邦到20世纪初的左翼艺术,前者像威廉·莫里斯、卢那察尔斯基,将艺术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主要看作一种日常生活的艺术设计化,尤其是威廉·莫里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看作一种浪漫主义的田园时代的手工艺人的自足生活。这是出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的劳动分工的“异化”概念,即卓别林在《摩登时代》影片中所讽喻的,现代工厂让一个工人只做生产中某一拧螺丝的工作,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是一种人的“异化”。人在劳动中的幸福,在于像农民那样参与了一个从播种到收成的全过程,或者像手工艺人那样,日常生活用品不仅是自己亲手制作,而且从建筑、服饰和用具都被艺术设计过。
左翼艺术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列宁主义的产物,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和艺术的首要功能是为党的事业的鼓动和宣传服务,早期就是宣传艺术和反映阶级视角下的底层生活以及在反抗过程中萌芽的“新人”特质。左翼文学和艺术在19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同时,葛兰西的理论率先酝酿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转型,他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通过暴力革命的政权更迭不再现实,可以通过宪政的选举政治实现社会变革,在资本主义政治的框架下,知识分子应该介入大众文化的话语争夺,一旦获得了大众话语权,就意味着获得了议会选举的选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及其宣传艺术的议题,转向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即有关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的符号学及审美异化、文化的身份政治等文化政治和美学政治的“新马克思主义”。
在法兰克福学派由阿多诺和本雅明代表的对文化工业的审美操纵以及艺术品作为商品的成批生产的神学批判之后,新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与索绪尔的符号学、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合流,主导了战后跨学科的文化和艺术理论的基础议题,包括女权主义、酷儿理论、消费社会批判以及后殖民主义。众多在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判、文化研究、印度庶民研究等名义下的泛文化理论,实际上都可以归在新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分支:身份政治和消费社会,前者包括女权主义、酷儿理论、黑人权利以及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义关于边缘身份的表达以及在文化上的话语建构;后者则是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到战后法国哲学的文本结构主义的消费符号学以及情景国际主义的景观社会批判。
纯艺术在20世纪经历了从抽象艺术到概念艺术,及其东方主义分支抽象表现主义的书法派和受禅宗影响的偶发艺术。这一基于几何学和柏拉图主义的先锋派现代主义,至六、七十年代告一段落。从杜尚的现成品、1950年代法国的新现实主义以及1970年代意大利的贫穷艺术,这一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现成品作为材料的语言方法,实际上也可以归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主义和商品批判之下。法西斯美学倾向的未来主义与佛洛依德理论之下的超现实主义,仍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关。
总之,自1980年代苹果电脑和硅谷的崛起开始,新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呈强弩之末,成为一种新学院派的跨学科艺术理论。后殖民主义在1990年代的各大国际双年展成为一种时髦思潮,但它只是一种策展理论,并未成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流派。
新媒体和基因技术的植入
先锋派和现代主义到六七十年代的激浪派告一段落,除了新媒体和基因学,作为一种技术植入,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实验形式。但新媒体和基因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更像是20世纪初摄影和电影刚发明的早期,人们想到可以将其作为艺术创作,但尚未形成基于摄影和电影的媒介自身的语言。新媒体和基因技术与当代艺术的关系,亦是如此,目前仍是一种作品创作的技术植入,尚未形成一种媒介的本体语言。
反而在好莱坞科幻剧中,以量子力学、虚拟网络、人工智能和基因重组为基础的新媒体和生物学议题,置于一种反乌托邦1984的议题之下,并与六、七十年代的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开始的科幻朋克美学结合,前者可追溯到1930年代初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弗兰兹·朗的《大都会》、六、七十年代戈达尔、特吕弗、法斯宾德、伍迪·艾伦的先锋派科幻片,以及像菲利普·迪克斯的《高堡奇人》等美国的战后科幻小说。
六、七十年代艺术,不仅是代表了从抽象艺术到概念艺术的先锋派的大致结束,也由新马克主义的学院派化以及科幻文学影视的高潮,意味着艺术的定义发生了一个基础转变,即当代艺术是一种广义的人文和视觉的关系,不再是基于一种纯艺术的形式主义或者艺术史的艺术,即当代艺术主要是一种通过视觉手段的人文表达,它同哲学、文学的泛文化主义一样,主要是思考广义的人文议题,只不过表达手段是视觉形式。就是先锋派音乐也一样,像意大利的后现代主义作曲家诺诺,他早期受葛兰西思想影响的先锋派音乐,像《不要消费马克思》(Non Consumiamo Marx,1969),同样表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主义批判与战后先锋派手法的结合。
“生物艺术”由巴西裔美国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于1997年在创作《时间胶囊》(Time Capsule)时提出,并出现在他于2004年出版的《遥现与生物艺术》(Telepresence and Bio Art)一书的书名中。卡茨早期曾是计算机交互艺术家,他于2000年在法国科学家的帮助下,创造了《绿色荧光蛋白兔》((GFP Bunny),这个被称为 “阿尔巴”的发绿光的兔子为世界上首例生物艺术,兔子的体内被注入绿色荧光蛋白,能在特定光线下发出绿色荧光。绿色荧光蛋白是一个由约238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提取于水母。当然这一作品也引起争议,即除了发出绿光,这个兔子算不算一个艺术作品?作为基因合成生物,这个兔子是否是卡茨的私有物?

▲《绿色荧光蛋白兔》,爱德华多·卡茨
GFP Bunny,Eduardo Kac, 2000
这是生物艺术迄今遇到的一个有关艺术定义的困境。众多的生物艺术,看起来只是以实验艺术名义的基因学实验,跟艺术自身并无太大关系。整个制造过程以及基因生物的最终形态,像许多人工智能或计算机交互装置一样,更像一个纯实验室的技术实验项目。基因合成的动物,亦有与克隆人和病毒实验一样的在社会法律和伦理上的合法问题,基因重组的植物,存活期很短,几乎无法保存,亦难以制模。
总之,高科技的媒体技术与生物技术,尚未带来艺术语言的内在变革及其本体语言的形成,它主要是在观念艺术的框架内的一种技术植入。
生态政治和意识外的自然
比起生物技术进入当代艺术的技术主义,而缺乏人文内涵,相对而言,以生态哲学和气候政治为核心的更广义的生态艺术以及1990年代关于意识之外自然的新唯物哲学的探讨,具有21世纪关于自然议题的新面向,其代表是法国的生态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及美国新一代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
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1991)、《自然的政治》(1999)等一系列著作,试图在前苏联解体的冷战后,重构一种以气候和生态政治代替乌托邦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的系统思想。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哲学质疑上,即“现代性”通常将文化和自然看作两个对立的系统,在哲学划分为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关系。但拉图尔认为并不存在社会和文化之外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无论是物质或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将自然看作在文化/主体之外的客体,实际上是一种19世纪以前的哲学观念。就这一点而言,人们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意识从未现代过。

▲2016年拉图尔策展的《重置的现代性》
(Reset Mondernity)
但拉图尔并未讲清楚过“现代是什么?”他只是提出一个将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重构成为一种动态性的网络系统,称之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大意是自然与文化是共处于一个系统并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拉图尔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看待艺术史与科学史的关系,尤其从文艺复兴之后,艺术史同时就是一部科学史,而不能将两者看作无关的两个系统。反应在艺术作品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上,比如17世纪荷兰的静物画,静物在画中所处的空间,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空间,其实是同一个空间,只是作了一种图像转换,静物画中的空间并不在我们主体之外的另一个系统。
拉图尔认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协商作为一种新的总体主义的“行动者网络”机制,可以打破现代性的试图通过社会制度改造自然的二元对立,在不断地民主协商中,将自然意识内化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种总体的解决机制。拉图尔将社会和自然意识看作相互渗透又形塑一个总体意识,并通过这一总体意识推动人类进步,这一思想显得过于形而上学,缺乏可操作性。有意思的是,拉图尔意外地在跨学科策展上风生水起。继利奥塔德、温贝托·艾柯等思想家介入艺术策展之后,通过当代艺术展来推动他的“社会行动者网络”的理论实践。
从2000年起,他跟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合作了多次策展,包括2002年的“打破偶像:超越科学、宗教与艺术中的图像之战”(Iconoclash:Beyond the Image-Wars in Science, Religion and Art),2016年的《重置的现代性》(Reset Mondernity),2020/2021年的《临界区:着地的科学和政治》(Critical Zon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Landing on Earth)。这些展览大部分是与ZKM的主任彼特·韦伯尔(Peter Weibel)联合策展,韦伯尔是美国早期概念艺术与新媒体的重要艺术家之一。2020年,拉图尔担任了台北双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的联合策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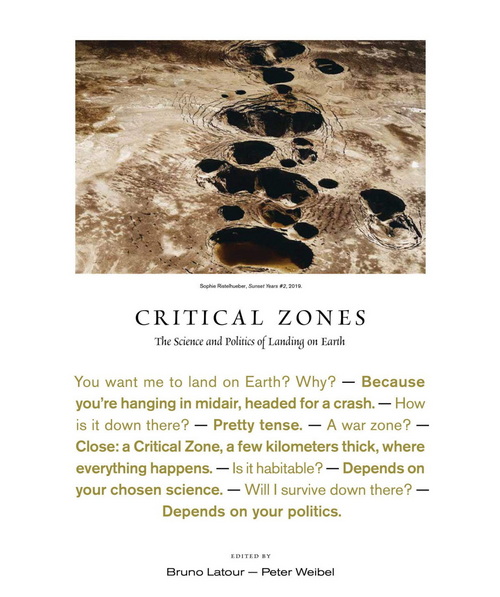
▲2020/2021年,拉图尔策展的《临界区:着地的科学和政治》
(Critical Zon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Landing on Earth)
拉图尔的大部分策展,反映了新世纪以来一种新的策展理念,即展览作为一种检讨和推进社会共识的公共讨论的场域,在意参展作品的议题性以及公共案例,并不在于作品语言的先锋性,以博物馆和双年展促进一种生态主义讨论。因而,这一策展模式就类似于1990年代的国际双年展的后殖民主义议题,主要是一种策展思潮,而不是一个艺术的流派现象。策展人的资质则越出了艺术史学者和批评家的范畴,邀请哲学家和文化学者以其跨学科的泛文化理论参与策展议题的定位,相关研讨会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展览本身。
在关于自然的哲学认识上,美国60后新一代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提出了一种称为“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的新唯物哲学。哈曼的哲学出发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将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阈限之外、海德格尔的“物—工具”论以及基督教的超自然概念原有的模糊地带,基本上界定清楚了。哈曼认为,“物自体”在康德哲学中只是提及了一下,并未深入展开解释。胡塞尔将哲学对物的意识,界定为进入意识的这部分物质记忆以及物质进入意识后由记忆到意识重构的时间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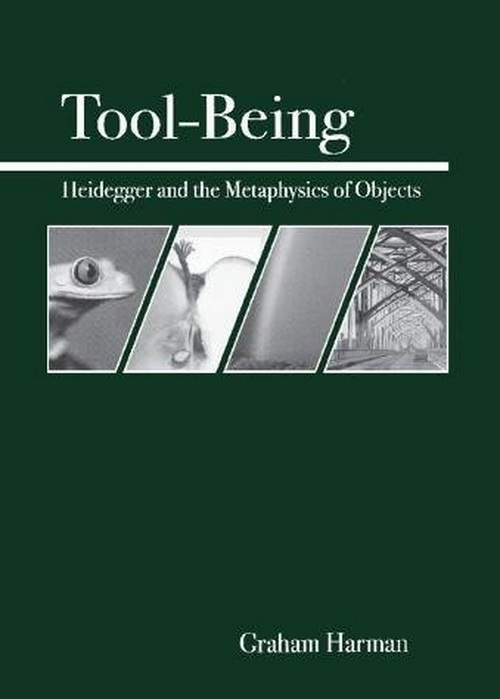
▲格拉汉姆•哈曼 《工具—存在:海德格尔和物的隐喻》(2002)
海德格尔实际上发展了“物自性”的概念,即物体被人类进行工具主义使用之后,物在人文意识中因而具有一种共情意识的投射,但哈曼认为,这种物的工具化使用的耗损之后的共情化,跟“物自性”毫无关系。好比人们在树林中捡起一根树枝当工具,这只是一个偶发行为,森林包括人到过的部分和未到的部分,不管人是否踏足以及捡起树枝,森林仍按照自性存在。人类的哲学史一直将森林看作一种由人定义和改造的自然,但森林与人交集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人们将自然赋予的人文内涵的共情化,并不反映森林系统的全部自性。
因此,哈曼将自然划分为与人类发生小部分交集的物自性的本体系统,与人不交集的自然部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将其也归入自然之外的神秘主义的“超自然”。但这是一个误区,19世纪以前的“超自然”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真正意义上的超自然,即上帝和神秘精神;另一部分是人类的感官和工具从未抵达过的物质世界,比如外星系,这部分古代误归入“超自然”,实际上是超出人的感知范围的遥远自然。
哈曼由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更为清晰定义的物自体的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本体论上,希望完全清除对自然系统的人格化和共情化,将自然体系看作一种独立于人类的自体及自性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佛教的“自性”或“空性”。因而,哈曼等人的物导向的本体论,可以看作一种彻底的唯物哲学。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论,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这一哲学对现代主义关于艺术和媒介材料的自足关系,具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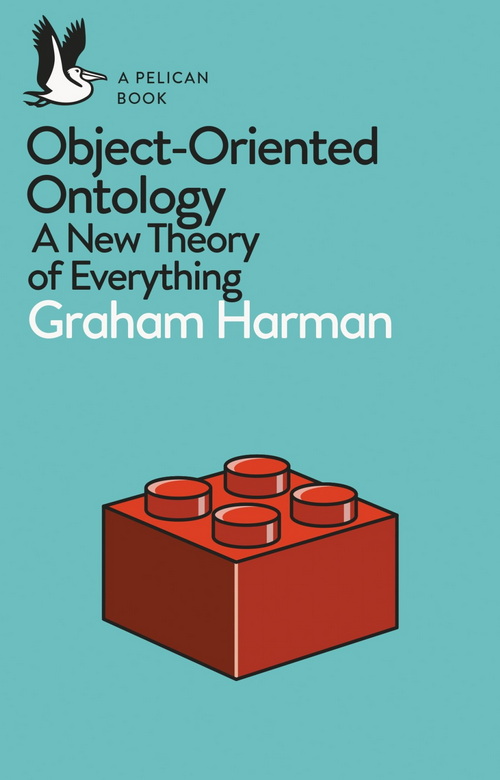
▲格拉汉姆•哈曼 《物导向的本体论:一种新的日常物理论》(2018)
历史没有终结以及后人类时代的博弈
在前苏联于1991年解体以及2001年纽约911事件之后的第二年,美国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先后写过两本书,即《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1992),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2002)。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福山当时宣称随着冷战的结束,有关意识形态及其制度之争的历史宣告终结。显然这一结论过于乐观了,2020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2022年的俄乌战争,预示着新冷战的开始。俄乌战争仍是冷战的一个遗绪,欧盟北约、韩日等仍维持在冷战军事机制的美国的控制之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框架并没有改变,经过改革,苏式的意识形态体制的核心机制在中国与市场经济嫁接,形成了与美国西方一种升级版的制度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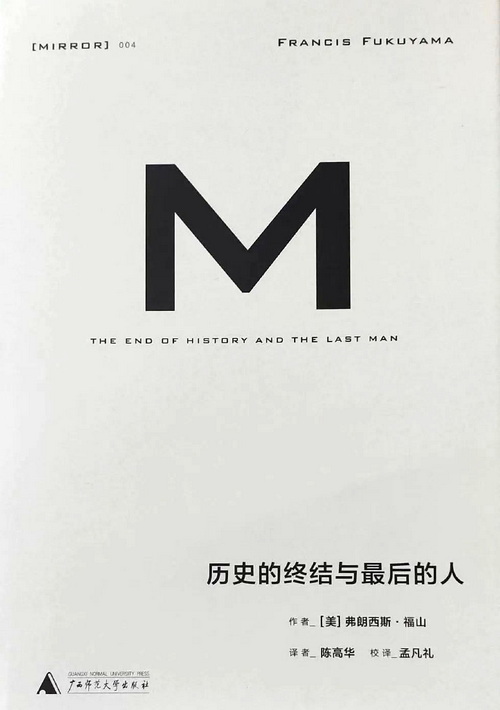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
福山在1992年预言的“历史终结”显然并未终结。但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福山以两部反乌托邦小说,即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作为生物技术和“后人类”讨论的开始。两本小说都是讨论极权对人的控制,但模式不同。《1984》是一种硬极权,《美丽新世界》则是软极权。所谓“硬极权”,指以一种清教主义的弄得大家不开心为终极形态,《1984》是一种贫穷的乌托邦国家,住房、衣着、食品、交通工具、工厂条件都很差,属于一种清教极权主义。
“软极权”则是让个体同质化以及在享乐主义的状态下以科学和消费名义下的统一安排和控制。《美丽新世界》是一种迷幻药极权主义,像未来世界,扎哈·哈迪德式的流线型建筑、未来主义风格的列车,男女经过优生学基因筛选,长得都俊男靓女,每天单位发一颗无忧丸,吃了一天就没有忧愁痛苦,晚上男女都去迷幻俱乐部纵情声色。大家都相当于一个统一组织中的肉身克隆人。但在迷幻药极权社会,没有人不满意,一切都完美无缺,只是处于一种没有个性的被安排的天然顺从状态。直到有一天,发现了外面世界存在一个不完美但生动自由的有缺陷的社会,大家却想投奔外面的这个有缺陷的自由社会。因为人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和自主,而不是被安排的无个性价值的无痛无忧的存在。
但赫胥黎的这本书并未成为极权主义批判的首席力作,首席代表作是《1984》,因为它有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现实版。《美丽新世界》之后意外成为六、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推崇的经典,因为其中的迷幻药文化及肯定有缺陷的自由任何的社会。但嬉皮士运动是否代表乌托邦社会的未来性,至少到1980年代暂时中止。1980年代的文化主流开始以硅谷和华尔街的商业与科技精英为楷模,占领华尔街运动不过像是六、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的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并未真正冲击华尔街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统治。
福山的“后人类”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讨论反乌托邦,主要讨论生物技术对“人”的定义的影响。未来两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非同一般,一是信息技术,二是生物技术。《1984》中也有高科技成分,即每个人家里的电视机,同时也是摄像头监控系统。这个系统还是一个互动系统,“老大哥”通过这个系统实现了直接统治,摄像头可以深入到每个人的卧室,不仅知道每个人在房间里干嘛,还可以随时发布指令,让每个人对着电视机忏悔或汇报思想。当然,这个互动技术及应用已经不是一个政治科幻了。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涉及到未来的新极权形态和等级社会。比如权贵可以通过基因技术,活到200岁,提升智商,综合各种人的基因优点,成为新的高级人种;穷人没钱,就在人种的外貌、智力、寿命上远远落后。通过脑机连接技术,富人就不用苦读几十年书,插座一接上,就完成博士知识库了。生物技术的病毒战,将是未来的超限战的优先手段。只要训练十几个敢死队员,携带病毒潜入敌国,传播一下,就能底成本的瘫痪敌国数年。Covid—19新冠病毒的流行,就是一个未来生物战争预演效果的例证。
《美丽新世界》无疑比《1984》更具有一种对未来主义极权主义的预言,即“后人类”社会仍存在着乌托邦总体主义的新极权可能性。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对新媒体艺术及其生物艺术,仍持一种柏拉图主义的观念艺术以及库布里克式的科幻嬉皮士的视角。“后人类”的探讨,在科幻影视中反而具有一种理论定义的模式演示及其人文主义的总体思考,前者如好莱坞的《终结者》(1984)、《超验骇客》(2013)、《攻壳机动队》(2016),演绎了从半人半机械、人脑内容载入的全机械身体以及无身体的脑知识和灵魂的网络控制的“后人类”的存在形式。
后者如HBO出品的乔纳森·诺兰(Jonathan Nolan)的《西部世界》(1-3),它取自《圣经》“大设计”的上帝视角,未来的克隆人社会的创世者不再是上帝,而是计算机编程工程师。不仅人类的知识、个性、情感乃至前世记忆,都可以人工模拟,甚至连克隆人的反抗意志也都是设计中预设的一部分。即让人反抗是为了避免后人类社会过于顺从导致的单调乏味,但既然设计好让你反抗,反抗也只是一个戏剧性插曲。这事实上如同前卫艺术在消费社会被资本买单后的图像反抗的空洞化及商业化媚俗的自我阉割。
结 语
中国的两次文化和艺术的颠覆性变化,同样产生于两次时代更迭,即清末民初和1979年之后的改革时代。第一次现代性变革,无论五四文学抑或中国画的现代改造,都走入了对现代主义的误读。五四文学主要参照的是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文学,中国画的现代改造参照的是19世纪之前的写实主义和前苏联的宣传画,两者都是对现代主义的误区。
民国三四十年代少部分作家和画家的现代主义萌芽,在1949年时隔30年后,才于1979年后重启现代主义进程。直到1990年代初实验水墨,才继日本的物派、韩国的单色画之后,在现代主义的东方主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90年代大批参与国际双年展的以毛图像、明清家具和长城等革命和传统符号为中心的身份政治的作品,算不上真正具有语言风格史上的价值,时至今日,实验水墨的成就更高一些。当然,由于后者是一种迟到的现代主义补课,仍是一种东方主义现代性的二级成就。
在新唯物哲学、佛教和量子力学、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升级、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反乌托邦的新1984以及中美新冷战等议题上,中国实际上都走到了核心场域,但我们是否为这一场域前沿的人文探讨以及艺术表达做好了知识准备?当代艺术作为跨学科的人文议题和视觉艺术的艺术定义,仍是一个基本方向。艺术就像新冷战的国家行为一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战争以及日常生活是一体的,任何其中之一项,同时具有其它所有各项的内涵。中国的艺术教育并不重视科学和技术,但艺术史还不仅具有科学史内涵,像量子力学、人工智能和基因编码,它除了作为艺术和科学,事实上,同时也是宗教、哲学和政治。这是艺术的跨学科人文化趋势的必然性。
2022年5月28日完成于宏源公寓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