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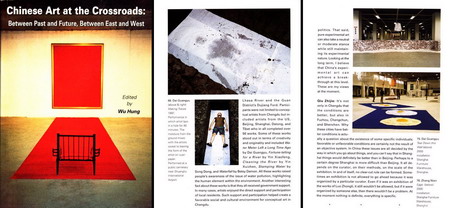
一 一个前卫主义者
戴光郁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前卫艺术群体,但他属于一个前卫主义者。
在讨论戴光郁的艺术之前,对“前卫”这个概念进行简要地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前卫”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它并不要求直接的对抗,而是意指一种往前侦察、向前探索的状态。用意大利前卫理论家波基奥里的话讲,“这(前卫)是一种前进、力量分散的探索,而不是集中火力向敌人扫射的行为……”。[1]20世纪初,“前卫”概念开始被理论界用于艺术领域,特指具有反叛和先锋性的艺术创造。
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前卫”仅仅属于现代艺术的范畴,并与各种现代美术运动和流派直接相连,但最终却以艺术家个体的实验体现出来。这一点不仅实用于西方现代艺术的研究,同样也为研究中国的现代艺术,以及艺术个案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当然,“前卫”并不是静态的,其内涵与外延都处于一种发展状态中。波基奥里认为,前卫体现为一种行动主义,而这种行动是以对抗、反叛、否定的面貌出现的[2]。波氏认为,这种对抗具有双重的目标,一是反对各种传统艺术领域的保守主义和教条方式,其中包括学院派和官方的艺术;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庸俗化的审美趣味。尽管波氏在讨论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前卫精神时提到了语言的变革,但他却没有将这种变革与现代主义的语言创新进行有效的区分。其后,德国文化理论家彼得·比格尔[3]不仅将前卫与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而且提出前卫艺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对现代艺术体制的批判。显然,比格尔的研究既拓展了波氏理论的边界,也弥补了格林伯格[4]将前卫与现代主义混淆使用的理论缺陷。在比格尔的研究中,杜尚的艺术是前卫精神的集中体现,因为杜尚不仅颠峰了艺术品与日常物品之间的概念,而且还直接拓展了现代艺术的既定边界。
实际上,西方理论界对前卫艺术的研究大致持以下三种观点:其一,强调前卫的反叛性与对抗性,将前卫看作一种独立的艺术。在这个理论系谱中,除了有意大利的波基奥里外,还包括20世纪初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提出的“非人化”理论。这种理论观点直接源于对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俄罗斯早期前卫艺术的研究。其二,对前卫和现代主义进行区分,强调前卫的极端个人性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并突出前卫艺术对艺术体制与自身的批判与否定。这种理论观点直接来源于杜尚的艺术,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约翰·凯奇为代表的偶发艺术。这种研究方向主要以比格尔为代表。其三,强调前卫与大众文化、前卫与庸俗艺术进行区分,将前卫艺术的精英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这主要体现在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的研究中。同时,格氏的一个最大贡献在于,他将前卫艺术与艺术市场那种潜在的生存逻辑提取了出来。格林伯格认为,“就前卫艺术而言,这种文化是由社会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精英阶层所提供的,而前卫艺术则假定它自己被这个社会所背弃,而它又总是通过一条金钱的脐带依附与社会。”[5]尽管格氏并没有区分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之间的区别,但他却以犀利的视觉洞察到前卫艺术的悖论之处,即前卫最终与它反对的对象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最终以被艺术市场“收买”和进入既定艺术体制为结局。
陈述西方前卫艺术的理论背景无非是为我们研究中国前卫艺术或者中国现代艺术提供一个参展系。同样,也只有将戴光郁的艺术放在前卫理论的系谱中,他的艺术实践和前卫精神才能凸现得更为明晰。

戴光郁的艺术发轫于“新潮美术”时期。80年代中期,他便和一些艺术家在成都发起了“红黄蓝画会”,并成为成都地区现代艺术的领头人。在这一阶段,戴光郁的艺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以民间现代艺术团体的先锋性来讨论戴光郁早期的艺术活动。实际上,文革结束后,中国新时期艺术的起步得益于民间美术团体的推动,这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的“星星画会”和重庆的“野草画会”中可见一斑。此时,民间艺术团体的艺术最大的特征在于与官方美术的决裂,正如波基奥里所认为的那样,即艺术家将“反叛性”和“行动主义”放在艺术创作的首位。这种前卫的姿态在其后的“新潮美术”时期达到高峰。此时,具有明确艺术目标和现代艺术追求的美术运动和美术团体粉墨登场,掀起了中国现代艺术的热潮。就西南的现代艺术而言,云南的“新具象”绘画,以及其后以张晓刚、毛旭辉、叶永青为代表的艺术家成立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都具有代表性,而成都的现代美术运动直接就来源于当时的“红黄蓝画会”。戴光郁不仅是“红黄蓝画会”的组织者和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而且参加了1988年“西南现代艺术大展”和1990年的“OOO九O”画展。之所以要强调戴光郁与这些现代艺术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这些现代团体所作出的贡献也就没有中国现代美术的多元发展,而这些不同的团体是由具有前卫艺术精神的艺术家构成的。同时,在新潮美术的发展中,现代美术团体和当时的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由艺术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前卫性。和西方20世纪初前卫艺术的共同之处在于,此时的现代艺术团体不仅要反对官方的艺术,而且还有对学院派的艺术、传统的艺术提出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前卫艺术明显具有波基奥里的观点,即美学的前卫和政治的前卫。因为对官方艺术的否定和拒绝其实就明确了艺术家自身的文化立场和艺术价值取向。戴光郁早期的艺术便是在这个语境下开始进行的。另一方面是从对现代语言的积极尝试和实验的角度来讨论戴光郁的艺术。整体而言,中国的现代艺术家都重视个体语言的现代形式建构。和大多数新潮时期的艺术家一样,戴光郁的作品明显借鉴了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方式,这在他八十年代中期作品那种对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接纳中可见一斑。但是,有必要提及的是,这种对艺术本体的现代形态建构同样具有一种前卫性。这不仅体现在八十年代初以吴冠中等艺术家所主张的“形式美”中,更体现为新潮美术时期兴起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中。因此,除了有艺术本体的建构外,同时也彰显出艺术家一种反叛的姿态,即前卫的姿态。因此,八十年代中期的艺术不仅具有前卫特征,也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尽管从作品上看,戴光郁此一时期的创作并没有强烈的前卫性,但这种实验的态度和前卫的反叛精神却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和比格尔讨论前卫艺术的相同之处是,中国的前卫艺术既有自身的否定性,同时也涉及到对艺术体制的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官方的艺术体制而不是对现代艺术自身。同时,前卫的终极意义最终也落实为个体精神的解放,即将艺术家的主体自由和精英化的身份放在首位。因此,前卫艺术的一个后果就是使艺术分化,即传统与现代的,官方与前卫的。就戴光郁早期的艺术活动和作品来看,他显然属于后者。
但是,和格林伯格关于前卫艺术的讨论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的前卫艺术并没有出现一个大众文化的语境。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现代艺术的文化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是海外艺术市场对中国现代艺术的接纳,以及其后国内艺术市场对现代艺术的“收编”;其次是大众文化对前卫艺术的冲击。实际上,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八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前卫传统和艺术的批判力也丧失殆尽。和八十年代前卫艺术有明确的反叛对象,即官方的艺术不同,九十年代中后期,官方对现代艺术的宽容态度反而使前卫艺术找不到反叛的目标。当艺术家可以相对自由的从事自己的艺术实践时相反失去了创作的热情;而且,在面对艺术市场的引诱下,前卫艺术的反叛精神最终被各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取代。尤其是架上绘画开始全面地进入艺术市场后,当早期具有前卫精神的艺术家进入不断的图像复制时,前卫艺术家在金钱的利诱下彻底地缴械投降了。
艺术的死亡就是从前卫精神丧失的那天开始的。这不仅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如此,对于个体的艺术家同样如此。
但是,在戴光郁眼中,艺术的前卫精神仍是激励他坚持创作最重要的动因——重要的仍然是艺术本身。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戴光郁主要从事行为艺术创作。不过,此时的行为艺术在当代实际上是非常边缘的。在诸多的原因中,行为艺术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以及作为一种典型的精英艺术方式其受众仅仅在一个有限的小圈子成为了许多艺术家放弃行为艺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行为艺术就必然具有前卫和反叛性,而是说我更侧重于探讨戴光郁行为作品所体现出的文化意识。
戴光郁的行为艺术并不具有像比格尔所说的那种挑战艺术体制和波基奥里所强调的极端反叛性。相反,他的前卫精神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以及对周遭文化问题提出不同的思考。例如,在《倾听》(1996年)、《搁置已久的水指标》中,戴光郁将中国当下所遭遇到的环境问题与中国传统关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文化观念作了智慧式的对比。在《制造印痕的行为》(1997)中,戴光郁对艺术品概念的颠覆,以及对行为过程所产生的意义的讨论具有极强的先锋性和实验性。而《想象行走、站立或逃逸》(2002)、《上路》(2004)、《失禁》(2005)等作品则将人所遭遇到的“异化”和“规诫”当作作品言说的主题。作为一个前卫性的艺术家,戴光郁能不断的否定自身,并不停留在一个既定的思路和惯性的思维模式之中从事创作。特别是在一个以艺术市场为主体所形成的当代艺术环境中,这一点尤其可贵。同时,就当代艺术的文化取向上说,戴光郁始终保持了对当代周遭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拷问。
正如前文所言,“前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对于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文化语境来说,“前卫”的意义并不在于像波基奥里、比格尔所提出的那种反叛,而是在于以一种精英主义的方式持续不断的对当代文化问题进行拷问和反思。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的前卫艺术主要是反官方的艺术体制和学院化的艺术的话,那么九十年代则是反流行文化和媚俗的艺术。当下中国的艺术已经进入一个分化的阶段,民间的、大众的、官方的、精英的艺术同时共存。因此,前卫艺术在今天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独立的个人性和实验性创造,以及艺术家对当代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之所以说戴光郁是一个前卫主义者,因为他真正秉承了一种前卫艺术的精神,即以精英主义的方式保持对流行文化地疏离和警醒,以实验的状态对自身艺术创作不断地超越与否定,以个人化的视角坚持对周遭社会现实地批判和反省。
二 水墨与观念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理论界出现了许多跟水墨有关的不同概念,最主要的有:现代水墨、实验水墨、抽象水墨、表现水墨、都市水墨、观念水墨等。由于不同概念的立足点不同,使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例如,现代水墨便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在面对传统水墨时,它可能是一种风格学上的概念,特指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或水墨样式;在面对西方现代艺术时,它可能是一种表明自己“中国身份”的文化概念,特指一种承载东方精神和具有“中国样式”的表现性水墨;在面对当代艺术时,它又可能成为一种时间上的概念,特指“八五新潮”以形式先决和文化反叛的这一段时期。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概念会产生不同的内涵。尽管,以上不同的水墨概念在学理上都有其合理性,但我更愿意将戴光郁的水墨作品称为观念水墨或实验水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戴光郁便以水墨和宣纸为媒介做过许多具有实验性的作品,例如《还原——水迹墨痕》(1998)、《山水·墨水·冰水》(2004)、《水落石出》(2007)等。这些作品最大的一个特征便是作品的观念性。
在谈到水墨与观念的结合时,批评家王林认为:“所谓观念,不是指一个概念、一种思想、一些可以用语言来言说描述的东西,而是指人的思维水平与思维能力,即充满悟性、禅机的智慧。智慧是与众不同的体验、是豁然开朗的见地、是突如其来的启发、是力透表象的反省。”[6]显然,观念取决于创作中如何使用水墨材料,取决于艺术家如何在自己与当代文化问题之间找到契合点,把文化问题转换为艺术问题。
戴光郁的水墨作品大致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强调作品的过程性和时间性。例如,在《还原——水迹墨痕》(1998)中,他将墨汁冻成的冰砖置于宣纸装裱的桌上,任其自然溶化,最终,自由流溢的墨汁形成的抽象墨迹正是他所期待的作品。在《边界》(1998)中,戴光郁用清水浇灌的墨土垒成一个中国地图的形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墨土开始融化,先前地图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在《山水·墨水·冰水》(2004)中,艺术家将两块中文“山水”字样的墨冰放入自然的湖泊中任其自然的消融。同样,在《水落石出》(2007)中,艺术家在一张铺着白色床单(上面临摹古典山水画)的双人床上放置一块墨汁冻成的冰,随着时间的延续冰块开始逐渐融化。在整个过程中,一股清水不间断地从悬挂于屋顶横梁的瓶子里落下,融入水墨冰砖中。若干时辰后,冰溶墨化,原来,里面隐藏却是一块石头。显然,在这些作品中,“时间性”和“过程性”是戴光郁作品的共同特征。但是,这个时间却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是自然的物理时间,因为墨冰自然融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的时间;另一个也是具有文化或历史隐喻性的时间。不管是《山水·墨水·冰水》还是《水落石出》,戴光郁都巧妙地将物理的时间与中国文化中特定的时间意识与文化观念巧妙的结合了起来。
其次,戴光郁的作品超越了水墨媒材的既定边界,将“水墨”还原为最本真的物,此时的“物”不仅具有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而且也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例如在《还原——水迹墨痕》、《水落石出》中,艺术家都将水和墨看做是最纯粹的“物”——仅仅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材料而已。这种对水墨媒材的使用是需要勇气的。按照传统的观念,水墨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物。因为水墨不仅是一种绘画媒介,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更与中国古典绘画密切相连。尤其是在当代这个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由水墨所承载的审美情趣、东方美学观念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象征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从“水墨”媒材自身的变化上看,从文化观念的“物”到纯粹材料上的“物”的变化实际上是现代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从 “文人画”到“中国画” 再到“水墨画”,仅从称谓上看,我们便能洞悉艺术界创作思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文人画”到“中国画”,这种转变不仅强调了“中国画”与“西洋画”在材料媒介上的区别,更突出了中、西文化精神上的相异特征;[7]而“中国画”向“水墨画”的转变,“表面看不过是概念的转换,而实质却从‘文化’逃避到了‘材料’”。[8]如果按照格林伯格的观点来理解,现代绘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材料本身“物”的自然属性。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国水墨艺术家来说,如果放弃了水墨自身的文化属性而仅仅把它当成自然的物,那么由水墨所带来的身份和文化标识就将消失。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由水墨媒介所彰显的文化立场异常复杂,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是异质同体的。换句话说,一些坚持以水墨为媒介的艺术家尽管高呼要弘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但实质是以“他者”的身份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往往披着“民族主义者”的外衣在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中就范。在我看来,一方面,在戴光郁的水墨作品中,他对传统水墨主体性的话语权力、笔墨中心主义等经典法则进行了颠覆,也放弃了现代水墨的个性化图式,而是将水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物质材料。另一方面,对于戴光郁而言,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语言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作品能充分表达思想的深度和独立的文化观念。
三、寻求观念背后的文化表达。在戴光郁的作品中,我们或许都能看到杜尚和博依斯的影子。杜尚和博依斯都是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但前者更偏向于挑战艺术体制和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后者却敏感于对现实文化问题的关注和表达。在我看来,戴光郁离博依斯的作品更近。
戴光郁能超越水墨媒材自身具有的文化性,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将作品所表达出的当代文化意识放在了首位。例如在《边界》中,除了由水墨自身融化的时间性和过程性外,中国地图形式的消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就像博依斯的行为《包扎》和《我爱美国,美国也爱我》等作品一样,艺术家作品的意义仅仅因艺术家为行为注入观念所产生出来的。同样,在《水落石出》中,由“水落石出”这个中文概念所指代的时间观念便与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过程性、时间性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同时,由墨汁自然融化后在宣纸上产生的墨迹也是一件艺术作品。于是,围绕传统艺术品的审美趣味、表达观念、接受方式等都在这种“非人工”化的时间流溢中被颠覆了。正是在这些作品的启发下,我们将自觉地去思考艺术与非艺术、行为与观念、艺术与日常方式等既定的艺术边界问题。
戴光郁的作品是充满智慧的,他对水墨实验的态度也是严肃的。艺术家立足于当代的文化事实,不为既定的、普遍的、人云亦云的惯性文化意识所蒙蔽。他以一个睿智的思考者的身份介入水墨创作,以行为体验或装置的方式显示持续不断的思考和敏锐的文化批判。或许,在他看来,在一个消费吞噬主体、物质代替思想的时代,文化的批判才是艺术家真正应承担的艺术使命。毕竟,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言,重要的仍然是艺术本身。
2007年4月26日于中央美院
戴光郁
1955生于成都,现居北京
主要个展
2000 "我射击自己",杜伊斯堡大学,杜伊斯堡,德国。
1996 "复活96’成都"装置艺术展,四川大学东区,成都。
1993 "戴光郁画展",拉鲁滋画廊,蒙特利尔,加拿大。
主要群展
2003 "亚洲中欧国际行为艺术交流展",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
1996 "CHINA!",波恩现代美术馆,德国。
1989 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
[1]雷纳托·波基奥里(Renato·Poggioli)的《前卫理论》(The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1962年初版于意大利,1968出版了英文版。1992年,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张心龙翻译,参见p24页。
[2]同上,p24??34页。
[3]彼得·比格尔(Peter·Burger)的《前卫派理论》(Theory of the Avant—Garde)(中文版译为“先锋派理论”),这是他1974??79年德文出版的文章,1984年出了英文版。2002年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版。在批评家约亨·舒尔特-扎塞看来,比格尔和波基奥里的不同在于,比格尔将前卫与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前卫是对艺术体制以及自律性的批判,而现代主义则更多的体现在语言的纯粹性和形式的自律性上。二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见《先锋派理论》,商务印书馆。
扩展阅读
艺术档案 > 人物档案 > 艺术家库 > 国内 > 戴光郁(Dai Guangyu)
view.php?tid=1837&cid=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