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自: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591-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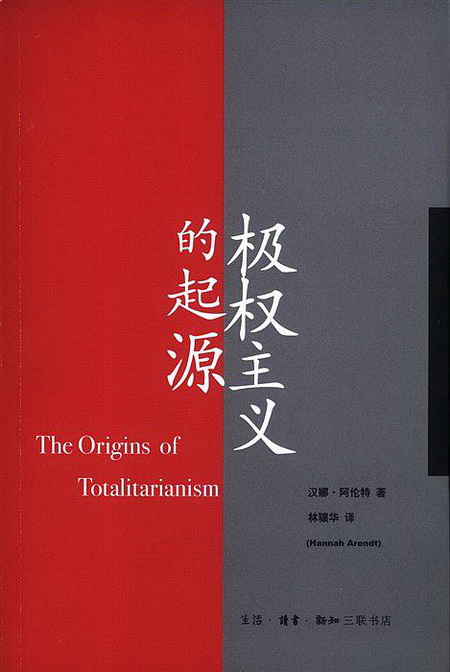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文
林骧华/译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人际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未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当然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是指社会交往方面的孤独。孤立与孤独(loneliness)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一一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然面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制造(fabrication;poiesis,指制作物品)一方面与行动(action;praxis)有区别,另一方面与单纯的劳动有区别,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注的孤立状态下进行,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中仍然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推毁了,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转变成劳动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在这种条件下,只有纯粹的劳动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抛弃,而人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动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作是制作工具的人,而被看作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ri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孤立因此就变成了孤独。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地成为对孤独(而不仅仅是对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它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却造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以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他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团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共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然而孤独却又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最明显地显示出来。除了几句离题的话之外——通常包装着一种吊诡的气氛,例如卡图(Cato)的话:“他从来没有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似乎是希腊血统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首先区别了孤独和孤寂。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义为绝对独立。埃皮克提图认为(《论文集》[Dissertations],第3卷,第13章),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他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竞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我和“自我”(self)共处,因此合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因为他们在自我中表现出来,我和这个自我进行思想的对话。孤寂的问题是,这种合二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搞错。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他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变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但是仅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它清楚地显示出,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说,孤寂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少数人的”,开始说出,但是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相反,一个孤独者发现了自己并开始在孤寂中思想和对话的机会总是有的。这似乎发生在尼采在席斯·玛莉亚(Sils Maria)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两首诗中(《席斯·玛莉亚》[Sils Maria]及《来自高山》[Aushohen Bergen]),他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为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贺庆;我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之中的嘉宾”。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人类思维的唯一能力(人类思想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世界,当它与思维有关时,它独立于经验之外)是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能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唯一可靠“真理”,这也是常识;人为了经验、生存,懂得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道路,就需要依靠这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是空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真理,因为它并不揭示什么。(如果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将无矛盾定义为真理,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独的条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开始多产地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的自证逻辑为特点的思维过程(这明显地是毫无例外的)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经注意到的问题(他对孤寂和孤独现象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敢于说“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上帝,以便让人能够相信”)。他对于《圣经》文本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评价。《圣经》上说:“人若孤独,是不好的。”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中的确包含了这种“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最坏的可能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地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可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唯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出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掌,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可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那个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也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他形式的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唯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