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未来学
约翰·厄里/著︱陆晓/译
选自《未来是什么?》,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
引言
虽然无法预知未来是什么样的,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社会群体都有一些仪式和话语,认为通过这些可以预测、描述并在一定意义上了解未来。无论预测未来是掌握在神还是人的手里都是如此。人们想象、预测、神化、预言并描述了不同的未来,有好的,也有坏的。
这些未来预测的获得方式显示了社会的运作方式。未来预测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尤其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构成和转移。权力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从众多想象、构建、实现和分配未来的方法中决定以及创建未来的能力。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经说:“未来已经来到眼前——只是还分布不均。”
本章将先简短介绍关于未来预测的方法、未来预测者以及未来预测带来的后果的历史,随后探究社会未来学,简述乌托邦式和反乌托邦式的未来社会。这段历史简述将开启本书后续章节中涉及的许多主题,关注未来社会预测的复杂问题,而不只是某一个体或者机构的未来命运。
预测未来
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中,关于未来有大量的想象和预言。这些创造未来的过程都掌控在“未来专家”手里,情况因历史和地理背景的不同而不同。这些专家包括预言家、先知、占卜者、神使、女巫、技师、哲人、星象家、未来透视者、小说家、巫师、未来学家以及算命者等等。这些专家常常运用某些专业知识,通常结合了神学和世俗知识。那些被认为能借助专业知识预测未来的人颇受追捧,报酬丰厚。如果未来预测对于强权阶层来说是“噩耗”或者预言被证实“有误”,那么这些未来专家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此外,关于未来的本质是什么的证据也常常受到质疑,大多数信仰体系建立了一些机制去解释为什么预测的结果没有实现,从而避免因预测失误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即使用于预测实验结果的科学理论亦是如此,如果在实验室或者试验现场的结果与预测不符,通常都有“补救”措施。卡尔-波普认为,这种补救预测的做法是科学哲学的关键,尤其是面临错误的预测应不应该导致理论的全盘推翻这类问题的时候(参见Lakatos, Musgrave1970)。
有些未来预测只针对社会中某些特定人物的命运,尤其是君主或者企业领导人,他们常常有自己的未来预言者。另外一些未来预测面向大多数人的未来命运,通常通过星象、透视或者算命来预测。还有些未来预测涉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宗教、神明或者世俗事件,通常在很远的将来。有些预测带来的是好消息,是一个可能的乌托邦式未来。另一些则是预言可怕的灾难——“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这种预测预警人类如果不完全改变现行的所作所为,灾难就要降临,以此希冀现状有所转变。
预测未来的方式有上千种(Adam,Groves 2007:chs.1,2),从解梦到观察人的肝脏状态(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肝脏是生命的中心),花样繁多。
在许多希腊神话中,命运是预先注定的。尽管人们相信像特尔斐神谕这样的预言可以预知未来,但它们依然无法干预或者改变未来事件的发生。许多希腊神话都是关于那些能预知未来却无力改变的预言家的悲剧的(Adam,Groves 2007:4-5)。其中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女祭司卡珊德拉的悲剧,她预先警告特洛伊人不要接受希腊人送来的礼物——特洛伊木马,但无人理会,最终藏在木马中的希腊战士攻下了特洛伊城。尽管卡珊德拉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她却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在第9章,我将探讨另外一些案例,如果人们知道他们明明清楚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什么样的未来却对此问题视而不见,这被看作是当代版的“卡珊德拉综合征”。
在历史上,德鲁伊教的教士预测未来的方式曾经很重要。德鲁伊教士从鸟飞行的轨迹、云的形状、特殊树种的样子以及自然界的其他特征中获得灵感,经过长期的特殊训练,他们被看作先知和术士,很多成为王室的谋士。据说德鲁伊教士会读心术,能运用复杂的占卜术和魔术预测未来。他们的做法和今天解读“奇特天气”有些相似的地方,今天的气候科学家越来越多地用这些方法来证明未来气候的变化,而这些都基于德鲁伊教神秘的传统(Szerszynski 2010)。
在许多社群中,经典著作在未来预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旧约》预见了许多未来事件,包括基督生活年代的事件,而在《新约》中则频繁出现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人们认为先知有特权获得上帝的旨意从而能预知未来,但是关于是不是只有特定的先知才能获得上帝旨意仍有争议。
利用星象,即根据星辰的运动以及与星辰相关的神祇的活动预测人类命运是最普遍的预测方法。印度、中国和玛雅文化建立了通过观测星象预测世事变化的复杂体系。西方的星象学通常使用星象图来解读个体的个性特征,并基于个体出生时太阳、月亮和其他星体的位置来预测未来。大多数的专业星象家利用的都是这些系统知识(参见www.astrology.org.uk)。一直以来,星象学都被看作是一种学术传统,与天文学、炼金术、气象学和医学等类似科学体系互相交织。即使在天文学出现之后,星象学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对于16世纪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有关未来战争、地震以及其他灾难的星象学预言就争议不断(参见有趣的网页www.nostradamus.org)。
综上所述,关于预言或占卜未来有许多富有影响力的记述。这些预言大都与个人未来的命运有关,预测的是特定的人的命运。它们让个体获知神祇或者命运对他们或其他个体的安排。人们认为未来是可以预知的,但即使人们已经感知命运,也大都无法改变。
某些社会未来预测
在过去几百年里,出现了关于未来的更复杂的描述,本文主要讨论欧洲的案例。这些预测详细分析了未来社会,还通过警示和引导寻求改变现状。有些关于未来的描述成为西方文学的经典,部分反映了写作年代的时代特征。故事以未来世界为背景,有乌托邦的,也有反乌托邦的。这些文本中的术语进入了日常语言,构成了日常和社会科学关于未来的话语,历时数百年。
有学者指出关于乌托邦的著作是在中世纪开始瓦解后才出现的。从16世纪开始,人们才有可能评价和批判社会(Kumar1987,1991)。一些重要的著作开始描述乌托邦,最早的著作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Andrews重印本1901)。作品完整描绘了一个不同的社会,而不只是描述社会的某一个完美的方面。《乌托邦》的出版就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之后。约500年前(1516),这一现代乌托邦诞生,统一的基督教也在此时通过宗教改革开始分裂,震动了全欧洲的天主教会(Kumar 1987:22)。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里预测了几百年后的社会,描绘了人类之城而非上帝之城的细节。书中,他首创了未来学的文学体裁和“风格”。《乌托邦》描绘了一个全面运行中的平等主义社会。莫尔的写作方式类似现代社会学家,描写了“乌托邦居民的相互交往、商业和平等分配所有财产的规则”(Andrews1901:173)。
乌托邦岛由54个基本一样的城市组成,每个城市有6000户,每户有10到16个成年人。为了使人数平均,人口被重新分配到每户和每个城市。如果岛上人口过多,就在别处开辟殖民地。只有一个出入口通往乌托邦岛。在乌托邦没有私有财产,货物存放在仓库里,人们在需要的时候按需申请。经济的基础是需求而不是收入。人们通过劳动制造有用的产品,而不是奢靡的奢侈品。人们只从事必要的劳动。女人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失业已经被消灭,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长不超过6小时。公民的房屋产权每10年轮换一次。
公民可以在岛上旅行,如果“有人想拜访居住在其他城市的朋友或者想到岛上其他地方游历一番”的话(Andrews 1901:178)。这里表现了对于旅游的一种现代看法,即友谊和渴望对他乡的凝视可以是旅游的正当理由。乌托邦公民拥有交通工具、旅行所需资金和国内通行证。任何没有通行证的人都会被遣返。个人隐私不属于自由权,没有小酒馆以及私人聚会的场所。每个人都处于他人的视线之下,必须行为得体。几百年后,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也提及了在有效的城市设计和规划中有“街上的眼睛”很重要(1992[96])。
乌托邦公民背诵统一的祈祷文,其中可见他们重视对其他宗教思想的包容。但是学者能做管理官员或者牧师,有奴隶存在。总的来说,乌托邦人憎恶战争,但当他们感到友好国家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们会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他们不会杀死敌人,而是俘虏敌人。通过杀戮流血得来的胜利会让他们不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一天能没有战争。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莫尔的《乌托邦》是“社会未来学”系列作品的奠基之作,有趣的是,马克思也将他誉为“共产主义英雄”。不同的是,H.G.威尔斯(H.G.Wells)认为百年之后于1627年出版的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才是第一部现代乌托邦著作(Andrews 1901;Kumar 1987:198-9)。
《新亚特兰蒂斯》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岛上的习俗,尤其是其被视为“王国之眼”的国营科研机构所罗门宫,涉及各种科学研究仪器、科研过程和方法。其中有一个场景是所罗门宫的负责人在向欧洲的来访者介绍科学背景知识时,展示以培根法进行的科学实验。这些实验旨在理解和征服自然,并运用所获得的知识改良社会。
18世纪科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持有相似观点。他凝望“未来之海”,预见到一个进步的未来世界的诞生,这一未来建立在平等、启蒙和由科学家群体指引方向的社会基础上(Kumar 1987:44)。科学将蓬勃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力量,这一力量能够改变并改善这个世界。
小说家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从更广泛的层面上阐述了乌托邦思想的积极作用。他写道:“如果没有对未来的乌托邦幻想,人类也许还居住在洞穴里,赤身裸体,充满苦难……美好的现实来自高尚的梦想。乌托邦是一切进步的标准,是进入美好未来的尝试。”(引自Mumford 1922:22)在19世纪以前,未来极少被想象成一个不同的地方或一个未被发现的领域。但在19世纪,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对未来出现的乌托邦做了详尽的想象(Armytage 1968)。大部分未来学家看到了新科学技术的活力,尤其是蒸汽机和电力将促进社会进步,进而进入一个全新的更好的未来世界(Kumar 1987:ch.1;Morus 2014)。
一些乌托邦的想象被看作是接近现实的梦想,而不是遥远的未来。例如,马克思源自阶级斗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理念以及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自由市场乌托邦(Kumar1987:46-9)。最有意义的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9世纪早期在苏格兰新拉纳克建立的工厂村范例。这一“真实的乌托邦”导致了19世纪乌托邦模式的大量涌现。欧文关于新拉纳克纺织厂的著作题为《新社会观》(A New View of Society)(1970[1813/14]);他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性和异化特征,宣扬规模相对较小的“合作村庄”,每个这样的村庄大约有1000人。社区有公共大楼、合作社、操场、公共厨房、讲堂和学校。欧文认为这些合作村庄能帮助改善“新技术和机器对人的贬斥"(Owen 1970[1813/14]:53;参见Wright 2010关于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近代“真实的乌托邦”)。
19世纪较晚期的乌托邦思想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所展示的理想社会(1890)。在这个想象的乌有乡社会里,人们免受工业化的困扰,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莫里斯认为机器可以减少令人痛苦的那部分劳动,但他没有设想家庭劳动的分工改变。这里的物质环境令人愉快,宽敞美丽,带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简朴风格(Levitas 2013:80)。在关于威廉-莫里斯的讨论中,莱维塔斯(Levitas)将乌托邦分为封闭式的和探索式的,用于检验和评判当代社会的乌托邦(2013:114-15)。在莱维塔斯看来,莫里斯的作品强调的是开放和参与,而不是一个固定封闭的乌托邦蓝图。
其他的19世纪乌托邦未来世界图景显得更加动感,有些作品更是涉及了大量的旅行、探险和迁移的描写,例如H.G.威尔斯有关“时空穿梭”和“世界脑”的描述以及儒勒-凡尔纳的《环游世界八十天》。还有的未来设想表现了人类与居住在地球内外空间中更先进的外星种族的冲突,其中最早的一个例子就是H.G.威尔斯的《世界大战》,它引出了此后许多类似的著作和未来设想。
19世纪的著作大多对科技进步的威力和进步持乐观态度,作为标志性事件的1851年伦敦博览会就表现了这样的乌托邦思想。奥斯卡·王尔德曾在世纪之交写下了一句名言:“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看的,因为它遗漏了那块人性永恒的国度。”(2001[1900]:141)H.G.威尔斯被称作“乌托邦主义的化身"(Kumar 1987:ch.6,关于其作品中的变化),他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乌托邦,因为“社会学是对理想社会与现行社会的关系的描述”(Wells 1914:200)。
威尔斯在他的《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 2011[1905])里详尽描述了这样的理想社会。他的现代乌托邦不同于较老的静态的乌托邦设想。在他看来,乌托邦充满了变化和创新。他想象全世界巨大的火车以每小时200—300英里的速度在地球上奔跑(Kumar1987:94),乌托邦不可能是止步不前的。个人隐私没有理由存在,语言、货币、习俗和法律都是一样的。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拥有土地和所有的能源。人类几乎完全免于体力劳动。社会设计有效、简单而又实用。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富有科学精神。最新的科技带来的机器进入人类的生活,对此没有限制。在一座大楼里存有世界人口索引,每个人都有一张记录卡记录其多种信息,包括其旅行模式。
然而,H.G.威尔斯在他的著作《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中却展示了一幅不那么乐观的图景。书中古怪的科学家Griffin发现了隐形的秘密,从而开始了对无上权力的疯狂追求(Kumar 1987:184-5)。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于19世纪早期塑造了由小说中的人物瑞士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创造的怪物形象,此后机器超乎预料的威力成为未来预测的永恒主题(2000[1818])。弗兰肯斯坦在科学实验室的全新空间里进行实验,摒弃生命创造的自然规律,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了一个新人——现代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也成为小说的副标题。但是,当他将不同的身体部位组装好时,他吓坏了。他扔掉了这个怪物,但最终还是受到了惩罚。人类创造了这样的“科学怪物”,失控的怪物又回头戕害人类,这一主题出现在此后的许多科幻作品中,如《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年首映)。
玛丽·雪莱以21世纪末为背景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常被人们称作最早的“启示录”小说。小说描绘了一群在迅速蔓延的瘟疫中挣扎的幸存者(1826)。在雪莱的笔下,“美国的巨型城市、印度的肥沃平原、中国的拥挤住宅都面临着灭顶之灾。不久前还是众人欢聚或者财源滚滚的地方,现在只听到痛苦的哀号。空气已经变成毒气,每一个人都呼吸着死亡的气息”。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他的小说《埃瑞璜》(Erewhon)也详述了人与机器的不正常关系,尤其是“机器工作簿”这一章(Butler 2005[1872])。小说紧跟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出版。关于适者生存,巴特勒警告说人类有一天也许会失去对自己创造的机器的控制能力,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进化到现在的样子,其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机器进步的速度,机器改进的速度似乎没有止境。巴特勒预计有一天机器会生成“思考”的能力,或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工智能。
机器能自我进化,自我管理,最终统治世界。巴特勒早有先见之明。他这样写道:“令我害怕的是它们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变化着,从前没有任何事物能有这样快的进步速度。我们是不是该用嫉妒的目光审视它们,并在有能力阻止的时候叫停它们的前进步伐?”(2005[1872]:ch.13;Armytage 1968:52-4)。在埃瑞璜(埃瑞璜Erewhon是乌有乡nowhere的回文)社会,反机器人士确实揭竿而起,捣毁了机器。巴特勒认为有必要消灭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更加先进的机器。
E.M.福斯特(E.M.Forster)也展示了一个科技将人类变为机器的奴役的未来世界。他的优秀短篇小说《机器停止运转》(The Machine Stops)中描绘的未来社会在后来的科幻小说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数字世界中能找到相似的模式(1985[1909])。构思这篇小说的部分原因是要反击威尔斯关于机器文明和世界国的乐观预测(参见福斯特的分析,2015:217-21)。
福斯特描述了一个人类受控于机器而被分隔并失去行动能力的未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生活在地下独立狭小的隔间里,通过大机器与外界交流。这里有一些飞船,但人们大多不旅行,因为他们没有会见他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于机器,另外还有一本由这个世界国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机器工作簿》(The Book of the Machine)。
这些居住在地下小隔间里的人不能接触他人,失去了嗅觉,也没有空间感知能力。人们基本不旅行,只能通过大机器的网线听到、看到看似“认识”的其他人(类似于今天的脸书联系模式)。所谓“笨拙的公众聚会制度”(会议)早就被摒弃。信件通过“气动邮政”递送,与20世纪前半叶的商店寄信模式相似,但生活主要是以大机器为中心。福斯特笔下的未来无疑是黑暗的。
小说的主人公Vashti跟其他人一样厌恶地面上的生活,无法理解没有大机器的日子。她的房间里都是按键,按下去就能供水、供热、放音乐、送衣服、送食物,尤其是还能跟其他人交流。福斯特说这样她“就能和世上她关心的一切进行联系”(1985[1909]:111)。她被描写成“一块包裹着的肉……露着一张煞白的脸”(1985[1909]:108)。她从不离开她那狭小的房间,从不外出呼吸新鲜空气,也从不锻炼,因而肥胖到病态。并且,像这个社会里除了她“儿子”和极少的几个人以外的其他人一样,Vashti对自己依赖于机器的生活非常满足。所有人都满足于过着由大机器控制的生活。
福斯特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互联网,尽管他所描绘的大机器的特性主要是机械的而不是数字的。在他的描述中,这个社会从事的研究主要是对大机器档案储存的已知知识进行再处理,我们今天管这种大机器叫互联网或者云。这里不允许科研人员走上地面进行研究。一位学者这样说明循环利用既有思想的合理性:“要小心那些一手的新思想……新的一代应该是“完全不带思想色彩的”(Forster1985[1909]:131)大机器像网络一样无法传递细微的表达,只能交流一个大概的想法,人们认为对于实际目的来说已经“够好”了(Forster1985[1909]:110,参见Carr 2010,关于数字淡化体验)。
然而,有一天,Vashti的儿子联系她,让她出来跟他说话,并且强调“不要再用那个烦人的机器”跟他交流。Vashti很不情愿地坐了两天的飞船到地球的另一端跟儿子面谈,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行动(Forster 1985[1909]:109)。
就像福斯特笔下的世界一样,如今的人们也陷入了机器的控制,互联网通过亿万连接线将一切连接。人们对机器存在依赖性,大机器一旦出问题,文明就要崩溃。没有互联网,也就没有了食物、水、电话、信用卡支付和交流。奈(Nye)对于现状的描写跟福斯特有几分相似:“如果从美国城市和郊区的供应网络中去掉电力(或者汽油或者计算机),它们将可能变得无法居住。”(2010:131;Foster 2015:219)
在福斯特小说的高潮部分,真的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机器故障。所有的电力都被切断,没有食物供应,空气无法循环流通。机器消亡前的最后几天,Vashti看着她的小隔间外的景象吓坏了。人们在坟墓的墓穴间爬行,尖叫着,哭泣着,大口吸着气,互相之间碰来碰去。这些粗鄙不堪的人让她厌恶,像一场最糟糕的噩梦。她关上门,坐等末日降临。有爆裂声和轰隆声传来,灯光变暗,她意识到当能源耗尽,悠久的文明就会终结。因为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社会行将崩溃(Urry 2014b)。
但是她即将死去的儿子告诉她地面上有一群无家可归者——我们现在称之为群众(the multitude)正在等待(Hardt,Negri 2006)。这些被社会摒弃的人藏身于迷雾、蕨叶丛中,等待着大机器的末日。然后,他们将重新开始,重新掌控生活,互相接触、交谈、感受,但不会再通过这个曾经无所不在现在已末日来临的大机器(Forster1985:139-40)。小说的结局是人类只能通过那些被放逐、被边缘化、远离机器的人获得救赎。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认同这一观点并指出“人类未来的希望在那些能看清事实并且面对邪恶仍能坚持真理的人身上”(2015: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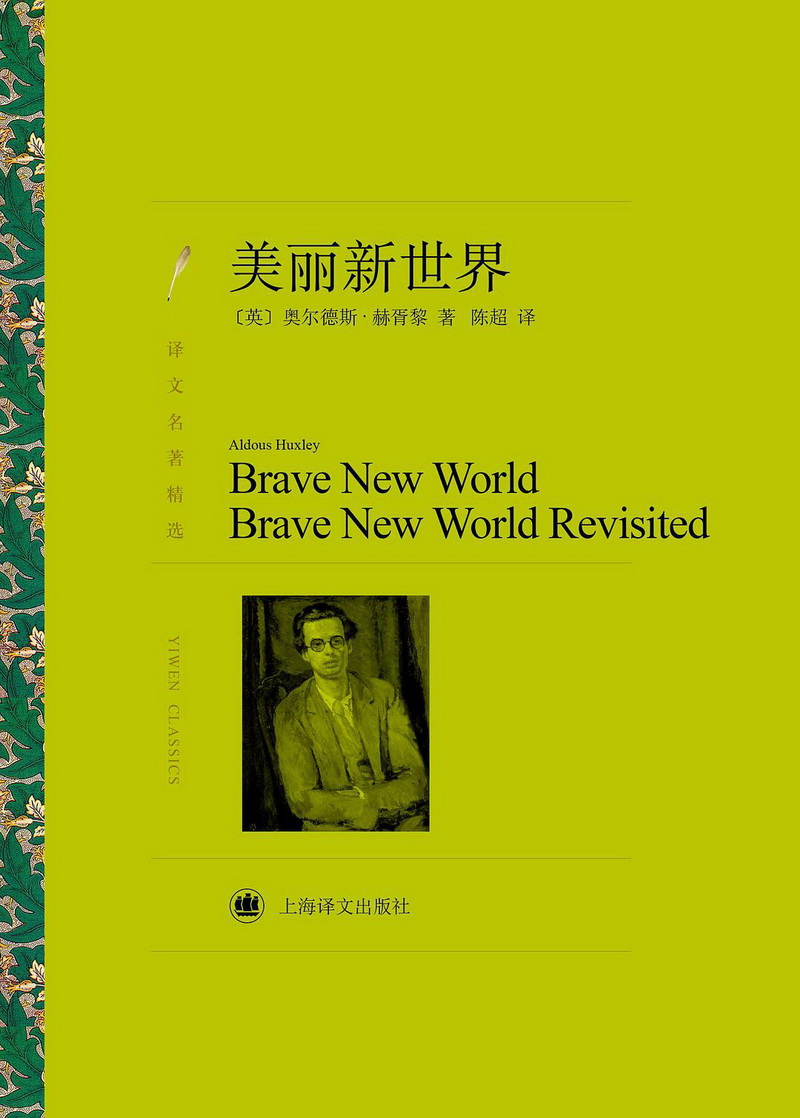
▲[英]奥尔德斯·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
与福斯特形成对比的反乌托邦作品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91[1932])。赫胥黎1926年在美国看到大众广告、心理调节、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让大众俯首听命感到震惊,预见到科学的发展最终将使人类获得原来神灵才有的力量。《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的基础是亨利-福特的流水线原则——大规模生产,统一性,可预见性,消费新产品。他认为美国代表未来,但这是一个恐怖的未来。福特被奉为新社会的神明,福特主义则是它的意识形态。生产传送带不仅生产亨利-福特开发的产品,还生产婴儿。大规模生产原则也被应用到了人类生物学领域(Kumar 1987:245)。
赫胥黎描述了公民如何从出生起就被干预训练得推崇消费。不断的消费和近乎全员的雇佣劳动以满足物质需求是世界国稳定的基础。婴儿也是通过我们现在所知的体外受精进行大规模培育。赫胥黎描写了如何培养儿童以确保其具有严格可控的能力,使其能够毫无怨言地适应新世界五个阶层的某一层。儿童自出生起就接受巴普洛夫条件反射训练,他们不会生病,每个人的寿命一样(大约60岁,到年龄就安乐死),没有婚姻或者对性忠诚的要求,也没有战争。
因此,在一种仁慈的独裁统治下,通过各种训练和药物“索麻”的控制,臣民乐于臣服。这个世界国开发的迷幻药确保没有药物副作用,让大家欢乐度假。《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就这样让人们爱上了他们被奴役的状态。赫胥黎接着写道:“《美丽新世界》中,麻醉性的不断刺激……被蓄意利用作统治工具,是为了防止人们过于关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状况。”(1965[1958]36-7)总的来看,赫胥黎担忧太多的娱乐、消费和药物麻醉将使每个人变得被动消极,外表幸福,浑然不知实际上他们正被“操控”。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电视真人秀节目里,这正是《美丽新世界》的当代版。许多后来的评论家发展了赫胥黎的观点,指出消费主义是大众的新鸦片。
奥威尔(Orwell)的《1984》(Nineteen Eight-Four,2008[1949])可能是最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书中描写的对大众的控制稍有不同。在第一页,Winston Smith注视着到处贴着的海报,上面写着:“老大哥在看着你。”一种被称为“电幕”的东西安装在居民家中和办公室里(包括占据人口85%的无权无势的无产者)。
这种电幕可以作为电视机和计算机屏幕在房间里使用,同时国家可以通过它看到、听到每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就像现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正在监视你。居民住在一个电子圆形监狱里。奥威尔写道:“你不得不活着一也确实出于习惯变成本能地活着——预先设想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被听到,除了在黑暗中,每一个举动也都被监视。”(2008[1949]5)还有一种“表情犯罪”,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被报道时,盯着电幕做出不适当的表情(Orwell,2008[1949]:65)。
奥威尔还描述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写作都涉及的读写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声音识别软件。手写已经变得有些多余,甚至还有了写小说的机器。
Smith在真理部工作的时候,各种气动管道输送着在屏幕上阅读的纸质版文本。他在报纸新闻报道之类的纸质版文本上做标记,改变文本,篡改历史。这些文本再通过气动管道传送回去。气动管道恰好出现于19世纪晚期,它们象征着技术进步,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将得到广泛应用。儒勒-凡尔纳的反乌托邦小说《20世纪的巴黎》(Par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描写了悬浮气动管道火车穿越大洋(1996[1863但直到1994年才出版])。还有人预见了海底管道运人速度快过飞机,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食品也可以通过气动管道递送到每个家庭。
Winston Smith开始写日记的时候,他的做法是用老式钢笔手写在笔记本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读写器留下记录。写日记本身并不犯法,因为根本没有法律,奥威尔以此暗指法西斯国家的统治无法可依。《1984》写于1946到1948年间,处于一党专政的集权主义时代,宣传机构的歪曲事实已经变得明显。奥威尔批判了各种宣传和监控技术,我们也因此了解到现代国家和公司利用了各种版本的“新语”。
奥威尔写到新语是如何被用来“缩小思想的范围,通过将词汇量减到最少来间接促成这一目的实现”(2008[1949]:313)。逐渐是各种“事实”消失进入“影子世界”(Orwell 2008[1949]:44,290),就像《1984》中的人失踪便立即被官员从历史中删除。最后,为真理部工作的Winston Smith自己也被历史删除。
在奥威尔看来,这个社会的目标就是权力本身-建立和保持独裁,由权力的代表施行,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加以实现。人们并不知道统治政权的成员是谁。Winston Smith遭受了七年的监视,在长期抗争之后,最终崩溃。他愉快地学会爱上老大哥,丧失了自我,最后声称2加2等于5(Orwell 2008:311)。《1984》剖析了未来社会权力构成的机制,尤其是监视技术在新的权力世界所发挥的危险作用。
在此讨论的最后一个反乌托邦未来出自一个不同体裁的作品: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短篇小说《黄色壁纸》(Yellow Wallpaper, 1982)。小说描述了禁锢对主人公精神健康的摧残并最终导致其患上精神病。女主人公整日待在自己的房间,慑于丈夫的淫威而无力逃离,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她沉迷于房间里黄色壁纸的花纹和颜色。最后,她出现了幻觉,以为壁纸花纹后面有女人爬行,而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离开,这是她认为唯一安全的地方。后来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探讨了许多相似的父权禁锢文本以及可能出现的不同的女性主义未来。
结论
至此,我提出了到上世纪中期为止英语文化中关于未来预测的一些主要节点。本章探讨了各种“社会未来”,展示了有关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式未来社会的预测简史,提出了一些在后续章节中将会进一步展开讨论的话题,研究如何预测未来社会。
尽管不可能“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大多数社会都有自己的步骤和话语用于预测未来,谈论未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未来,无论这个预测的未来是在神灵或人类的掌控中。人们对未来进行了想象、预测、神化、预言和讲述,这些预言未来的方式被称作“昔日未来学”,它们为后来的未来预测提供了关键的术语和关注点。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